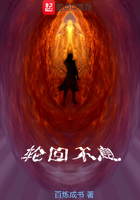孙健君看见远处的一条机耕道,一辆拖拉机在道上行驶,扬起的尘土遮盖了一小片天空。有一次他和赵渔大谈机耕道,很快达成了一致:机耕道充满了诗意,阳光下的机耕道,通向天尽头,两旁的田野次第铺开。机耕道是乡间小路和林中小径的同义词,她和如今随处可见的、光滑平整的水泥路不可同日而语。雨天的泥泞,导致阳光下的尘土飞扬,挡不住她溢向四面八方的诗意。她纳人了天空,河流和田野,而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劳作的人们洒下汗水……赵渔说得好,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不会懂得机耕道的含义,正如他们不懂林中路的含义。他们的思维整体趋向于物,趋向于计算机。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世界对自然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算计……
机耕道近了,黄色的泥土路,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小沟一闪而过。孙健君回头瞧机耕道,碰上潘婷的目光。后者有了一种沉静的光景。孙健君不禁想:看来你们用以自卫的武器都一样。
他笑了笑,继续目视前方。
后座上的两个女人不说话,她们的坐姿显示了她们之间的距离。两个沉静的女人,两个不说话的女人,她们共同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她们共同构成了某种状态,有趣的状态,值得玩味的状态。谁来玩味?孙健君来玩味。他是这种状态的揭示者。他一手促成了这种状态,又加以揭示,这就很有趣了,非常有趣,非常非常有孙健君再度笑了,他模仿谁呢?托尔斯泰还是海明威?海明威是把握形形色色的状态的老手,极善于切人当下,仿佛他是海德格尔的大弟子。看看他那些大作吧,《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雨里的猫》、《白象似的群山》、《大二心河》、《阿尔卑斯山牧歌》……这个欧内斯特啊,真是太棒啦。
孙健君暗自发笑,没有逃过后座上两个女人的锐眼。自鸣得意哩,尤佳想,你自鸣得意就说明你不够优秀。你有钱,你风度翩翩,你写小说,可是你呀,你自鸣得意,就暴露了你的缺点,影响你的魅力……他干吗发笑呢?潘婷想。笑我还是笑她?莫名其妙……
两个沉静的女人,开始用眼睛说话。换句话说,她们开始用眼睛打架,不须直接开火,只同时把矛头指向了孙健君。这开车的男人朝她们投去一瞥,立刻有所领悟。静态变成了动态,他想。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你要记住,用你脑子里常用的那个笔记本。她们先前不说话,现在用眼睛打架,不动声色的黑眸子活跃起来,长睫毛既矜持又生动,仿佛进入了临战状态……但是放心好了,她们打不起来,有你在,她们打不起来。她们至多暗地里互不买账,除非你存心制造恶作剧……
龙泉驿到了,不高的几座山,一望无际的桃子树,其间点缀了竹林茅舍这个词,如今包含了水泥楼和青瓦房。这一带的农民早已翘首以待,有些人在树上弄了绢花,看上去倒比真花还艳。这年头,城里人所到之处,乡下人也学精了,一家一家的像是比试精明。孙健君有个朋友吃过一顿倒霉透顶的饭:盘子里混杂着别人吃剩的鸡骨头,因是两种鸡皮色不同,才发觉了,同店主大吵一架,险些动手。这朋友对孙健君讲述时,仍是余怒未消,他骂道:我日他妈的龙泉驿!他吃了一顿恶心饭,十年八年忘不掉,难怪他要日它的妈。孙健君当时打趣道:龙泉驿没有妈,你日它上面的空气好了。
空气不错,游人不多。有人躺在树下晒太阳一从枝叶透过来的零碎的太阳。孙健君停车的那个院子的农民殷勤劝他洗车,孙健君说:我昨天才洗过车。那农民就笑,递烟搬椅子的,一面炫耀他洗车的优势:高压水龙头,雕牌洗涤精,四个人动手擦三次……主要是价格公道!又说:您大老板水牛身上拔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哩。孙健君被言语围困,动弹不开,他知道洗车不过是前奏,后头还有配套服务……却也罢了,于是坐到椅子上抽烟,望着那两个女人往桃林深处走去。潘婷的黄色灯芯绒裤因路的不平,便一扭一扭的。那背影有点似曾相识。阳光照着他的脸,记忆不甚清晰。
桃林深处,别有景观:有男女抱在地上嘴对嘴,不止一对,靠山的油菜地里还有动静,花枝摇曳,似乎不仅是嘴对嘴。两个女人走过,地上的男人欠起身,吃惊不小,张了嘴瞧着,直到同他对嘴的女孩拧他的耳朵。也许是同性恋,他作着判断。女孩继续拧他的耳朵。女孩说:人家同不同性恋,关你屁事……
终于有一块清静地,且在半山坡上,视野开阔。潘婷铺开一块蓝色的塑料布,摆上一堆吃的东西,啤酒和饮料。塑料布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四周洒了风油精,驱赶蚊虫。尤佳躺下来,睁眼是桃树和桃树后面的蓝天。微风吹拂,并无半点凉意,倒是送来了油菜花的清香。有什么东西掉到她的头发上,潘婷俯下身子,替她拂了。尤佳睁开眼,两人的脸这时靠得很近。对视片刻,尤佳的眼睛又闭上了。她们一直是好朋友,虽然性格不同。她们互相照顾,一人生病,另一个守病榻,决无半点怨言。孙健君出现了,她们的友谊忽然变得脆弱。女人的友谊经不起男人的考验。车上的滋味不好受,现在好些了。潘婷是个直肠子,又刚从死亡线上回来不久,或许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提醒她,暗示她,她或许会走开。不过那也没意思了,何必呢?
过了好一阵,孙健君还没有过来,潘婷站起来张望:这人跑哪儿去了呢?
尤佳说:他在洗车。
潘婷说:洗车也洗不了这么长时间嘛,莫非迷了路?
尤佳说:迷了路他会打电话。
潘婷说:你起来,咱们去瞧瞧。
尤佳说:我们走了,这些东西咋办?你一个人去吧。
潘婷说:你不去,我也不去。让他迷路好了。
尤佳说:也许他就喜欢迷路,在这林子里东游西窜。
潘婷说:你这个朋友挺特别的。
尤佳说:也是你的朋友嘛。从昨天起,你们就成了朋友。要不就在更早的时候,从他到医院来看望你,送你一束鲜花的那一天起。
潘捧说:当时我昏昏沉沉的,你们两个好像在床边谈了很久。后来你又送他出去。
尤佳说:我是送他出去了,我替你感谢他的鲜花。
潘婷说:那是我住院期问,收到唯一一束鲜花。
尤佳说:那学生家长不是送来了一束花吗?
潘婷说:我扔到楼下去了。那家长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嬉皮笑脸的,他巴不得送我一个花圈。
尤佳说:我没送你鲜花你不怪我吧?
潘婷说:瞧你说的一束花算什么?你陪我的那些日子,我永生难忘……
潘婷的眼圈红了,她握住尤佳的手。再往下说,眼泪会掉下来。车上的那点不愉快,此刻化为乌有。蜜蜂在旁边嗡嗡响。太阳照在山坡上,发出泥土和青草的混合气味儿,连同塑料布的气味儿,油菜花儿的气味儿……尤佳忽然心生一念:向潘捧讲情人节,讲那天她同孙健君……她试了几次,开不得口。她是温和的女人,很少同别人争夺什么,何况是同她的好朋友。
尤佳怔怔的,阳光和油菜花有些刺眼。她打呵欠。你睡一会儿吧,潘停说。尤佳闭上眼,潘婷抚摸她的头发。周遭宁静,蜜蜂的嗡嗡催人人眠。尤佳呼吸匀称,平坦的腹部缓缓起伏。这人睡着了,潘婷想。潘婷有午睡的习惯,此刻却一点睡意都没有。她眺望远处的桃林,留意着一个身影,穿蓝色西装的身影。他挺拔的身姿同桃树的形状恰成对照……然而又过了一阵,桃树仍是桃树,哪有什么蓝色的身影。奇怪,潘婷想。这时有人从身后拍她的肩,吓她一跳。扭头一看是孙健君。
潘婷红了脸。刚才她想着他,而他从背后悄悄朝她走过来……
孙健君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尤佳,潘婷压低声音说:睡着了。孙健君说:好个睡美人。潘婷莞尔一笑。
两人坐着说话,由于声音低,难免靠得近。潘婷斜倚着身子,孙健君打了盘腿。另一边躺着尤佳,仿佛真的沉沉入梦。太阳已成斜照,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有风拂过,孙健君脱下西装,叫潘婷盖在尤佳身上。
潘婷坐回来时,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你心真细,她夸奖孙健君。后者笑道:我小时候做过学雷锋标兵,受到全校表彰。这件事对我有影响。
潘婷说:助人为乐的好同志。
孙健君说:助人为乐谈不上,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小时候受表彰,激动不已,是虚荣心在作祟。
潘婷说:小孩子有时也需要一点虚荣。我们小学教师有一个法宝:充分调动学生的虚荣,然后呢,再加以引导。没虚荣的孩子不好教。
孙健君笑道:有道理。是你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么?
潘婷指了指尤佳说:我们共同研究的成果。
山风又起,虽是和风,却也吹得花枝摇动,蜂腰倾斜。潘婷说:你不冷么?孙健君摇头。潘婷又说:不冷才怪,你穿得那样单薄。
孙健君说:我额头上还在冒汗呢,不信你摸摸看。
潘婷伸手摸他的额头,果然有微汗。孙健君瞥了一眼地上的尤佳,尤佳不动,仿佛仍在梦中,他的目光就回到潘婷脸上。适才潘婷关切地摸他的额头,现在他含笑瞧她的脸。潘婷脸上的红晕尚未褪尽,经他这一瞧,又有回复的趋势。她说:这太阳晒得……
他说:是啊,这太阳。
她说:你额头冒汗,我脸上发红。
他笑道:人面桃花相映红嘛。
她也笑:桃花尚未开哩。
他说:没开才好。桃花若是开了,明年再来时,就是人?
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了。
孙健君这一说,潘婷的脸就真像桃花了。地上的睡美人翻身朝向山那边,看来的确是睡着了。潘婷转身望着她,想说句什么的,一时却找不出话头。过了一会才转过来,重新迎着孙健君。后者嘴里含了一根思茅草。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孙健君这个年龄的人,童年是斗过草的,潘婷就难说了,即使斗过一两回,也是循着前人的诗意。斗草……潘婷说。孙健君启齿一笑作应答。二人似乎同时想到了苏轼的名句,都不念出声,效果就比较理想,不出声的诗句,渗人不出声的山、不出声的阳光和阳光下的花瓣。风有声,蜂也有声,却是有声衬无声,将身边的景物融为一体。
孙健君近距离看潘婷,看见了那道刀痕,略呈弧形,像一弯新月。外科医生会欣赏它:从缝合术的角度看,几乎是个奇迹。而孙健君宁愿正视它:刀痕就是刀痕,它意味着美中不足。不过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美中不足的好处是:它带给了潘婷一份坦然。坦然与刀痕一同摆上了这张俏脸,前者一望而知,后者若隐若现,得与失还很难讲哩。
孙健君近距离看潘婷,看见了刀痕,也看见了她的坦然。你摸摸看,潘婷说。凹凸感基本上消除了,我吃了一种德国人的药。但要彻底消除,医生和药品都无能为力,除非请出一个人。
潘停说话时,孙健君正摸她的脸。摸完了往上一指,潘婷就会心一笑。她所讲的和他所指的完全一致。
那人是上帝。
上帝是在高处,无意做什么外科医生,却一手安排了此情此景:两人你摸我的额头,我摸你的脸,摸完了还要默契,抵达了交流的最佳境界。上帝大约微笑了,他接着安排,伸出无形的巨手,将太阳轻轻地拨进云层。那手指随风而至,要将这山坡上的男女合二为一,临了却方向一转,拍了拍睡梦中的女人。
尤佳醒了。
我睡得好香啊,尤佳醒来就对自己的睡眠作评价。她欠身坐起,伸了个舒适的懒腰。潘婷说:孙健君怕你着凉,把衣服盖在你身上。尤佳含笑谢过,潘婷说:我们说话的声音小,没打扰你的美梦吧?尤佳眉头略皱,旋即笑道:既然你们的声音小,自然不存在打扰的问题。再说我也没做-一我这人不大做梦的。
潘停说:做梦也不是坏事嘛。
尤佳说:做梦是好事。祝你美梦成真。
潘婷说:祝你先做个美梦,然后美梦成真。
尤佳笑道:美梦多半是假的,是兑不了现的空头支票。
潘婷说:做做也行啊。
尤佳说:你做吧,那是你们的事……
越说越不像话啦,孙健君想。他动手撕鸡腿。两只连皮带肉的肥鸡腿,分赠两位说梦的女士,他自己享用鸡屁股、鸡爪子和鸡颈项。一瓶红酒转着喝,瓶口上带点口水,虽然不大卫生,却能见证友谊。一只烤鸡下肚,太阳也西沉了。又吃了些薯条、面包、沙胡豆,后者咬得脆四川人吃这东西,已不知吃了几百年。孙健君咬得尤其响亮。
潘婷说:你这牙齿可以做广告了。
孙健君说:我父亲就爱用沙胡豆下酒。困难时期,一颗胡豆一杯酒。文革时搞武斗,红卫兵来了,他端出一盘沙胡豆,化干戈为玉帛。我当时小,两三岁,咬着胡豆满地跑。
尤佳笑道:沙胡豆是你家的传家宝。
两个女人原本不吃这类零食的,孙健君有此一说,她们便吃起来。潘婷还吃得有滋有味,一口细牙,满是沙胡豆。
日落时分他们在农家喝茶,碧空如洗,圆圆的落日在地平线上欲下未下。他们在楼顶平台上喝茶,视野广阔。茶叶也不错,上好的竹叶青,只是价也不菲。楼下停着孙健君的2000型桑塔纳,黑色车身泛着夕照的红光。他眺望天边,意识到自己的好心情,昨天和今天的好心情。赵渔在这儿就好了,他们可以讨论落日。赵渔的特点是无中生有,凭空思索。他有描述落日的能力,纯粹的落日,跟科学毫无关系,也说不上投射人生体验。他盯住一点不放,从不轻易挪开视线。这叫定力。好比爱情。是啊,爱情。他的爱情也就是商女的爱情,两人的爱情是同一个东西。彼此都盯住不放,盯了十年了。看情形还会盯下去。祝你们好运,孙健君想。爱情辉煌如落日,至于我,我要个插曲就行了,快慰平生的小夜曲……
尤佳起身上厕所,约潘婷同去,潘停摇头。尤佳走向漆成白色的露天楼梯,背影略显矜持。厕所在庭院外的桃林中,店主有意搞的花样,让客人在桃花下或站或蹲。尤佳步出庭院,没人桃林。孙健君的视线追随她,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潘婷坐他对面,问他看什么。他说:我在想,这店家将厕所建在桃花深处,有些名堂。
潘婷转过身去循着他的视线张望。几十步之外,有一座简朴的茅屋露出它的尖顶。
过了一会儿孙健君也去了厕所,潘婷一人留在屋顶上。她站起来走动,走到屋顶的边缘。孙健君正走到院子里,他抬起头,同她的视线相接,彼此笑了笑。有个男人站在院子当中,他也笑了笑。他双手递给孙健君一支烟,又仰脸看潘婷,是讨好的意思。他随即发现自己被忽略不计:楼顶上的女人目送这个穿西装的男人,直到后者在桃林中消失。
弄不懂,院子当中的男人想。他一直在揣度这一男二女,他们之间谁跟谁……他们留下来过夜就好了,谁跟谁就能见分晓。或许一个跟两个……他再次咧嘴笑了。他瞄了一眼堂屋,那儿坐着他的胖老婆。胖老婆不看他,她瞅着院墙边的一群鸡。
太阳落下去了。
潘婷再次走到屋顶边缘,一只手搁在楼梯的扶手上。她的黑线衣、黄裤子同白色的扶手相映生辉。院子里的男人走来走去,像是在忙碌。
孙健君进厕所小解,女厕那边没动静。他用打火机点烟,又咳了一声,那边仍是没动静。他走出厕所,喊一声尤佳,没人应答。他顺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走了几分钟,才看见尤佳站在一条水沟旁。她身边的两棵桃树巳经开花了。她低头看水,并未仰面看花。这情状令人心动。孙健君注意到她也穿了件黑线衣,款式比潘婷的那件更俏。下身是一条黑裤子,配着乳白色的高跟鞋。
听见脚步声,尤佳朝孙健君转过身来。
孙健君说:我忘带相机了,在这儿给你照一张相,一定很漂亮。
尤佳说:我平时很少照相的。
她想:我以为你又要来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
孙健君说:这两株桃树先开花,恐是临水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