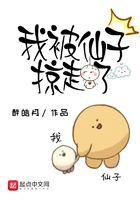日子越过越慢,在我们的沉默中,慢得几乎有些拖不动了。屋子里的那些木质的家具还摆在那里,发着黑黝黝的光,一副很疲惫的样子。这天我下楼,她刚好上楼梯,我们就在楼梯口撞着,她让我,我让她,最后还是我抢步下了楼。又过了几天,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我试着跟她说话,我说:“水开了。”我说:“我去洗澡去了。”我说:“一会儿你洗吗?”她说:“洗。”
和母亲冷战的日子,我感到烦闷,我想逃离这个家,这个如死水一样的黑屋子,快下雨的时候,屋子闷得更慌,我受不住,感到难言的不自在,就时常跑到外面换空气,去闻那些黄桷树的味道,闻那些青苔的味道,从西街跑向东街,然后从东街跑向西街。等到雨彻底地下来,滴在屋檐上,“啪嗒啪嗒”的,我再慢悠悠地走回去。
这天,又逢“一四七”,外面下着雨,店里的生意并没有因为雨天而清淡多少。母亲说:“锅里蒸饭来不及了,你上东街张家饭馆借盆米饭回来,动作要快些。”我说:“哦。”然后穿过堂屋,穿过那些正吃得起劲的客人,慢腾腾地走出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端着一盆米饭,故意慢腾腾地走,我知道母亲在家很着急,那些等着吃米饭的人,会着急。可我就不喜欢踏进那屋,更不想帮她干活。
我慢腾腾地走在青石板的长廊上,雨水轻轻地落在我头发上。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了,这些日子雨水充足得很,有一阵没一阵地下着,有时候还会东边太阳西边雨。
我宁肯在石板路上多换会儿空气,多淋些雨,也不要回家。我抬头望屋檐,望那些纷纷的雨线,雨水像三月的美酒一样,在风向合适的时候,扑在脸上格外甜美,我慢腾腾地走着。
一位老太太在自家屋檐下缝着鞋垫,她在身后说:“唉,当年我和她一样,也是这样走着走着,就老了。”我回头望望她,她并没有同我说话的意思,而是坐在门槛上自言自语着。
我停下脚步,望着她斑白的头发,我突然感到一种双重的存在,过去的影子在我脑子里塞得满满的,像一堆垃圾,怎么清理也清理不掉,还流着污水的味道。而现在,我手里端着那盆米饭,傻乎乎地站在雨里,远远地望着那排青石板长廊,那个家门敞开着,家门口没有人向我快活地招手,家门敞开着,外面也没有谁向我招手,我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一种难言的尴尬与窘迫,只有雨水还在我眼前不停地下,没有答案,没有未来。
转眼,一年,两年,三年,都过去了。
由于我成绩偏下,也就考了个专科。她逢人就说:“女儿上了专科大学。”
“哦?专科大学,好哟,惠芳,你也快苦出头了。”刘阿姨说。
“唉,我们家夏茜就考栽了,没考上啊,以后还是跟着我打铁吧!”刘阿姨有些叹气。
母亲笑笑。或许她以为专科大学比本科还好吧,我也不做什么解释。
“我给你弹了床新棉被,你拿学校里用吧。今年棉花又涨价了。”这天太阳出来了,她坐在我的左边说。
看着她在阳光下暖暖的样子,我脑子里空白了好一阵。我停下手中的活,呆望着青石板路很久,我想原谅她,真的。就在此时,我想原谅她,可是后来我突然又笑了,也许那一晚,不过只是你连绵不断的一桩事而已,一桩偷情的事而已。我不断地说服自己,即使这天阳光再好,她在阳光下再温柔,我也不能原谅她。
去城里上学的那天,我收拾了行李。走到黑水滩河边的夫妻树下,我背上她新做的棉被,上了船。
船夫撑着长篙,船离开了岸,她站在码头上没说话,船夫摇着桨,一浪一浪地划着水浪。
我到了河岸的那头。现在,她在河的左边,我在河的右边。我沿着河岸走,打算穿过河岸边的竹林子,去车站,去城里。她在那头也顺着河岸走,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她时不时地在河的那头,一边低头走,一会儿又看看我,一会儿又抹抹眼泪。
河岸那边有很多鹅卵石,她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走了半个小时,我终于忍不住说:“回去吧!”
她没听见,继续顺着河岸走,我喊着:“妈——回去吧!”
她听见了,在河岸的那头,站住了,痛哭不止。
三年了,我发现我三年没称呼她为“妈”了。我不禁走着走着,在路上给自己唱了首英文歌。其实,那首英文歌的歌词是关于爱情的,可我总觉得那旋律很适合我和母亲隔岸相望的场景。唱着唱着,阳光跌进了河里,从河面发出刺眼的光芒,那些光芒一颗颗碎石般地打在我脸上,刺得我眼疼,我用手背抹了抹泪水,唉,今天的阳光好烈。
13
大学四年,我颇爱名牌,因为小时候“节约”怕了,所以我偏爱名牌。她每个月都会寄来六百块生活费,这些是远不足以我买一件外套的。没办法,我爱名牌,爱得没办法。于是,我打工,每周末去商场做临时促销,一天能挣到五十块钱,从我买第一件衣服起,我就暗自发誓,要把小时候没穿过的新衣服都给穿回来。
我的床铺是全系女生中最乱的。没办法,这是她从小教育我的结果。有句话说得真好:“物极必反!”我能有多懒就有多懒,袜子时常堆着不洗,内裤也不洗。逼得没法穿了,才会去洗。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很多女生都和我一样,寝室乱糟糟的,只是乱的程度不一样,大概一百个女生当中还是有一两个是勤快的。
大学四年,我自卑得不敢谈恋爱,心里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因为我的胸部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开始发育不良。说得好听点是“太平公主”,说得难听些是“飞机场”。我害怕恋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自卑,我害怕男人发现我的秘密之后不满意离开。同时,我也害怕游泳,唯一游泳这个体育项目,我懦弱得不敢参加。我还羞涩地对我的男体育老师说:“不方便。”我想那个体育老师一定瞎琢磨着,为什么每次都不方便,你一个月要来几次?没办法,我害怕穿那些紧身的泳衣,害怕。
大学四年,我颇爱洗澡,可是从来不用香皂,只是用很烫的清水淋浴。每当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洗澡,脱去那些厚重的衣服,那些有“负担”的首饰,一丝不挂地去洗澡。每当冬天冷的时候,我也洗澡,因为洗澡可以驱逐寒冷。每当我头发很长的时候,长得用梳子理不清,打结,我也去洗澡,因为把头发洗干净后,我再慢慢把它们梳理清楚。同学说,剪了吧,梳着费力。我说不剪,我要把它理清楚。
大学四年,我从没有回家过过春节。
母亲打电话来,她的语言妥当了些,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家都不要了吗?”
我说:“学习忙!”
这一天,母亲又打来电话,忍气吞声地重复着:“家都不要了吗?”
我说:“学习忙!”
她是个脾气倔强的女人,她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她又怎能在电话那头默默忍受我对她的敷衍呢。她终于忍受不住了,她愤怒地说:“你忙你忙你忙!你天天都在忙!我怎么办?”她说不出她的委屈,她抓不住关键词,论不清道理。她只能在电话的那边胡闹。
“我本身就很忙!”我没好气地一句话把她顶回去。
“你现在读书了,有文化了,我说不过你了!”母亲愤怒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她又打来电话,低声下气地说:“我来看你吧,妈妈来看你。”
我找理由推辞。
她说:“你让妈妈来看你吧,你一个人在学校待着干啥?冷冷清清的。”
我继续找理由推辞。
她又退了一步,说:“妈妈求你了,妈妈来看你,好吗?”
我接受了。
这年寒假,母亲来看我。四年不见,她老了些,额头上有了皱纹,两鬓也添了些白发,眼下的皮肤有些松垂,但是皮肤依然白皙,穿着依然干净得体。
“现在我们镇成了旅游景点了。”母亲说。她仍旧坐在我的左边跟我聊天。
我说:“哦。”
“老街上的树,都挂上‘保护植物’的牌子了。”她说。
“我这几年头发掉了好多,早上梳头,头发就大把大把地落,头顶上都没多少头发了,只能戴帽子遮遮。”她说。
我说:“哦。”
她一个人说了很多,她说什么,我就回答说“哦”。她不再问我为什么没话说,她拼命地找些话来避免母女之间的尴尬。可是我偏偏就是很不知趣的,很不给她面子地说“哦”。
两小时后,她见我并没有留她之意,有些郁郁不乐地起身要离开。她走的时候,我假惺惺地把她送到公交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
公交车站在对面,她客气地说不用送了。于是,她独自穿过马路,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似乎在驱使着我,让我移步上前,想让我去跟她描绘一些东西,比如描绘些未来的生活,描绘些明天我们的需要。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置身于人海更孤单了。在车水马龙中,她又那么不顾及车辆地,脑袋来回张望,像一只迷途的绵羊,非常渺小地,被丢在人堆里浮不出来。
我的心抽缩不止,我恍然发现自己像个暴君,折磨着这个女人的心,并且是一个孤独的、正在一天天衰老的女人。
我担心她会不会在路上有意外。是的,第一次对她有担心。我自己也惊讶着,为何原来的仇恨与恼怒竟然在霓虹灯中慢慢褪去,唉,为什么我的视线会越来越模糊,模糊到看不清那些霓虹灯,模糊到看不见她。
14
工作了,终于工作了。不用再花她的钱了,不用再长期遭遇她了。
她说:“以后你能每个月给我寄点钱吗?一百块也行。”
我说:“好。”
她说:“不是寄,是给我带回来,行吗?”
我说:“行。”
我照旧每个月都会回去看她,只是回去给她送钱而已,有时吃过一顿饭,在家待不住,就想着要走。饭馆仍然经营着,窗台上的昙花还在,她说:“老了,还是得找些事来打发时间。”
她去买了只猫回来,她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和猫住一起。她每天都去菜市给猫买些鳝鱼、泥鳅回来,她给猫咪煮饭。有时候我在屋子里坐着不说话,她就同猫咪说话。她说:“猫咪,过来,过来洗澡咯。”
猫咪不听话,她就到处找猫咪,逮着猫咪后,猫咪又从她手里溜走了。
猫咪躲床脚下,她就趴在地板上,像逗一个小孩那样,偏着脑袋看床底下:“猫咪,出来哟,出来洗澡澡。”她说着一些宝宝语言,猫咪还是不出来,她就伸手说:“过来嘛,猫咪,洗澡澡,洗了才干净。”
……
母亲说:“我就喜欢猫咪,猫咪爱干净,猫咪睡觉醒来,还自己趴在花台上,懒洋洋地洗脸,眯着眼睛。”母亲还说:“猫咪拉完屎,还知道自己把屁眼舔干净呢。”
母亲说:“猫咪听话,你一唤它,它就摇尾巴。”
……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只猫。因为我觉得猫是奸猾的,就像我的仇人夏茜那样,脑子特别奸猾。其实,我也很替小猫担心,每次看到她给猫咪洗澡,就会想起小时候我洗澡的样子。猫咪很不自在地站在水池里,母亲给它抹香皂,替它洗脚爪,一边洗,她一边说:“猫咪别乱动,洗干净了才漂亮。”猫咪洗完澡后,母亲又找来吹风机,把它身子吹干,母亲说:“别感冒啦。”
我至今也想不出,为什么母亲偏爱给别人洗澡,真的想不出来。
这天,我回家看她看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要起身走。我不喜欢在家过夜,不喜欢那阴阴暗暗的阁楼,如此一来,天也快黑了,也该走了,我起身找“明天还上班”的借口,表明要回城里。她也不挽留了,她仍旧用着开玩笑的语气说:“你翅膀硬了,我哪还能管得住你?”她送我到桥头,像记忆中所有的母亲一样,如送如迎地站在桥头望着远去的游子。
她站在河岸边,旁边还有几只鸭子,在岸边“嘎嘎”来回踱步。船夫用长篙撑船,船只在水面上打转后,慢悠悠地越撑越远,桨声一浪接着一浪,在寂静的夜空下有节奏地泛着,我已经看不清她的脸了,她只是默默地伫立在岸边。
我到达右岸后,她依旧停留在左岸。我朝前面走,她也顺着河朝前面走,现在,在我的前方,是北碚城的灯火辉煌,它在夜空下,在不远处繁华地闪烁,我的身后,小镇的枯藤老树在夜空下黯淡下来,渐渐沉睡,只有母亲一个人站在河岸边,在黑暗中,顺着河水“哗啦啦”的声音,逆行而上追随我的身影。望着河畔的那一边,她佝偻的黑影,我不禁黯然泪下。母亲,如果今世,我是一个男人,我必然好好爱你,耐心地去爱你,爱你奇怪的脾气,爱你的缺点和优点以及所有。只可惜,我是一个女人。
北碚城是繁华的,那里有川流不息的人潮,那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丰富的城市。它没有偏岩小镇的灰蒙蒙,也没有湿漉漉的伤感。尤其是霓虹灯令我着迷,甚至有些沉醉,望着那一片斑斓,我内心的感情上下起伏不定,这么多年了,我无法把那桩事从她身上推开。这么多年了,那个被他人欺负的孩子,现在已经彻底摆脱了。可是摆脱之后又怎样?好吧,说我想说的,时至今日,我依然孤独,我独自走在河岸边,走向通往那个繁华的北碚城,我想起那只可怜的猫,想起家里阴阴暗暗的光线,想起屋子里木质的家具,以及那个以猫为伴的女人。我悲也不是,喜也不是。
15
这一个月,我又回了一次家。
时间真快,又快到过年的时间了,老街的样子依然没有改变。小镇虽然旧,但不邋遢,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被人擦明亮了,有的人家还把去年屋檐上的灯笼卸下来,换上新的,门窗都大大地敞开着,说是为了通风换气。那些老太太们闲来无事,就扛着被子拿到老街上去晒,她们晒完被子晒青菜,她们说,青菜晒干了,再腌上盐,来年春节的时候就能吃。
“你有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母亲坐在我的左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