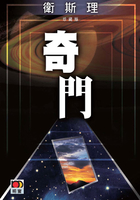姬兰音又回到了原先的医院上班。第二天她给远在茅茨的丽娜姐妹打了个电话,告知她们家里近日的变化。丽娜在妹妹工作的医院里接到了妈妈打来的长途,半小时后,茜如便分娩出一个男婴。就在茜如产期临近,痛苦地在产床上呻吟时,卢西鸿被派往县北一个乡镇考核干部去了。
“原谅我,”临出发前,他匆匆跑来跟妻子告别,“眼下正是调整提拔干部的关键时刻,我抽下去考核别人,组织上也正在考核我。我不能让人家说:‘喏!他卢西鸿靠着当代省长的老丈人爬上去了。’我也是为了避嫌才这么狠心的。整个县城像我这样成天下乡跑的人多的是。男人哪能不顾及自己的事业呢!再说,你身边有姐姐丽娜照顾,等忙过了这阵子,我从老家把妈接过来服侍你。”茜如衰弱无力地抬眼望望丈夫,又一阵更紧密的宫缩袭来,疼痛让她不得不紧咬嘴唇,完全无遐顾及丈夫的去向了。
丽娜接完电话回来,卢西鸿已经走了。她紧攥住茜如因为疼痛变得冰湿的手,喜滋滋地说:“这下好了!妈妈也回省城了。我们再也不用每次坐三、四个小时的破车在讨厌的山路上颠簸了。我讨厌紫溪,讨厌那个地方。”
她兴奋地看着妹妹,毫不掩饰她对那个地方的憎恶。
“记得上小学,每次布置作业老师就叫我先滚出去。我不想离开教室,老师就说我是‘牛鬼蛇神’的子女,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要哭一场。爸爸倒霉的第二年我小学毕业,那些造反派不准我上初中,硬生生的荒废了我两年的时光。他们把我下放到紫溪最偏远的一个山村插队落户,住在生产队一个破旧仓库里。仓库角落里堆了几十袋化肥,那气味呛得人泪水直流。头年冬天下了一场暴雪,像尿素颗粒的雪粒打在屋瓦上‘嘣嘣嘣’的响,雪粒和风搅在一起‘嗖嗖’地从瓦缝往里灌,筛洒得满地一层,连床铺被窝上都洒了一层雪。冻得实在受不了,我抄一把镰刀摸到后山砍了一捆松树丫子,趟着没膝的雪窝子一步一爬往回拖……连夜里做梦都梦到我们家搬了好房子,上面盖了顶棚,不漏雨,不漏雪,还安了两个亮敞敞的大窗户……好不容易熬到了大招工,就因为我没有后台,被分去跑堂端盘子!而那些权贵老爷政治暴发户的子女呢,一个个随心所欲地挑拣好大学、好专业,还有的蠢货放着大学不上,像一群疯子一窝蜂钻营到国营大工厂。呸!我罗丽娜以为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呢!哈!我倒要看看以前欺侮过我们的势利小人怎么再重新表演一次——像狗一样!”
茜如在宫缩稍微缓解的空隙集中精力想了想丽娜的话,反过来用力捏握住丽娜温暖的手,就在那一瞬间,她惊讶地感觉到丽娜的手竟然变得粗糙不堪,肤间纹理粗深,她努力把它举到自己胸前,看见那曾经同她一样细嫩的手掌罗布了一层淡黄色角质化的茧层!她不禁叹息一声,下意识地用自己已经疲软得没有力气的手痉挛般地抓住丽娜的手不松开。她拼命抑制住困倦,低弱地说:“姐,我们姊妹你最造孽,错过了最起码的初中教育。这样的文化底子实在太薄了。”
“算是扫盲吧……”丽娜叹息说。
“你的英文不是还有一些基础吗?”茜如声音渐渐小到像蚊子嗡。丽娜小声嘀咕道:“也就剩二十六个字母还没忘……”接着她又听茜如说,“这几年我也在反思,当初报考中专是不是头脑发热,太亏太傻了!中专生刚出校门是有它的优势,做事麻利;但从长远看就不如大学生了。底子不足哇!即便将来爸妈把你弄回省城,起码得有一个大专文凭才行呀。好在政府开设了大学教程自修课,我们各自选一个专业自修吧,姐?”
丽娜连连点头,看着茜如慢慢睡着了。足足有五分钟光景,茜如就那么抓住丽娜的手,似乎要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幸运和力量,借助手掌间的魔力传输给对方。茜如比丽娜幸运。至少她现在在知识分子人堆里混。她深知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气质形成的影响。一个人衣食谈吐的档次全在那上面表露出来。——当然,姐妹俩从来没有正式地讨论过有关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这里面也有不好意思的成份。在那宝葫芦状的紫溪盆地……那一座爬满青藤的青砖老屋、一片逶迤葱笼的茶坡山岭……留下了茜如最纯洁的初恋,青春的欢愉痛苦,所有这一切梦幻和秘密,她永远不会开口对丽娜讲的,而丽娜,自己的婚姻遭受了挫折,当然希望妹妹获得真正的幸福;茜如在生孩子最需要丈夫呵护的时候只字不提卢西鸿,一个女人熟睡中脸上流露出来的幸福,决不是单纯到对丈夫对孩子的爱能够包容的。想着即将出世的小生命——她这个当姨妈的还不知道那个小东西是男是女呢——她对外界的议论开始觉察出不安了。于是她从茜如手掌里轻轻抽出手来,趴在病床边的小木柜上写了一封简洁的书信,犹豫半晌,这才悄悄塞进妹妹茜如的衣兜里。卢西鸿虽说固执、轻浮,但他跟茜如马上就有一个孩子了。丽娜毕竟希望妹妹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她以一个姐姐加旁观者的身份力劝茜如。
……妹妹,听我一句劝告。关于那个男人,他已经结婚了。紫溪那边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他跟你的事。那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曾对他的朋友说,他只是在玩弄你,报复你对他的背叛。男人一旦把爱情变成了仇恨,那将是很可怕的。醒醒吧!妹妹。对于失掉和不属于你的东西,过于痴心或沉缅旧情只会毁掉你自己……
很快的,又一次宫缩开始折磨产妇,罗茜如已经顾不上想丽娜的事儿了。一阵紧过一阵的痛楚之后,她和卢西鸿的儿子诞生了。
助产士在忙着给男婴的肚脐做过无菌包扎、给婴儿粗略的施洗过后,把婴儿放在一只襁褓里包好,抱过来给茜如看。丽娜这时也被允许进入产房照顾产妇。她从助产士手里接过婴儿凑举到茜如面前,快乐地喊:
“哟!多漂亮的小东西。”
茜如无力地扭过脸去看孩子,一时竟惊讶得忘记了合拢嘴巴:婴儿略宽的额头满是刀刻般的密纹,在他稍微睁开一只眼时皱纹愈加明显,小脸上密生着浅细淡黄的胎儿茸毛;而且——由于瘦小,婴孩皮肤显得干瘪巴巴的。
“怎么像个小老头儿?”茜如皱皱眉,“瞧他一头稀黄的头发……”
“稀黄的头发怎么啦?”丽娜生气地说,“他还是一个不到六斤重的婴儿呢!哎——,你瞧,他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眯缝儿,喔!他在看这个世界!瞧他的眼睛弧缝有多么长,眉眼儿长开了肯定是一对漂亮的大眼睛。”说着责怪地瞪一眼茜如:“医生说了,早产儿能够有这模样儿很不错了。不要再说那些叫人伤心的话了。”
茜如受到姐姐的奚落,只是苦笑笑。她第一眼看见这个从她身体里分离出来的小生命,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婴儿发出第一声虚弱的啼哭时,她又产生了深深的愧疚。六个月前,她跟卢西鸿之间爆发了一次大的争执,一赌气到门诊去做人流。那一刻她的心情坏透了。她的要求遭到了助产士的断然拒绝。
“你这是第一胎呀!”助产士用满含轻蔑的口吻对她的求助者说。她当然希望看到这个绯闻缠身的女人生下她的孩子。“我们不能负这个责任。”
罗茜如有些狼狈,撒了个谎:
“我吃了感冒药,恐怕……胎儿畸形。”
助产士点点头,睥睨的目光从额头到脚踝睃视一遍对方,看得罗茜如心里直发毛。据说她是个老处女,在妇产科呆长了,目睹了太多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内心里便产生了独身的念头。可罗茜如听说的另一个版本,是多年以前油泵厂一个年轻的工程师看上了她,她也对那个男的动了心,后来院方警告她,那男的出身不好,问她是要那个资本家少爷,还是选择向党组织靠拢,再后来那个痴情的男子天天傍晚在她二楼的窗户下等她,下雨的时候就打一把黑布伞在那里等。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很悲惨的。助产士入了党,她所钟情的男人最终去了另一个城市——沙市,那里有一所精神病院。在所有接触过老处女的人当中,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她的敬业精神还有她的……坚强,她总是认真负责地充满快意地去给那些愿意和不愿意堕掉胎儿的女人刮掉子宫里的赘物,坚决不放过那些企图拿红萝卜私刻公章盖在假介绍信上的未婚女子前来堕胎的丑恶行径。这会儿她肩膀斜倚在进入手术室的门框上,半信半疑地瞧着罗茜如。
“你丈夫呢?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
助产士还在说什么,罗茜如已经听不进了,找个借口溜了出来。她讨厌那个老处女喋喋不休的废话和在别人身上游离闪烁的眼神儿,听她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口吻,就像医生在处方上开过呼吸兴奋剂之后,又不慌不忙地在旁边注明“Prn.”(“必要时”或者“随时”)字样儿……也许在老处女眼里,她罗茜如不过是一头野兽,一头渴望用男人填充饥辘情肠的野兽。因为罗茜如在转身离去的一瞬,瞥见对方眼里充满了鄙薄的神情。“世界上所有最令人恶心最丑恶的字眼,此刻一定塞满了那颗无聊空寂的心灵。”罗茜如在心里用最恶毒的词语揣度着老处女。“不过,尽管如此,跟别的女人不同的是,她还有理想,还有工作热情……而不像一些女人,仅仅只是满足于身边陪有一个平庸至极的男人。”
不可否认,助产士的冷漠和拒绝最终保全了孩子一条性命。不管当时的罗茜如如何的尴尬,如何地痛恨那些庸俗不堪的、甚或戴着巴拿马睡帽满大街闲逛炫耀时髦的可怜的同类,脸上又如何地挂着类似《无名女郎》般倨傲不恭的冷笑、堂·吉诃德战胜大风车的不屑逃离了那个地方,反正现今她生下了这个小狸猫般的孩子。
卢西鸿从乡下回到妻子身边已经是十天以后了。茜如的气色恢复得跟产前一样好,抱着孩子倚靠在门槛旁晒太阳。她张开一只手掌撑遮在婴儿额前,婴儿躺在妈妈臂弯甜甜地睡熟了;经过茜如奶水的精心调养,婴儿脸上柔密的茸毛看起来柔和多了,额鬓皱巴巴的皮肤渐渐地粉嫩红润起来。
卢西鸿惊喜地脱放下肩上的挎包,蹲在妻子膝盖前,满脸的歉意。
“对不起,”他柔声地说,“你生孩子的关键时刻我却不在身边。你能原谅我吗?”
“那没什么。”罗茜如淡淡地回答,“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假话?”卢西鸿讷讷地说,“这次考核干部搞了十来个乡镇,我又是考核组的秘书,真是身不由己呀;其实,人在外头,我心里比谁都着急哩。”
“谢谢,”妻子抬头望望太阳,又埋头瞧一眼熟睡的婴儿,真诚地说:“部里的领导来看过我和孩子了;我知道你是主动请缨,我不会怪你。”
卢西鸿听罢放了心,匆忙洗了把脸又走出来,从妻子臂弯里轻轻抱过儿子,笑眯眯地端详着。“嗨!儿子多漂亮!”他忍不住嚷嚷道;婴儿被父亲的喊声惊醒,惊恐地睁开眼睛,眼珠儿不安地睃转,小嘴一撇,“哇”地哭出声儿来。
卢西鸿一边笨拙地抖弄着孩子,一边大声哄哄:
“哦……哦……宝贝别哭,等你满月了,我和妈妈带你去见当大官儿的外公,还有了不起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