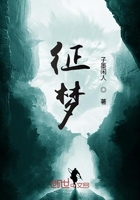连肩搭背,络手包头。疯瘫的毡裹臀行,喑哑的铃当口说。磕头撞脑,拿差了拄拐互喧哗;摸壁扶墙,踹错了阴沟相怨怅。闹热热携儿带女,苦凄凄单夫只妻。都念道:明中舍去暗中来。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刘员外分付:“今日散钱,即按户给发,大乞儿一贯,小乞儿五百文。”乞儿中有个刘九儿,有一个小孩子。他与大都子商量着道:“我带了这孩子去,只支得一贯,我叫孩子自认做了一户,多落他五百文。你在旁做个证儿帮衬一声,骗得钱来,我两个分了买酒吃。”果然去报了名,认做两户。张郎问道:“这小的另是一家么?”大都子旁边答应道:“另是一家。”就分与他五百钱。刘九儿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来分他的。刘九儿道:“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钱?你须学不得我有儿子!”大都子道:“我和你说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儿的,便这般强横!”两个打将起来。刘员外问知缘故,叫张郎劝他。怎当得刘九儿不识风色,指着大都子千绝户、万绝户的骂道:“我有儿子,是请得钱,干你这绝户的甚事?”张郎脸儿挣得通红,止不住他的口。刘员外已听得明白,大哭道:“俺没儿子的,这等没下梢!”悲哀不止。连妈妈、女儿伤了心,一齐都哭将起来。张郎没做理会处。
散罢,只见一个人落后走来,望着员外、妈妈施礼。你道是谁?正是刘引孙。员外道:“你为何到此?”引孙道:“伯伯、伯娘,前与侄儿的东西,日逐盘费,用度尽了。今日闻知在这里散钱,特来借些使用。”员外碍着妈妈在旁,看见妈妈不做声,就假意道:“我前日与你的钱钞,你怎不去做些营生,便是这样没了?”引孙道:“侄儿只会看几行书,不会做什么营生,日日吃用,有减无增,所以没了。”员外道:“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我那有许多钱勾你用!”狠狠要打。妈妈假意相劝。招姐与张郎对他道:“父亲恼哩,舅舅走罢。”引孙只不肯去,苦要求钱。员外将条拄杖,一直的赶将出来。他们都认是真,也不来劝。
引孙前走,员外赶去。走上半里路来,连引孙也不晓其意,道:“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来?”员外见没了人,才叫他一声:“引孙!”引孙扑的跪倒。员外抚着哭道:“我的儿!你伯父没了儿子,受别人的气。我亲骨血只看得你。你伯娘虽然不明理,却也心慈的。只是妇人一时偏见,不看得破,不晓得别人的肉偎不热。那张郎不是良人,须有日生分起来。我好歹劝化你伯娘转意。你只要时节边勤勤到坟头上去看看,只一两年间,我着你做个大大的财主。今日靴里有两锭钞,我瞒着他们,只做赶打,将来与你。你且拿去盘费两日,把我说的话不要忘了!”引孙领诺而去。员外转来,收拾了家去。
张郎见丈人散了许多钱钞,虽也心疼,却道自今已后,家财再没处走动,也尽勾着他了,未免志得意满,自由自主,要另立个铺排,把张家来出景,渐渐把丈人丈母放在脑后,到像人家不是刘家的一般。刘员外固然看不得,连那妈妈起初护他的,也有些不服气起来。亏得女儿招姐着实在里边调停。怎当得男子汉心性硬劣,只逞自意,那里来顾前管后。亦且女儿家顺着丈夫日逐惯了,也渐渐有些随着丈夫路上来了。自己也不觉得的,当不得有心的看不过。
一日,时遇清明节令,家家上坟祭祖。张郎既掌把了刘家家私,少不得刘家祖坟要张郎支持去祭扫。张郎端正了祭盒担子,先同浑家到坟上去。每年刘家上坟已过,张郎然后到自己祖坟上去。此年张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张家祖坟上去。招姐道:“怎么不照旧先在俺家的坟上,等爹妈来上过了再去?”张郎道:“你嫁了我,连你身后也要葬在张家坟里,还先上张家坟是正礼。”招姐拗丈夫不过,只得随他先去上坟。不题。
那妈妈同刘员外已后起身,到坟上来。员外问妈妈道:“他们想已到那里多时了。”妈妈道:“这时张郎摆设得齐齐整整,同女儿在那里等了。”到得坟前,只见静悄悄地,绝无影响。看那坟头,已有人挑些新土,盖在上面了;也有些纸钱灰与酒浇的湿土在那里。刘员外心里明知是侄儿引孙到此过了,故意道:“那曾在此先上过坟了?”对妈妈道:“这又作怪。女儿女婿不曾来,谁上过坟?难道别姓的来不成?”又等了一回,还不见张郎和女儿来。员外等不得,说道:“我和你先拜了罢,知他们几时来?”拜罢,员外问妈妈道:“俺老两口儿百年之后,在那里埋葬便好?”妈妈指着高岗儿上,说道:“这答树木长的似伞儿一般,在这所在埋葬也好。”员外叹口气道:“此处没我和你的分!”指着一块下洼水淹的绝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这里!”妈妈道:“我每又不少钱,凭拣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们葬?怎么到在那水淹的绝地?”员外道:“那高岗有龙气的,须让他有儿子的葬,要图个后代兴旺。俺和你没有儿子,谁肯让我?只好剩那绝地与我们安骨头。总是无后代的,不必这好地了。”妈妈道:“俺怎生没后代?现有女儿女婿哩。”员外道:“我可忘了。他们还未来,我和你且说闲话。我且问你,我姓什么?”妈妈道:“谁不晓得姓刘?也要问!”员外道:“我姓刘,你可姓什么?”妈妈道:“我姓李。”员外道:“你姓李,怎么在我刘家门里?”妈妈道:“又好笑!我须是嫁了你刘家来。”员外道:“街上人唤你是‘刘妈妈’,唤你是‘李妈妈’?”妈妈道:“常言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车骨头半车肉,都属了刘家,怎么叫我做李妈妈?”员外道:“原来你这骨头也属了俺刘家了。这等,女儿姓什么?”妈妈道:“女儿也姓刘。”员外道:“女婿姓什么?”妈妈道:“女婿姓张。”员外道:“这等,女儿百年之后,可往俺刘家坟里葬去?还是往张家坟里葬去。”妈妈道:“女儿百年之后,自去张家坟里葬去。”
说到这句,妈妈不觉的鼻酸起来。员外晓得有些省了,便道:“却又来这等,怎么叫做得刘门的后代?我们不是绝后的么?”妈妈放声哭将起来,道:“员外怎生直想到这里?俺无儿的,真个好苦!”员外道:“妈妈,你才省了。就没有儿子,但得是刘家门里亲人,也须是一瓜一蒂,生前望坟而拜,死后共土而埋。那女儿只在别家去了,有何交涉?”妈妈被刘员外说得明切,言下大悟;况且平日看见女婿的乔做作,今日又不见同女儿先到,也有好些不像意了。正说间,只见引孙来坟头收拾铁锹,看见伯父伯娘便拜。此时妈妈不比平日,觉得亲热了好些,问道:“你来此做什么?”引孙道:“侄儿特来上坟添土的。”妈妈对员外道:“亲的则是亲。引孙也来上过坟,添过土了。他们还不见到。”员外故意恼引孙道:“你为什么不挑了祭盒担子,齐齐整整上坟?却如此草率。”引孙道:“侄儿无钱,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块纸,略表表做子孙的心。”员外道:“妈妈,你听说么?那有祭盒担子的,为不是子孙,这时还不来哩。”妈妈也老大不过意。员外又问引孙道:“你看那边鸦飞不过的庄宅,石羊石虎的坟头怎不去,到俺这里做什么?”妈妈道:“那边的坟,知他是那家?他是刘家子孙,怎不到俺刘家坟上来?”员外道:“妈妈,你才晓得引孙是刘家子孙!你先前可不说姐姐、姐夫是子孙么?”妈妈道:“我起初是错见了。从今以后,侄儿只在我家里住,你是我一家之人。你休记着前日的不是。”引孙道:“这个,侄儿怎敢?”妈妈道:“吃的穿的,我多照管你便了。”员外叫引孙拜谢了妈妈。引孙拜下去道:“全仗伯娘看刘氏一脉,照管孩儿则个。”妈妈簌簌的掉下泪来。
正伤感处,张郎与女儿来了。员外与妈妈问其来迟之故。张郎道:“先到寒家坟上完了事,才到这里来,所以迟了。”妈妈道:“怎不先来上俺家的坟,要俺老两口儿等这半日?”张郎道:“我是张家子孙,礼上须先完张家的事。”妈妈道:“姐姐呢?”张郎道:“姐姐也是张家媳妇。”妈妈见这几句话,恰恰对着适间所言的,气得目睁口呆,变了色道:“你既是张家的儿子媳妇,怎生掌把着刘家的家私!”劈手就女儿处把那放钥匙的匣儿夺将过来,道:“已后张自张,刘自刘!”径把匣儿交与引孙了,道:“今后只是俺刘家人当家!”此时,连刘员外也不料妈妈如此决断。那张郎与招姐平日护他惯了的,一发不知在那里说起,老大的没趣,心里道:“怎么连妈妈也变了卦?”竟不知妈妈已被员外劝化得明明白白的了。张郎还指点叫摆祭物。员外、妈妈大怒道:“我刘家祖宗不吃你张家残食,改日另祭。”各不喜欢而散。
张郎与招姐回到家来,好生埋怨道:“谁恇先上了自家坟,讨得这番发恼不打紧,连家私也夺去与引孙掌把了。这如何气得过?却又是妈妈做主的,一发作怪!”招姐道:“爹妈认道只有引孙一个是刘家亲人,所以如此。当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觉,预先走了。若留得他在时,生下个兄弟,须不让着引孙上前了。况且自己兄弟还情愿的,让与引孙,实是气不过。”张郎道:“平日又与他冤家对头,如今当了家,我们到要在他喉下取气了,怎么好?还不如再求妈妈则个。”招姐道:“是妈妈主的意,如何求得转?我有道理,只叫引孙一样当不成家罢了。”张郎问道:“计将安出?”招姐只不肯说,但道是:“做出便见,不必细问。”
明日,刘员外做个东道,请着邻里人,把家私交与引孙掌把,妈妈也是心安意肯的了。招姐晓得这个消息,道是张郎没趣,打发出外去了。自己着人悄悄向东庄姑娘处说了,接了小梅家来。原来小梅在东庄分娩,生下一个儿子,已是三岁了。招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觑他母子,只不把家里知道,惟恐张郎晓得,生出别样毒害来;还要等他再长成些,方与父母说破。而今因为气不过引孙做财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来家。次日来对员外道:“爹爹不认女婿做儿子也罢,怎么连女儿也不认了?”员外道:“怎么不认?只是不如引孙亲些。”招姐道:“女儿是亲生,怎么到不如他亲?”员外道:“你须是张家人了,他须是刘家亲人。”招姐道:“便道做是亲,未必就该是他掌把家私!”员外道:“除非再有亲似他的,才夺得他。那里还有?”招姐笑道:“只怕有也不见得。”
刘员外与妈妈也只道女儿忿气说这些话,不在心上。只见女儿走去叫小梅领了儿子到堂前,对爹娘说道:“这可不是亲似引孙的来了?”员外、妈妈见是小梅,大惊道:“你在那里来,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谁逃走?须守着孩儿哩。”员外道:“谁是孩儿?”小梅指着儿子道:“这个不是?”员外又惊又喜道:“这个就是你所生的孩儿?一向怎么说?敢是梦里么?”小梅道:“只问姑娘,便见明白。”员外与妈妈道:“姐姐快说些个。”招姐道:“父亲不知,听女儿从头细说一遍。当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张郎便嫉妒心肠,要暗算小梅。女儿想来,父亲有许大年纪,若暗算了小梅,便是绝了父亲之嗣。是女儿与小梅商量,将来寄在东庄姑娘家中分娩,得了这个孩儿。这三年只在东庄姑娘处抚养,身衣口食,多是你女儿照管他的,还指望再长成些,方才说破。今见父亲认道只有引孙是亲人,故此请了他来家,须不比女儿,可不比引孙还亲些么?”小梅也道:“其实亏了姑娘,若当日不如此周全,怎保的今日有这个孩儿!”刘员外听罢,如梦初觉,如醉方醒,心里感激着女儿。小梅又教儿子不住的叫他爹爹,那员外听得一声,身也麻了,对妈妈道:“原来亲的只是亲。女儿姓刘,到底也还护着刘家,不肯顺从张郎,把兄弟坏了。今日有了老生儿,不致绝后,早则不在绝地上安坟了,皆是孝顺女所赐,老夫怎肯知恩不报?如今有个主意,把家私做三分分开:女儿、侄儿、孩儿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业,和气过日子罢了。”当日叫家人寻了张郎家来,一同引孙及小孩儿拜见了邻舍诸亲,就做了分家的筵席,尽欢而散。
此后刘妈妈认了真,十分爱惜着孩儿。员外与小梅自不必说,招姐、引孙又各内外保全。张郎虽是嫉妒,也用不着。毕竟培养得孩儿成立起来。此是刘员外广施阴德,到底有后;又恩待骨肉,原受骨肉之报。所谓亲一支,热一支也。有诗为证:
女婿如何有异图,总因财利令亲疏。
若非孝女关疼热,毕竟刘家有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