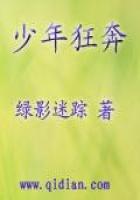张俊的遽然逝世,无疑是一大损失。假使他健在的话,四个月之后,在反抗侵略者的战争中,以董、张老搭档,他们的两支军队必然会紧密地协同作战,而且“中军翼长”还会相机调动其他各军,对全局擘划运筹,那就会给侵略军以更沉重的打击,战局为之改观也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战争中,我们看不到荣禄的全盘指挥;继任者孙万林,我们只从史料中见到他镇压义和团的记载,很少找到他率部抗击侵略军的材料。而且庚子之役之后不久,他的军队也就遣散了,在近代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
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骤然逝世于维系国运的反侵略战争爆发的前夕,实在是万分惋惜的事。它使人不禁兴起杜诗中所抒发的情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义和团反帝爱国高潮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长期以来全国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是甲午战争之后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高峰。这一运动首先发起于山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各地设立拳厂练习武术,进而设立“坛”,“坛”也是群众烧香拜神的场所,具有神秘色彩。
其领袖称为师兄,著名领袖有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他们在茌平、高唐一带领导反教会斗争,后被清朝军队镇压。1898年,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一说为李来中所提),参加的群众日益增多。山东巡抚毓贤开始对义和团进行屠杀,但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毓贤感到屠杀不是办法,另方面,他又恶于教会的猖獗,转而对义和团采取利用的态度。于是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大的发展。这就引起外国侵略者的不满,在美国的胁迫和干涉下,清廷撤换了毓贤,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果然不负洋主子的期望,带领其新军7000人对义和团进行疯狂的镇压,屠刀挥舞,杀人如麻,使山东人民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义和团有的坚持斗争,有的转移到直隶境内。
于是直隶各地“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引起更激烈的反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将率兵前来镇压的副将杨福同打死。在天津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写有“杀尽外国人,再跟大清闹”的字样。
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率众进入天津,裕禄已无能为力,不得不改剿为“抚”,对义和团以“礼”相待。清廷对义和团举棋不定,主剿与主抚的两派各持己见。刑部尚书赵舒翘奉命考察义和团之后奏称;“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待,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慈禧太后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对义和团转而采取利用态度,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等控制义和团。实际上义和团是许多支,互不统属,所以有的被清廷控制了,有的仍在自己行动,但他们爱国仇洋的热情则是一致的(尽管带有原始的性质)。六月中旬,义和团纷纷进入北京城,焚烧八面槽和宣武门一带的教堂和教会医院,继又围攻西城区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把反侵略斗争推向高潮。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在内蒙古、东北三省、河南、陕西、甘肃以及江浙、广西、贵州等地相继兴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在当时情况下,适应民族反抗情绪的一种组织形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助,它在反教会斗争中是坚决的,在尔后的反侵略军的战斗中更是英勇的,他们以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凭着血肉之躯和神秘色彩,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浴血搏斗,写下了一幕幕悲壮的战歌,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光耀于史册。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是迫不得已。用“上论”实即慈禧太后的话来说:“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这是不打自招的实话。而他们的“挽救”之法,就是先施以釜底抽薪之术,再继之以屠刀。所以清廷在尔后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处处掣肘、破坏,最终又加之以“痛剿”,直至绝灭而后已。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又出了一个怪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派,他们主张剿灭义和团,公然与帝国主义妥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他们甚至对清朝廷的对外宣战,也拒绝执行。
而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这样一来,就使得八国联军解除了很多威胁,他们可以置中国大部分地区于不顾,放心大胆地集中力量在京津一带用兵。所以,所谓“东南互保”,实际上是大大帮了侵略者的忙。
但事后,他们却被顺从洋人意旨的清朝廷目为保国功臣。是非的颠倒,一至于此!
手握中枢兵柄的荣禄,本来是反义和团的,但他处事圆滑,善于观风使舵,一味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极会“变色”。起先他在给李鸿章、刘坤一等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中曾经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因此主剿;“现在拳匪之事,惟有急治其标,……盖我自能剿,则洋兵不敢妄动”。所以,他的武卫军大多是与义和团为敌的。如袁世凯在山东,专门屠杀义和团,称得上当时的头号刽子手;聂士成的武毅军、孙万林的中军以及宋庆的毅军都接受他的命令剿杀过义和团。但后来,在慈禧太后一时冲动,要荣禄联合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他也立即遵命照办,不过暗中打些折扣而已。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即在荣禄的武卫五军中,只有董福祥的甘军没有与义和团交手的记载;不仅如此,而且有的竟是董部与义和团并肩作战的记录。有一篇《匪党蔓延京师记》中说: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即阳历六月六日)董军入都,先期由其先锋官将弁数人持令箭入京,于路宣称已命义和团拳作为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云云。闻者均为骇异。然自是之后,拳匪踪迹即已遍布都城,较前愈盛矣”。
此文作者将董军、义和团一律称之为“匪党”,其立场之反动是十分明显的。反面文章正面看,这正是董军与义和团并肩“剿灭洋人”的真实记录,而且它证明董军早在入城之前、即六月初之前,就已经与义和团合作了。看文中“闻者均为骇异”一语,说明当时这种合作,是一般官员特别是“主剿”派所不能接受的。还是上引文章中又说:
“拳匪既云集京师,更有董福祥义弟、陕人李来中,从中指挥。
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作为与拳匪无二致”。
这段文字的最后几句话,是过去一般反动作者污蔑起义者的陈词滥调,不可相信。但“兵匪遂合而为一”一句,则是实情,不过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董军与义和团合而为一”。至于这位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有的资料说他是“南人”,原为太平军李秀成的部下,后“投入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加入义和团,倡“扶清灭洋”之说(见胡蕴玉《太平天国轶史》)。他跟董福祥是不是结义弟兄,无从考证。如果他真是“南人”又隐匿于山东多年,二人无从相识,即使结义,也是当年在京郊的事。其实结义与否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传说,又进一步证明义和团与董军是亲密无间的、他们的反帝爱国立场是一致的。
大概正是义和团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激发了甘军将士,成了他们所以对敌英勇作战的一个主要因素吧!
清朝廷宣布对外作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极端仇视和痛恨,他们一再要挟清廷对义和团严厉镇压。前述要清廷以袁世凯代毓贤为山东巡抚是其中一例。此外,各国驻京公使屡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进行威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四月间,各帝国主义在大沽口外组织海军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十一国公使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团民纠党练拳,对团民首领和放纵义和团的官员要尽数诛杀。各国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也做好了登陆入侵的准备。
与此同时,约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各国“洋兵不下五百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分两批进入北京城。但这些“洋兵”在北京城远远不止于保护使馆,而是横冲直撞,开枪杀人。连清朝廷在“六月癸酉”发的“上谕”中也指出:他们“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其或任意游行,几欲闯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洋兵”在京城如此横行霸道,连帝宫都要闯入,广大群众和爱国将士怎能容忍!所以仇杀是在所难免的。六月八日(即农历五月十五日),甘军在永定门外,捉杀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据说,甘军士兵在路上捉住了杉山彬,解送大营。董福祥问是何人,回答是个书记官,董令“撒过”,士兵即推出斩杀。原来陇东口音,“撒”、“杀”同音。据此,当是误杀,否则,不会如此简单处置。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则是另一种情况。
一种记载说,克林德带领水兵向练武的拳民射击,引起甘军的愤怒。
六月十六日,当克林德又向东单牌楼巡逻的清兵挑衅时,甘军士兵当场将其击毙。另一种记载说,清总理衙门约各国使臣前去商谈,克林德先行,被瑞郡王所部虎神营士兵枪杀,其余使臣折回。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京城之内,中外之间已形成敌对状态,相互动手是难以避免的。究其根源,远因是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洋情绪;近因是洋兵入城的胡作非为,又给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义愤火上浇油。作为清政府来说,首先应该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对使馆加以保护。自己无力保护,让“洋兵”入京自卫,已属丧权之举,造成又一大错。而“洋兵”入城之后,又随意杀害兵民,那么兵民的还击,属于自卫,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总之,此时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了。
但这些并不足以使慈禧太后下定抵抗的决心。促使她宣战的,是另外的原因。原来,“百日维新”之后,她就屡屡打算废黜光绪皇帝,但要看帝国主义者的眼色,取得他们的支持才敢动手。光绪二十五年底,慈禧太后立瑞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后,令溥继承同治皇帝为新皇帝。按照礼仪,清廷立“大阿哥”时,各国使节应该前来庆贺。但各国使节都没有来,这使慈禧太后颇生醋意;但另一方面,她也从中了解到各国并不支持这件事,因此未敢采取第二个步骤。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接到外交使团让她交出政权的报告。这其实是一个谎报,她当时认假为真,触到痛处,立即恼羞成怒,作出了向帝国主义宣战的决策。十七日,清廷照会各国使馆,限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二十一日,颁布宣战上谕。上谕宣称:“与其荀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而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无论我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但之后,慈禧弄明白那不过是个谎报时,已覆水难收,只好暂时硬着头皮做下去。如此重大决策,单凭一己的恼怒和冲动,并不深思熟虑,广泛征询,认真准备,直将国家命运、人民命运视同儿戏,在这样情况下的宣战决心是靠不住的,一开始就种下了狐疑不定、首鼠两端的因子,哪里会有什么胜利的希望!但它毕竟是表面上对外宣战了,总算给了义和团和爱国将士提供了一个杀敌报国的机会。
甘军廊坊阻敌“继洋兵不下五百人”进入北京城之后,侵略者胃口越来越大。
接着,八国联军二千余人不顾清政府的阻止,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指挥下,于六月十日从天津乘火车开向北京。他们在沿途不断遭到义和团的袭击,不得不走走停停,直到六月十八日才到达廊坊。
在廊坊,他们又遭到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的坚强阻击,终于败退东返。
打这场阻击战的,除义和团外,是董福样所部马福禄的“简练军”马步七营和姚旺、董升官、马海晏等各部军队,仗打得相当激烈。《清史稿?马福禄传》中记述是役的经过说:
“五月(农历),各国联军躏杨村而西,(马福禄)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廊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
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邃却。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参与是役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记述云:
“仲兄寿三与祥率所部迎击于廊坊,择地设伏,俟敌近发枪猛击,轰毙无算。敌反击,我军散伏蒿莱间,鲜死伤者。续至各军,分两翼夹攻。自午至晡战益力,敌不支,乘火车遁。翌日往探,交绥及乘车处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此我军庚子岁第一恶战也。”
(《磨盾余墨》)两种记述,基本相同。这是伏击战、近战、拼杀战。
半天的战斗,可分三个阶段,先是马福禄设伏以待敌(覆即伏七覆,即七重埋伏)。敌人乘车至廊坊附近,大概已发觉有埋伏,故下车迎战。但马禄福掌握“敌近始发枪”的原则,这不仅是为了增大杀伤率,而且也是在敌人优势火器面前必须采取的措施。待到敌军受挫还击时,我军又以“散处蒿莱间”,使他的火力难以发扬,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然后,我军两翼包抄夹攻,就成了近战包围战。有记载说:马福禄一马当先,“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马福禄《神道碑铭》),主将当先,全体将士必然奋不顾身,英勇拼杀。至此,敌军火力的优势全失,打了被动的交手仗,自然不是,对手只好乘车而逃了。当然,我军也有些伤亡,管带张进昌战死,帮带侯玉麟受伤。们他死伤在痛击侵略者的战场上,是光荣的。
马福禄部所以有坚强的战斗力,能打胜这一仗,与平时的严格训练分不开。《马寿三总戎别传》中说:“戊戌,公统简练军马步各营旗,就粮于晋,驻防山海关、永平各处,讲求战法,勤慎操防,训士厉马,精益求精,以故士马强壮,为诸军冠。”
这次牛刀小试,使侵略军特别是西摩尔尝到了中国人的厉害。
他们从天津出发时,原以为当天即可轻松地到达北京,没想到沿途处处受阻,更在廊坊碰了这样一个硬钉子,在他们慌忙乘车东逃之际,被我军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当晚,他们退到杨村,火车又不通了,只好又改为乘船,顺北运河向天津逃窜。但水路也不平静,义和团不断给以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直到八天以后,即到二十六日,他们才在俄国侵略军的救援下退到天津海河岸紫竹林租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尔惊魂甫定,对人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
如果仗都是这样打法,哪有它侵略军的便宜可占!
董福样宫中被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