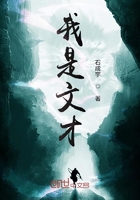曾丞相年岁越大,虽然有习武,但也难免渐渐嗜睡,春困秋乏,他变得愈发容易疲乏,长子曾嵘和次子曾峪也看出自己老爹的异样,就是不提,只将自己能做的事情都做完,生怕老爹劳累。
枫叶火红,被秋风吹落,满院红叶,几只鸟儿停息在枝干上,歪着脑袋看坐在院子里的老少二人,那憨憨模样真真惹人喜爱。
曾丞相同自己嫡孙女下围棋,仍旧是那副悠闲,不疾不徐的样子,而曾莘珠已经焦头烂额,右手拿着白色玉子,举棋不定,最后自暴自弃,随便下了,曾丞相轻轻松松获胜。
虽然明知祖父棋艺之高,曾莘珠还是忍不住鼓起腮帮子,低声嘟囔:“祖父明知我棋艺不精,还叫我对弈,欺负小姑娘家。”
曾丞相笑得高兴,伸手拍拍她头:“哪里是小姑娘家,你都快及笄,是大姑娘了。哎,嘴巴撅得可以挂油瓶啦,真小家子气,以后嫁人,该如何是好。”
曾莘珠满脸通红羞赧起,急道:“我还想再多陪陪祖父几年,哪里会那么快嫁人,祖父莫要打趣。”
曾丞相看着她小女儿可爱模样,忽然就想起从前,他的娘子,那个笑起来有梨涡的温柔女子,笑意愈发和蔼,只是眸子里却沉淀着他人难以看透的情绪。
“我家珍珠儿要嫁就嫁最好的。”曾丞相抬手将曾莘珠发髻上的红珊瑚镶东珠的步摇扶好,“祖父会让你风光大嫁,这辈子幸福美满。”
曾莘珠心不细,还和小娃娃那般,高高兴兴地撒娇:“那一言为定,祖父可不能耍赖逗珍珠儿。”言罢,便要和自己祖父拉勾勾,当真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
“嗯,祖父说到做到。”曾丞相丝毫没介意这幼稚,反而伸出了右手。
秋叶,夕阳,风从遥远的秋山吹来,能闻到山林里的露水清香,可以感觉到飒飒落叶,兔子从灌木里钻出,雪白,毛茸茸。
他能想起很久以前,真的是,在那久远的过去,一个布衣荆钗的女子,跑到自己跟前,给了他一片红叶,笑意犹如二月花,何其绚丽。
“女儿的话,就要娇养啊,千万不能跟我这样,四处乱窜找猎物,啊咧,你那什么嫌弃眼神啊,我说的是实话,若我能娇养早就娇养了,这不是家里条件不允许嘛。”
枯叶从苍穹之下飞落,落在女子眉眼如画的脸颊上,她把枯叶拿下,一掌拍到他心口。
“好好记住我的话呀,以后有女儿,要疼爱,否则,要你这爹爹有啥用,对吧?宥珲。”
她笑得肆意,无忧无虑,炫目至极,仿佛穿过五彩琉璃的蜜光,竟让曾宥珲迟迟挪不开目光。
“我们会分离的,在久远的以后。”女子坐在泛黄枯叶上,朝他伸手,连容颜都渐渐淡去,像古老的画卷,“你不会来娶我,我知道的,所以,我无法,和你永远在一起,宥珲,我说的,对吗?”
“宥珲,你忘了吗?我的名字,你很久没有喊过我名了。”
“你怎么可以忘记呢……”女子的声音轻似叹息,她双手交叠在膝上,稍稍抬头,长裙落了枯叶。
狂风大作,红蝶振翅而飞,犹如浴火重生,那色泽,竟是同血凝固般,艳丽无比,骨架则是深夜幽暗勾勒。
红蝶飞过他的双眸,一只白皙的手从女子身后暗处伸出,骨节分明,指尖葱白,曾宥珲睁大了双眼,却无法挪动身子分毫。
女子浑然不觉,那鬼魅红蝶最后停在纤细指上,黑暗悄然来袭,却能看见立于暗处的人,茶白裙裳,一双眼眸,阴冷如雪,就直直盯住曾宥珲,令他感觉到冷冽刺骨的寒意。
“你会后悔的。”她笑了,另外一只手搭在女子肩上,女子的面容,顿时如碎裂陶瓷般裂开,化为碎片,“你迟早,会后悔的,因为这是命,不是你的,始终不会是你的。”
“你失去了妻子,然后失去女儿,很快就失去所有,那是你种得因,苍天自有道,因果轮回,你逃不过的。”
红蝶碎落,狂风猛地席卷而来,将所有景物吞噬殆尽,化为灰烬,幽暗之中,只剩下那声预言,久久不散。
——“你逃不过的,曾宥珲!”
曾丞相蓦地睁开双眼,冷汗湿满襟,他看见窗外晨光熹微,黑色树影爬上大半屋子,枝干摇曳。
只是梦而已,曾丞相按按眉心,虽然是这么告诉自己,可还是觉得有些心神不宁,那场梦太过诡异,以至于他醒后还无法回神。
曾丞相的发妻,乃一户落魄书香门第的女儿,姓叶,闺名绯虞,名字取得文雅归文雅,实际上本人却非那回事儿。
彼时大洐才经历过天灾人祸,皇帝到处赈灾,忙得脚不沾地,无奈曾宥珲的家乡实在太过偏远,赈灾赈不过来,大家饿得都米开锅,叶绯虞家里没落,早已无往日之风光,于是她爹娘也不拘小节和那些老祖宗规定,教闺女打起猎,不止身为的次女的她,叶家长子长女都已打得一手好野味,以保全家伙食。
曾宥珲认识叶绯虞时,叶绯虞八岁,性子早就歪得山水十八弯,表面十分能装得温婉乖巧,背地里,只要曾宥珲惹她不开心,随时一脚踹过去。
曾宥珲很不开心,他家贫苦,却还是叫他学文习字,所以对叶绯虞说:“你这样哪里有个女儿家模样!”
叶绯虞吐吐舌,做鬼脸:“要你管,反正我长得还算人模狗样,肯定能嫁的出去。”
这话说得理所应当,理直气壮,气得曾宥珲差点没顺过气,把自己气晕过去。
二人两小无猜,虽然非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那样美好,但关系还算好,好吃好喝的,都会留一口给彼此,免得大家双双饿死,到时候没伴,多么无趣。
叶绯虞总嫌弃自己的名字,她说:“弟弟认字,听见我名,就留着口水跑过来问我说我是不是鱼。”然后捂脸,痛心疾首,“你没瞧见他馋成那样,两眼放光,就差没扑过来把我啃一口。”
曾宥珲只好将刚刚烤好,涂了果子的烤鱼分给她,并提醒道:“你的虞,是虞美人的虞,不是小鱼儿的鱼,想吃东西就直说。”
“胡扯,我是这样的人吗!”叶绯虞恶狠狠咬一口香喷喷的烤鱼,“而且名字取得再好听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吃不好穿不暖,我今儿个给弟弟再捉几条鱼回去,免得他把我给咬了。”
曾宥珲见豪爽啃完鱼,没个女儿家模样就气得跳青筋,干脆用自己袖子抹她脸上去:“你非得吃得满脸都是吗!”
叶绯虞还特厚脸皮点头,把他手拍掉后就着他袖子擦脸,那叫一个淑女,可怜曾宥珲又差点背过气。
尽管嘴上不承认,但两人关系,确实很好,曾宥珲知道叶绯虞每个小情绪,委屈了,痛了,伤心了,哪怕不说,也能准确感觉到,然后臭着脸,把自己做的好吃的凶巴巴塞给她,叶绯虞就嬉皮笑脸,欣然接受。
他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下去,两人小吵小闹,哪怕吵架,第二日,叶绯虞也会别扭地去找自己捉鱼,然后再重归于好。
只是,很快,曾宥珲天真想法就被事实给打破。叶绯虞家里子女众多,岁数都太小,她十三岁那年,终于成功长成了一只含苞待放的花,虽然在她眼里自己依旧是人模狗样,没什么出挑,但别人不这么以为啊,看小姑娘水灵灵,歪心就起了。
一户屠户提着一两百钱和猪肉,到叶家提亲,不是要娶长女,而是次女叶绯虞,因为长女漂亮得过分,早就给临城富商定下做妾。
叶家没落,叶父看着自己孩子们日日吃不饱,狠下心,便准备解下,被叶母用砂锅砸了过去,把屠户砸出家门。当日两夫妻难得大吵起来。
叶母原本身子不好,是个药罐子,没法子做点女工补贴家用,以至于累得女儿都只能上山打猎谋生,可无论如何,她也不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屠户,叶父虽万般不舍,但苦于生计,又想让妻子吃点还要,才会肯,无奈妻子根本不懂他心中之苦,两人才吵得面红耳赤。
最后,叶绯虞跪下来抱住叶母,一遍又一遍说,别这样,别这样,我嫁,我嫁人了,家里才有好日子。
叶母抱着女儿痛哭,为命,为这没法过下去的日子,还为自己苦命的女儿哭。
曾宥珲独自坐在院子里,听着隔了一面墙的叶家闹得天翻地覆,终是无言。
第三日,曾宥珲在山上看见许久未露面的叶绯虞坐在枯叶里,抬头,望着远处的天,听到动静,就低头,看他,笑得恣意,梨涡深深。
他们说了很多,几日未见,更是想念。
但曾宥珲不会承认自己很想叶绯虞,叶绯虞也不会承认,他们就是这样,嘴硬别扭,永远没坦诚之时。
说到最后,两人都沉默了。半晌,叶绯虞忽然就问:“宥珲,你会娶我吗?”
“……”曾宥珲盯着自己满是茧的手心,许久没有言语。
叶绯虞就笑了:“我胡说的,嘛,我就知道你讨厌我,肯定不会娶我过门,以后别见面了,我快嫁人了,就是上次来我家提亲的。你看,虽然你很讨厌我,但我还是很抢手的。”
他们分开,各自回家,曾宥珲环顾家里四壁为空,爹娘饿得瘦弱,擦擦眼泪继续做事。
叶绯虞最后还是没嫁人,叶母在夜里上吊自杀,临死前对叶父说,我死了,大家才能吃点好的,看在多年夫妻情分上,对儿女好些,别让他们过的凄凉。
而后,叶家长女因为被那富商正室打压挤兑,承受不下去,投井自尽,叶父痛苦,叶家连办两场丧事。
第二年,天灾终于过去,百姓日子终于好转起来,叶父打拼出事业,在即将过世前,去问曾父,多年好兄弟,把自己女儿说给他儿子当媳妇可好。
曾父含泪,叫他别担心,他们曾家会好好照顾叶绯虞。亲事就这样定下,叶绯虞嫁给自己竹马曾宥珲,洞房花烛夜时她问他:“你真想娶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介意退婚的,还有人想娶我呢。”
曾宥珲一吻她蹙起的眉心,说,叶绯虞,你嫁给我,是你这辈子的福气,好好给我感恩,别想其他人。
后来,这句话并没有成真,因为,叶绯虞跟着曾宥珲的日子,很辛苦,他要走仕途,没钱没身世没地位,俗称三无。
哪怕曾宥珲写得一手好文空有一身才华,但你穷,就没法上京,叶绯虞为他上上下下的跑,不知憔悴多少,凑够了钱,终于可以让他出发。
临行那一日,叶绯虞头一回亲了他,对他说:“我会等你回来的,你定要回来,否则我就改嫁,哼。”
曾宥珲哭笑不得,好好的离别,硬生生弄成叶绯虞闹小性子。
考秀才路途漫长艰辛,他后来因为得罪户有钱人家,生生和家里断了联系,叶绯虞苦等五年,没等到他中秀才,反而听闻他死在上京途中的假话。
曾父过世,曾母已老弱,叶绯虞生的极好看,无奈家徒四壁,只好做点其他正经活赚家当。
当年被拒绝的屠户如今财运亨通,便又起歪心眼,想强抢了叶绯虞,叶家曾家就那点小生意,被打乱,弄得又成以前那样揭不开锅。
叶绯虞呆坐在院子石凳一夜,看梨花落尽,第二日,屠户上门,叶绯虞拿起匕首将自己了尽。
曾宥珲终于得以中状元,青云直上之日,回乡,而那时叶绯虞进了黄土,红颜薄命,莫若于此。
叶绯虞在给他的遗书里些道:“我不相信你死了,那都是别人胡说,希望我断念头而已。
当初你离开,我跟你说,你不回来,我就改嫁,其实那都是骗你的,我这辈子只嫁一次,嫁给你,便此生相随,夫妻情分,至死不渝,如今先走一步,也只是我太累了,你无需介怀。
老天爷爱开玩笑,兜兜转转,你我缘份终尽,但望你能记住我,永远把我记在心里头,哪怕日后,你娶妻生子,有更好的日子,也希望,你可以在年迈后的某日,想起我们曾经的岁月。”
叶绯虞的一生太短,短得曾宥珲没来得及拥抱她,给她最好的日子,最好的生活,让她衣食无忧。
叶绯虞多年不离不弃照顾的曾母,在曾宥珲面前,哭得肝肠寸断问,你为何不早回来,为何?如今绯虞死了,什么也没了!
曾母从此变得痴呆,看见谁,都要念叨一句,绯虞是我好媳妇,可是,我好久没见她了,她在哪儿呢。
很多年后,曾宥珲娶了个女子,眉清目秀,梨涡浅笑,和叶绯虞十足的像,连名字,都何其相似,叫叶绯渔,曾母很高兴,拉着她手,喊着绯虞,绯虞,我的好绯虞,你要生好多大胖小子。
不知情叶绯渔羞答答应了,当然,她到死才知道,自己只是因为曾宥珲要拉拢朝中权利,而且模样与亡妻异常相似,才娶的她。
曾宥珲不后悔,甚至没半点愧疚,在他一路坎坷,当上丞相时,他回头看,再没有哪个女子,能让他动心,除了那个没心没肺的叶绯虞。
可惜她死得那么早。如今曾宥珲,当今两朝元老曾丞相望着窗外,枯叶四飞,想起的,还是当初坐在枯叶中笑得梨涡深深的好看女子。
曾嵘上前一步问:“父亲,何时动手?”
“就今日,午时。”曾丞相把茶盏放下,淡淡答道。曾嵘领命,退出去。
曾宥珲叹了口气,整个人都靠着梨花木椅,无数次,在心中喃喃:绯虞,我本来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本来。
边关出大事时,莉言换上女儿装,混迹在清越城的名门闺秀中蹭点心,然后悠哉游哉回府午睡。
鹰珀听到影卫来报,五皇子重伤难以救治,必须暂时送回帝都,六皇子被一箭射中,生死不明,他犹豫着是否要告诉莉言此事,直到午睡醒来的时候过了许久后,鹰珀觉得奇怪,去屋子里看,却发现莉言心口蔓延出大片血。
但赶紧叫来暗中随行的女祭司,那女祭司花了整整一日,才将莉言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奇怪的是,她的伤口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刺穿,却没在房间里找到类似暗器。
莉言醒来后,虚弱许多,听鹰珀提起过边关之事时也只是叹口气:“劳你去安排一下,我是时候该回府了。”
鹰珀觉得她反应平淡过头,但思虑到可能人家小姑娘被人莫名其妙暗伤,心里不大痛快的缘故,就去叫人备马车。
待鹰珀出去后,莉言抚着心口,垂下眼帘,轻声喃语:“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六皇子被箭射下马,还是一箭穿心,按理而言,应该死了,奇怪的就是,六皇子不见了,就在边关战场上。
满朝文武听罢,哗然一片。
那日,皇后将手中药瓶里的药,全倒进了池子里,眼神暗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