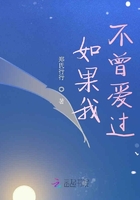行之眉心跳了跳,稳住手,把茶盏丢桌上,探身去看榻上的莉言:“丫头,你刚刚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莉言仍旧厌厌的不说话,就望着被光照得发亮的窗棂,黑眸幽深,没有尽头。
芙霜给她把脉,疑惑道:“跟之前的脉象没什么区别啊。”
陈少傅捋捋白须道:“行之,是不是你又捉弄我们了?多大岁数人,还玩这些有的没的吓人。”
行之会口技,早些年,皮得很,跟着外头的口技先生学来捉弄人的,当时铭天宗里绝大多数弟子,都他耍过。
行之简直委屈得跟朵长在苦瓜尾巴的小黄花一样:“滚犊子,我好久以前就没再用口技了,而且方才那话,真不是我发出的。”
芙霜想想,说:“兴许吧,我瞧他自从被随月狠狠揍过一回后,便禁了,好多年没耍人。”
“指不定他就突然起兴子玩我们呢。”陈少傅按按眉心,白高兴一场,“随月都不在那么多年,早就没人能治住他。”
芙霜佯怒道:“师傅都说了,叫我们别在行之面前提起随月,你提起随月就算了,还说他的往事,简直是在人背后戳伤疤,随月肯定心疼极了。”侧目就给自己九师弟打眼色。
陈少傅颔首,了然道:“我省的,不过师姐你方才一口一个随月随月,比我还要过分,而且还说了三次,这样着实不好,行之再怎么没心没肺,听到随月的名字,还是会很伤心,别再说随月。”
行之终于没忍住骂道:“……你们这帮混蛋。”
芙霜这回可来气:“谁混蛋啦,小十你简直学坏不学好,只怪师傅和随月太惯着你,惯出一身臭毛病,换作我,当年就把你揍成猪头三。”
反正她就是认定刚才那声是行之发出来逗大家的,以前自己被阴过,留下太深刻印象。
况且,如今什么节骨眼上,芙霜自己都不确定能否让莉言快点醒过来,日日夜夜得焦虑起来,行之踩在她最烦躁的时候简直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所以师姐你非要提随月那丫头吗?而且从来都是我让她的,她曾几何时惯过我啊。”行之气恼道。
陈少傅给自己师弟一个你自求多福的眼神,便去看莉言,反正他已经顺着师姐话气行之,剩下的,皆看师姐,他就不再管那边吵得水深火热。
“姑娘,你听得见老臣说的话吗?”陈少傅一面把着她脉象,一面轻声问,“听见便回老臣一句,可否?”
见她没有反应,又道:“应了,老臣便叫六殿下给你带南香楼的糕点,听说南香楼出了许多点心,你还没来得及尝尝对吧。”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姑娘闻言抬抬眼,睫毛轻颤。
陈少傅想,果然,姑娘贪嘴的毛病十年如一日。
半晌,小姑娘动动唇,似乎说了个什么字,大抵旁边太吵,她声音又沙哑,所以听不清楚。
陈少傅皱眉,轻呵一声:“四师姐,行之,够了!”
两人被他这吼给震得没敢说话,面面相觑,怎么突然间就发火了。
陈少傅转头,轻声道:“姑娘,再给老臣说一回你方才说的话。”
小姑娘脑袋有气无力耷拉着,暗色绣花枕头上,发丝乌黑,衬得那张脸愈发惨白,像个死人,嘶哑如干涸枯河的声音在安静下来的房屋中,低低响起,犹如年过半百的老人叹息般:“雪……”
芙霜和行之各自交换眼神,对那个字表示不解,毕竟如今压根就没下雪,雪早在一大早便停了。
会是跟莉言在湮寂那会有关吗?芙霜摸摸下巴,沉思起来,但这想法很快便被推翻,要知道,她被“杀死”的那日,是炎夏。
行之走过去,伸手摸摸莉言脑袋,也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丫头,乖,再多说点话,先生给你买糕点吃。”
陈少傅站起来把窗子打开些,外边确确实实没有雪,院子里,白茫茫一片,天清澈得,犹如洗过般,如此纯粹,让他忽然想起,多年前,莉言和翁墨规站在一块,穿的那身蓝衣裳,笑靥如花。
那个小姑娘,似乎疲惫得,马上,便会昏昏欲睡,嘴里还喃喃着:“雪……”
陈少傅蓦地,有种不详的预感:“四师姐,快!”
芙霜还在困惑,听到自己素来沉稳聪惠的师弟急急一喊,似乎想起什么,吓得直接冲过去。
电光石火间,却已来不及,莉言突然间,咳出一大滩血来,双手死死攥住毯子,喘不上气般,浑身颤抖。
血浸湿了白绒绒毯子,暗红,盛开,满目苍痍,她抬头,眼里是无尽深渊。
“哥哥呢?”莉言战栗般,抓住身旁行之袖子,枯骨似的手,指节泛白,染上暗红血迹,“我要……见……哥哥……”
她说的断断续续,十分吃力,眉头一皱,又狠狠咳起来,血从指缝滴下,落入男子青色衣裳。
行之顾不得自己衣裳,扶住莉言,拍拍背,给她顺气:“听话,丫头,先别说话,师姐,你快给她看看。”
莉言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气,仿佛下一刻就会窒息,却执着道:“我、我要见哥哥,他在哪儿……”
芙霜过来给她点穴,才点到一半,小姑娘推开行之,发狂般挣扎起来,将榻上的软垫全扔向他们,三人武功底子好得很,轻松避开,软垫摔在地上,只是闷响。
“咳咳咳咳!”莉言咳得全身发抖,右手抓住软榻边,血从口中,不断咳出,旋即染红地毯,“哥哥、哥哥呢?”
她无力喃喃着,明明痛苦得要死,但就是,不断重复问,哥哥,我的哥哥在哪儿。
她想见他,见自己的兄长,可其他人,并不懂。
芙霜一个眨眼,冲到莉言跟前,手如疾风,飞快点中几道穴位,小姑娘身子软了软,没撑住,险些摔在地上,幸亏芙霜反应好,及时抱住,否则人家小姑娘之后就算好得利索,也非破相。
“这是怎么回事?”陈少傅趁芙霜将莉言放入软榻时问道,“好好的,为何就成如此。”
“我也疑惑,你问我,我问谁。”芙霜没好气道,搭上她手腕把脉。
行之半天才道:“莉言有兄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是孤儿啊,而且据我所知,她爹娘就生了她一个祸害。”
芙霜把毯子卷起来,丢到旁边,然后将莉言抱回屋里,掖好被单,叫木檀红芍收拾软榻,让竹青给莉言擦身,毕竟那血,留在姑娘家身上,怪吓人的。
忙完后来三人坐在大堂里,喝着茶,芙霜放下茶盏,揉揉眼角道:“我听闻莉言在湮寂,暂住在一户人家里,便认了个哥哥,其实这也没什么,最重要的是,东宁城,刺客来袭,当中,就有那个人。”
陈少傅捧着茶,半天,不晓得该说什么好,这两兄妹,再见面,竟是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身份,着实尴尬。
行之挑眉:“总不可能,她哥哥,把自己妹妹给捅了吧?那会儿,莉言可没受伤。”
“是啊,据我所知。”芙霜撩眼,笑得几分古怪,“人家兄长没捅死她,她倒是先下手,把哥哥砍了,就是没砍死,重伤而已。”
行之:“……”他也不晓得该说丫头什么好了,你说,把人砍后,又一直念叨着人家,几个意思。
陈少傅对此不说想法,就问:“你说人没死,那她兄长如今在哪儿?”
芙霜撑着下巴,收敛起笑意,望向地上那描百鸟展翅的地毯,道:“在六殿下手里,六殿下说,刺客竟然敢找上门伤人,就要自己审问,不让影卫插手,所以我也不晓得他近况。”
行之倒来了兴致:“六殿下当时吃了不少亏吧,非得泄恨一回,唉,我看他估摸着没多少气了。”
陈少傅对自己教出的弟子,脾气秉性如何,他自然清楚,堪忧道:“确实麻烦啊。”
“麻烦什么,又不会真让莉言看见那个人。”芙霜对他们神情凝重起来,觉得好笑至极,“莉言病着,哪里能再受点刺激,待她好后,什么事也记不得,一了百了,要我说,六殿下把那人解决才好,省得惹出麻烦。”
芙霜也没什么好心肠,她从前可是影卫出来的,若非年岁渐长,厌恶起,过刀风剑雨日子,才递了卷轴,请宗主把自己调去炼药阁。
退一百步讲,芙霜哪怕是个好人,也只会对自家弟子,外人如何,生或死,与自己无关。
很冷血,但很稀松平常,因为,她早已看淡人命,看淡世事。
行之听罢,没有半分犹豫赞同道:“是这个理,不过,这件事,要跟六殿下提提吗?”
“自然要提,要么叫六殿下下令把人给解决掉,要么请他,将人,给我们铭天宗自己处理。”陈少傅知道六皇子帮皇上做事后,手早就不干净,但还是希望他少沾人命,“我兴许没办法见到六殿下了,你们寻个空,趁他在府里,就把这事给办了,永绝后患。”
“行,我记得。”芙霜点点头,答应得痛快。
三个人,把人命,看得很轻,很轻,仿佛杀死别人,无法只是动手一捏的事。
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发现,其实铭天宗的所有人,都冷血,都无情,因为,他们早已在腥风血雨中,过了大半辈子,手里全是血。
哪怕是宗主,哪怕是德高望重的长老们和大长者,甚至莉言,都已经,从鬼门关中,从三途川旁,走过一遭,没有当初那般干净。
很可悲,但也极正常,没有人,能一辈子不沾血,不染尘,你或者,就是罪。
莉言一直没能看透这道理,从五岁到十三岁,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毁得差不多了,只因,看得不够透彻。
这一夜,莉言没有睡好,反反复复的咳血,时而抽搐,时而昏睡,芙霜照顾她很久,弄得自己也未睡好。
直到,五日后,六皇子姗姗归来,还带着五镜城的小点心,给竹青,叫她先送去蔓娪院,自己洗漱后,才去见莉言。
那日已有些乌云,莉言大抵好了些,坐在榻上时,至少没再咳血,只不过比平常还要困倦。
木檀分了点心,给芙霜医女送去,芙霜看着玉碟上精致糕点,略一思索,带着药箱,就匆匆赶到蔓娪院。
六皇子已经坐在暖和里,翻着清王府近日来的账单本,红芍小心翼翼用银勺舀了一小块赤豆糕,喂着莉言。
小姑娘闻到淡淡桂花香,侧目,盯着银勺上,松软赤豆糕,张张口,乖巧地吃下去。
翁墨规瞥她一眼,压压上扬的嘴角,接着翻账本。
芙霜对此,并没有多大感觉,从善如流坐在绣墩上,接过木檀递来的碧螺春。
“六殿下,臣有事想对您说。”如今芙霜是宫中医女,自然得称自己为臣,“这大抵有些逾越,能否叫其他人先下去呢,还有,望殿下听后,不要发火。”
翁墨规余光中扫一眼,还在慢慢吃糕点的莉言,颔首,算允了。
芙霜笑得端庄娴雅,拿过红芍手中的银勺和赤豆糕,自己喂起莉言,小姑娘睁大空荡荡的双眸,动动鼻子,闻闻她身上的味,没有什么反感,便继续吃。
莉言这人,病后,迟钝了许多,可是鼻子倒愈发好使,这也算值得欣慰之事。
芙霜一勺一勺慢慢喂着,笑道:“我们宗门里的姑娘,都是顶好的,可惜,生来命运坎坷,六殿下可知,阿言,有位兄长,无血缘关系,却是早些年在外头迷了路,落入户人家,拜的兄妹。”
翁墨规翻书的手一顿:“嗯,然后呢?”
“东宁城,想必六殿下记忆犹新吧。”芙霜笑笑,对六皇子皱起眉头,冷哼一声,置若罔闻,“那时候,不是有个刺客只受了点皮外伤,没有死吗,臣估摸着,便是他了。”
翁墨规木着脸道:“哦,所以?”另一只手拿起手帕,给莉言擦擦嘴边的点心残渣。
芙霜倒觉得六皇子小家子气了,无非就是那人是刺客,没准砍过他而已嘛,至于吗,便道:“臣要说的事,便有关那个刺客。前些日子,就五日前,姑娘咳血咳得厉害,还说出几句话。”
翁墨规把手帕漫不经心丢桌上:“好端端怎么咳血了?”
“血气上涌,大抵是心急了,身子又没养好回来,一时受不住,才咳血。”芙霜拿起红枣桂圆枸杞茶给莉言喝,轻描淡写道,“索性无碍,咳咳血,当把毒排出来,留在身子里也不是事儿。”
“所以,你们想如何处置那个刺客?”翁墨规看着莉言惨白无神的脸,沉默一会儿,才问道,“他确实在我手下。”
芙霜露出浅浅笑意,跟之前在行之面前那副母老虎不同,温柔得,像只披上朵朵花影的蛇,莫名地,让人觉得脊梁骨发寒。
“六殿下您都说他是刺客了,既然是刺客,那便有属于解决刺客的法子,不必来问臣。”
芙霜将莉言落发别好:“臣依旧是那句老话,我家姑娘,可再经不起,半点折腾。”
话说到这份上,其实,已经无需再讲下去,翁墨规又不傻,自然知道芙霜出自铭天宗,心多多少少,偏着莉言,也明白那话里头的意思,当即便颔首。
芙霜把养颜补血的茶往旁边一搁:“陈少傅早前回来看过姑娘,可惜身上还有要事,没法子等六殿下回来,便先行离开,六殿下海涵,莫要责怪。”
“陈少傅教导本皇子多年,此等小事自是无需追究。”翁墨规对此真没什么意见,他对陈少傅要做的那些事,略有耳闻,“不知少傅大人如今可好。”
“当然,六殿下不必挂心,大人会照顾好自己。”芙霜笑笑,没有坦白,反正老九除了日日被曾丞相派出的追兵给追来追去,中点毒外,也就没什么了。
她本来想给六殿下说说的,可惜之前陈少傅就嘱咐过,这点琐事,没必要太多知道,免得连累别人。
芙霜心里头,还是看着自己九师弟,他说得话,自有他的理,她就照办便好。
“行之先生呢?”翁墨规看看四周,自打自己回来后,就没瞧见先生踪影,难道还没回府?
芙霜轻咳一声:“行之?他啊,看完姑娘,便说自己有事,跑到外边继续游山玩水,让臣给您托句话,说斩草要除根,否则春风吹又生。”
翁墨规扬眉,笑了笑,觉得第一次,与自己素来不对盘的行之先生,终于不谋而合。
“劳医女你帮我看着莉言,我去处理些小事,很快回来。”翁墨规把那本厚厚账本放下,伸手,将莉言发绳理好,而后才离开,步子沉重。
芙霜笑得温柔,叹气:“到底,你还是遇见个好友,肯给你出口气。阿言,虽然不知那人究竟是好是坏,但你真的不能见他,否则,又该伤心,别怨师叔我们,我们只想让你平平安安过下半辈子。”
那个小姑娘,抬抬眼睑,终是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