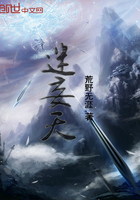说来也怪,几刻前天还好好的,晴朗蔚蓝得让人赏心悦目,怎知天突然就变了,乌云浓黑近似万古深渊,缠绵万里,黑压压的,阴沉中无声无息里散发出压迫感,大抵是天生异象太古怪,百姓乃至平日忙着种田的农夫也不好出门。
阡陌小路两旁的树木已生出嫩芽,但此时阴沉得很,以至于那柔嫩绿芽都无精打采。一阵轱辘声由远到近,深棕色皮毛的骏马后是看似平常的车厢,车厢光滑的繁复雕花木纹精美绝伦,绝非普通木匠能细心雕刻出来,而单单只是打量那些木质,便觉得十分珍贵,可又讲不出是什么木头,这些都静静表达出厢里的人是拥有怎样的富贵。
赶车人是个约摸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双鬓已见雪白,一声朴素却又不简陋的淡色衣裳,两只手苍劲有力握着缰绳。车子行驶得不快不慢,让马车少有颠簸,可见他赶马车技术之好。
男子瞧了眼天,他眼角早有皱纹,浓眉里掺了几丝白须,皱起来时额头甚容易堆起一层又一层的折痕,颇为踌躇后,才低声问车厢里的人:“这天或许过不了多久便会下雨,您可还要过去?”
车厢里传来低沉的一声“嗯”,便没了其他回响。
他倒有耐心继续道:“主子您前几日染上风寒,昨儿个才好,如此舟车劳顿,对身子怕是不好,带刀侍卫都已经先赶过去了,即使现在到那也没什么打紧事,您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莫要累坏。”
“徐伯。”车厢那人的声音虽是带着几分稳重和惫意,但却毫无疑问是个还尚未褪去稚嫩的男孩声音,“纵使带刀侍卫再有能耐又如何,他带走的是谁,什么身份,你晓得的吧。”
徐伯一下就闭嘴不言了,他身份低,却也经历过几次风浪,这次带主子出来早就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呵,被带走的人,尽管是个黄毛小姑娘片儿,背后那座大山除了皇上太后,没人惹得起,可就是有如此望而生畏靠山的小姑娘偏偏就被劫走了,若非伏璧城中安排了探子,恐怕到现在都不知。
“既然我们有安排探子,那么铭天宗会闲着吗?他们到现在都装作什么事情皆未发生,只不过是给足皇家一个面子罢了,倘若没有救出她,估计,事情会发展到难以收拾。”
男孩儿话刚讲完,徐伯便不禁感觉到脊梁骨渐渐蔓延出冷寒,缰绳一甩,赶紧认真赶起路。
铭天宗是国宗,国宗代表什么?即是为民祈福,为国求安,当然也必须保卫天子的平安以及训导出人才,除此之外,它素来最重视未满岁弟子的安全,甚至立下宗规传承下去,若有不知好歹者胆敢侵犯到宗规,那么后果,非死即伤,反正定以悲惨收场,这是众人皆知的。
“人活着,说来不长也不算短,所以总要做一些蠢事。”
霓轻忘记是谁这么讲来着,但她现在算是明白那话的意思了,敢身为绑架铭天宗弟子的她,如果没有抱着谋朝篡位遗臭万年的准备,就说明他早经活腻才来挑战权威,亦或者,那人只是个脑子有问题的富家公子哥。
她被自己跳跃得跟锦鲤跃龙门有一拼的想法由心表示深深地无奈,原来自己竟已如此无聊没事做。于是干脆乖乖不躺了,方才听到脚步声,也许是有不请之人到访,否则护卫绝不会如此匆忙走路,既然如此,那么护卫忙于对付外人时定会留下空隙。
机会来了!
连衣服都没有闲情打理,她翻身下床,从自己贴身衣袋中掏出一个似火折子般的东西,可它外层却为温润白玉,玉纯白无暇,厚实得绝不可能轻易摔坏,霓轻眸子里倒映出的不是玉珠,而是犹如狂风暴雨下翻滚的滔滔江海。这次,就看这次,如果能成功跑到院外并且脱逃成功就用不着这急召令,如果不能,立即用内力点燃它,以“空迹”的本领,半柱香都无须用便可集合完毕来救她。
紧紧握住急召令一会儿,又缓缓松开,仿佛充满勇气和决心似的,霓轻将它收好,把长发稳稳挽好,没有留下任何一丝发丝,又从床板底下抽出偷偷藏了许久的匕首,匕首乃玄铁打造,尖锐无比,真可谓削铁如泥,若护卫上前阻挠,斩!
仅仅时年七岁却有此番破釜沉舟心思,直教人感叹。
霓轻轻轻推开房门,木门发出低低的吱呀声,却没有任何人突然出现像往常般挡在自己跟前,她咬住下唇,破罐子破摔走出房间,微弱午光洒落于肩,足以媲美漫长黑夜里的一道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