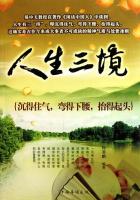由旬虽然温和待人,但武功造诣上,还是不给宗门里的师傅和空迹丢人,怎么说都身为小字辈大师兄,自然要有些尽量。
一招秋风扫落叶,险些将莉言后路断掉,也亏得她机敏,往旁边避过,顺道向苏格丟暗器,以保周全。
她虽打得兴奋,但理智还在,知道不往墙那边躲,而努力朝宽阔地方去,免得连逃跑都跑不了,生生被人逼到死角了就真玩完。
苏格套路,以强硬、速度为主,半点不给人留活路,加之又会暗器,莉言光对付他就很吃力。
这会子,苏格单刀劈下,莉言一个旋身闪开,右手接过佩剑,向他挥去,姑娘的剑柔韧灵活,似水蛇般,苏格用没扔掉断剑挡住,她嘴角微扬,却直接挑开了。
苏格料想过如此,但没想过当那把佩剑刀身抽到他手腕时,震得他手直发麻,才不禁松开了,而莉言长剑勾起向上挥去,断剑便飞到半空中去。
由旬感觉眉心跳了跳,他就趁此机会冲过去,莉言还记得这人在旁边,暗器由左手飞去,直击他空门。
她虽是女儿家,可力大无穷,和苏格完全有的一拼。由旬和她对过几招,自然心里头清楚,不敢懈怠。
握紧长剑在面前划开十字,玉簪花银尖头碰撞到剑刃,“叮”的一声响,颇为清脆,玉制的花瓣,碎落满地。由旬暗自咬咬牙,觉得手一阵生疼。
天啊,之前那个温柔小师妹呢?她从前没有此怪力,几年不见,简直力大如牛呀,苏格前辈怎么和她打下去的,由旬又好奇又心疼自己师妹,毕竟苏格是男子,小师妹还是个姑娘家,难免吃亏。
鹰珀点了止血的穴位,将簪花拔出来丢到脚步,用随身带着的绷带捂住胸口,看见由旬纠结成那样,恨铁不成钢喊道:“什么时候了还走神,回去后你们俩肯定会给宗主揍!快去帮苏格,你没发现他快就快被砍死了吗。”
由旬这才提剑继续杀去。
苏格青筋一跳,这小子能不能把嘴巴闭好滚到墙角里蹲着,每次开口,非得惹人嫌。
莉言见状,便吃吃笑了,但是没听出多少笑意,佩剑流光忽闪,绕过苏格,直接劈向红墙,竟划过一道长痕,她手旋即又往上挥去,墙壁便垮下半块,往苏格那头掉落。
古怪的是墙裂开时,并无太多声响,他只是感觉到头顶上忽地暗沉,转头看去,三人高的墙已塌落一小半。
连久经风雨多年的苏格都不禁睁大了双眸,忘记该去做什么,而他余光中,瞥见那个小姑娘茶白衣袖,点点血红逐渐渲染开,再往上看,嘴角弯弯,她笑意浅浅,唇畔生花。
轰隆一声巨响,墙直接砸在地上,溅起满地落雪,灰尘滚滚。由旬已经傻在原地,鹰珀也不例外,他们就讲几句话后转个头,墙就突然垮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到他们还没反应回来怎么了。
由旬用袖子挡住口鼻,退后几步,大声喊道:“前辈?苏格前辈!”
鹰珀站得还算远,只感觉灰飞漫天,实在呛人,但没有殃及到他,可尽管如此,他仍觉得一阵心凉。
“莉言,你疯了啊!你知道残害同宗门弟子有什么下场吗?不管到底是有意无意,最后只有死罪,那可是死罪,没人能保住你。”鹰珀吼完,喉咙一天,半口血就咳出来,落在雪里,墨红得显出几分可怕。
莉言定定看着他们,又看了眼还没散去烟尘的墙塌之处,脸上平静如常,而后转头,握紧手里佩剑,头也不回走了。
鹰珀咬牙:“由旬,去追莉言!别让她跑了,再继续这样,她迟早酿成大祸,到时候真会一发不可收拾。”
由旬站在原地,只短短犹豫一瞬,便赶紧追上去,鹰珀前辈拜振源师叔为师,医术高明,他是知道的,这里交给前辈,最好不过。
至于阿言,真的不能继续错下去,否则,覆水难收,她哪怕没事,可铭天宗规定从不会为谁破例。
出发前,一个空迹问宗主,若突发情况,莉言失手做出什么事该如何?
宗主对他们说了:“倘若莉言真违什么事,纵使那丫头有千千万万合理的解释说辞,但只要弟子没错,她何来这资格弑同门弟子,违令者,斩!没得商量。”言罢,拂袖而去。
由旬回想起此事时,脸色渐渐冷下来。
镂水剑擦着地面,发出尖锐刺耳声,火花隐约可见,莉言猛地回头,面前便溅起半人高的雪,她皱眉,脚步顿住,以剑护前。
白雪升起,又即将落下,然,雪中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小姑娘在手中微微抬高,那东西便破空而来,刀风凛冽!
男子黑衣如夜,剑刃雪亮,似长河千里冰封,而他眸子里暗沉,雪从发鬓边擦过,衬得男子脸色愈发惨白,仿佛没有血色,像打磨得发亮的白玉子。
如此好看的男子,是自己的师兄,那个在从前悠久岁月里,温柔待她的师兄。
莉言嘴角扬起笑意,在纷飞雪花里,她容颜渐暖,没有之前那般面无表情,冷淡对人,微垂眼睑,掩去眸子里万般情绪。
“咳咳咳——”苏格一脚踹开塌壁,左肩袖子被扯开大口子,袖下血淋淋的,估摸着是擦伤,可他却并不在意,只是看看四周,问道,“莉言和由旬呢?”
鹰珀扶着墙站起来,松了口气:“莉言跑了,我让由旬先去追,你怎么样?还能撑下去吗?”
苏格皱起眉头:“该死,你这回真是笨到家看,赶紧去阻止。”
“由旬是有分寸之人。”鹰珀又点了自己几回穴道,运好内力,跟他一块赶过去,只是手还有捂住胸口,“何况莉言是他小师妹,他没可能下狠手。”
苏格干脆骂了句:“白痴,我怕的,不是由旬没分寸,我担心的是,莉言她想不开。”
“哈?”鹰珀觉得风太大,他耳朵似乎出问题,莉言想不开是指哪方面,动手杀了她的大师兄由旬吗?
“你没注意到莉言左手开始流血。”苏格虽是问,但语气极为笃定,“宗主说过了,内力失而复得之人,往往会伴有极大的副作用,莉言身子本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枯竭了,刚才我和她交手时候便发现不对劲,她没可能有那么大力气和如此好功夫与反应,甚至可以放到我们空迹,劈下高墙。”
除非多年练家子,内力浑厚,才能做得出这些事,而她一个小姑娘家,多年不动武,怎么可能办得到。
鹰珀失声喊道:“她完全恢复内力了!”
“对,这下糟糕透了。”苏格终于看见远处那两个身影,一黑一白,格外打眼,他赶紧加快脚步,“镇忆琐玉,大抵已经,压制不住她内力。”
鹰珀抿嘴不言,觉得天要垮了,而且垮得十分严重,很有可能把大家给压死。
“而且,我刚才看见,她忽然笑了。”
鹰珀还没来得及问那是什么意思,苏格突兀停下,害他没及时停住,撞到这家伙肩膀,差点没把咽下去的血再吐出来。
“你干什么……”鹰珀抬头,话说到一半,却震惊地讲不出来。
茶白衣裙的小姑娘站在雪地里,腹部犹如血花舒展开花瓣,何其妖冶美丽,她平静站着,嘴角噙着笑意,浅似春风化雨,好像只要一眨眼,便会消散,双手垂在身侧,佩剑落于她脚边,刃上点点血渍。
由旬整个身子都僵住了,手里还握着镂水剑,脸上只剩讶异,慌张,他动动口,艰难吐出几个字,却是哽咽:
“阿言……”
莉言静静看着他,眼里含了淡淡笑意,平日里一贯的神情:“嗯,我在。”
我在这里啊,什么事也没有。
所以,别露出和梦魇中,那些人,在昏暗光下,看她的神情好吗?真是,太令人讨厌啦。
由旬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忘了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甚至,忘记身处何方,只闻到,萦绕在面前,浓浓的血腥味。
刚才究竟发生什么?由旬不断问自己。
他很愤怒,然后,用师傅教他的破空直刀八式,想要从背后袭击,趁其不备拿下她。
莉言已经转身看见了,但从头到尾,她都只是看着,没有闪躲,只随手挡下些许,由旬心里咯噔一声,想收回,可是,他的一刀,依旧刺入她的腹部。
这不对!这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由旬慌乱起来,预料中,莉言本该可以轻松避开,他会伺机闪到旁边用手刀打晕她。
但是,莉言根本没打算躲,从头到尾,包括雪飞起来时,她看见自己,眼里甚至没有多少惊讶,只有平静。
为什么会这样。
莉言缓缓抬起手,抓住镂水剑,笑意仍旧浅似云烟,唇瓣红艳,是被血染红的。
她开口,语气极是平稳:“杀了我。”
由旬睁大双眼,低头去看她,看自己的小师妹。
“帮帮我,大师兄,杀了我。”
莉言的眼神已经开始有些涣散,似乎空荡荡一片,眼里倒映不出由旬的身影。
“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苏格重斥一声:“由旬,她会失血过多而死的!”
由旬这才回过神,莉言却空出另一只手握住他,他这时才发现,原来莉言手很冰凉,还轻轻的发颤,不由去看她。
莉言仍是镇定,仿佛平日里说话般,只是放慢许多,每个字,都很轻:“大师兄,你最疼我了,帮帮我吧,将我杀了,什么事都会落幕。”
由旬觉得胸口莫名闷得很,不忍挪开双眸,避开她腹部鲜红:“阿言,你还是执迷不悟。”
鹰珀和苏格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然而莉言只是看了眼他们,浅笑安然,让人莫名心安。
可,下一刻,莉言突然抬起手,对着由旬肩膀,便是重掌一击,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砸到肩膀,隐约听见什么闷响,似狂风迎面冲来,连脚步都不由自主往后连退。
镂水剑被他紧握在手里忘了松开,他退后的那瞬间,由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血随着锐利长剑飞扬,那些凝结的血珠红艳如花,在半空中盛放,绽开,没一粒,皆艳丽得刺痛双眸,带着热意,落在他们神情诧异至极的脸上。
由旬跌坐在地上,血沿着他的脸颊,缓缓滑下,白玉脸,妖冶红,在冰天雪地里,透出几分旖旎。
“阿、阿言……”
由旬不敢相信看着她,看她笑靥如花,看她面色平静,眼眸似海,淹没了所有思绪。
莉言直直站在雪上,身子早已麻木,恍恍惚惚间,仿佛看见翁墨规,他坐在地上,神情痛不欲生。
她很想伸出手拂去他皱起的眉头,可是根本没有力气,费力动动唇,轻声道:
“别害怕……”
别害怕,墨乌龟,我从前跟你说过的,祭司又很多,没了我,也会有其他人来辅佐你。
别害怕,你日后会有许多友人,亲人,你将过得很开心,渐渐地,就会把我忘记了。
所以,不必害怕,别露出那样的表情。
没有任何人能永远陪伴自己,唯一能做的,只有适应,适应孤独,适应寂寞与长久岁月,而后,才能强大。
莉言很想对翁墨规这么说,她知道墨乌龟同小孩子一样,又固执又别扭,虽然暴躁,其实很怕独自一人,所以才拘着自己在王府,担心自己离开远走。
因为她这个人呀,从来都随心随意,自私自利啊。
如今再想想,心里最放不下的人,竟然是翁墨规,莉言笑了,笑得恬淡,身子一沉,眼前天旋地转,再也没有任何景色。
唯有那个撅着嘴闹别扭的少年,从脑海里,一闪而过。
啊啊,最后想的,是这家伙,倒是不值呀,还以为能想起大洐万里江山呢。
茶白衣裳的小姑娘倒入雪地里,血从腹部慢慢爬满身下整片白雪,染红了纯白。她闭着双眸,嘴角微扬,似乎还含了笑意,脸色渐渐苍白,乌黑发丝便紧紧贴着脸颊。
鹰珀给她把脉,脉象十分虚弱,又去探她鼻息,也是微不可测,余光里一撇,便看见她左手全是,略微迟疑顿了顿,还是将袖子撩开,这一撩,却吓人得很。
莉言左手本就白皙,但从手腕开始,便突出十几条黑色青色的经脉,显而易见,若定睛细看,还能看见它在跳动。
又撩开另外一边的袖子,发现也是一模一样,瞧着便怪可怖。
苏格皱起眉头问:“这是怎么回事?”
鹰珀将袖子拉下盖好她的手:“内力毫无预兆,突然恢复后导致的,经脉尽乱,又没好好调息,所以此时此刻在她身子里四处游走,太危险了,赶紧带她去元辰长老那里。”
鹰珀本想抱她起来,但无奈他自己也是个受伤失血,苏格身强体壮,啥事都没有,便打横抱起莉言。
“当心点,她如今情况不大乐观,路上再磕着碰着,估计人就这么没了。”讲句老实话,鹰珀根本反对苏格抱她,苏格什么人?那叫一个不懂何为怜香惜玉,无奈由旬没个谱,他也只能让步,“你先过去,我和由旬后面再到西进院。”
苏格没应,嫌他嘴巴太烦太聒噪,抱着莉言就用轻功跃上墙壁,向西进院赶去。
鹰珀摆摆手示意由旬跟上:“还傻愣着做什么?出发了。”
由旬呆滞地拾起落入雪里剑的,目光落在镂水剑上斑斑血渍,没有应声。
“你不必感到愧疚,莉言就是这样的家伙,做事出其不意,半点不顾我们其他人的感受。”鹰珀拍拍他肩膀劝道。
半晌,由旬才开口问:“前辈其实,也很害怕对吧?”声音,都在发颤。
“这是自然,害怕乃人之常情,你别看苏格镇定得跟什么似的,其实差点就给吓到喊出声。”鹰珀收回手,叹了口气,“我原想安慰你,但我觉得,我并没有那本事。”
因他自己很恐惧,尤其是那血,飞扬出来的那一刻,他仿佛重看到当年,她坐在血地里,朝他们伸出手,笑得可怖。
他也需要有人安慰,来开导,所以没办法去劝由旬要看开。
由旬捂住额头,咬着下唇:“我从前总想着,要帮身在外边的弟子,免他们收到伤害,你看阿言,倘若那年,能及时获救,如今也不该是今天这副模样。”
“所以我才执意加入空迹,就只想守住自己家人而已啦但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阿言她是毁在我手上的。”
如果没有拔剑相向,如果自己再细心点,再厉害点,是否,她便不会被刺中,一切会往好的方向走去。
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这一说。
鹰珀只摇摇头:“你也发现了吧,莉言她根本没意愿活下去,所以才挨下你那剑而已,这是她做出的决定,我们没法阻拦。”
“等到镇忆琐玉将她往事给封住,内力镇压好,莉言会恢复成往日那般。”
这句话,鹰珀说得很轻,像是对由旬说又像是对自己讲。
由旬咬咬牙,跟着鹰珀一道赶去西进院。他们到时,其他几位影卫也到了,便拜托他们将被莉言放倒的两位空迹带回来。
苏格给元辰长老打下手,叫进屋里,门外的天月女司发现鹰珀受伤,就顺手帮他疗伤。
天月女司看看他伤口,有些觉得奇怪:“你这伤,瞧起来似乎很重,还有些许中毒的迹象,但实则根本没那么厉害,就放了点血而已,过几天就会自己好。”
鹰珀自己也察觉到,想了想才问:“那毒呢?”
“估摸着是自己做的毒药,没多毒,但里头麻药倒是很多。”天月女司将手洗净,用帕子擦干,“你要庆幸,虽然并非什么剧毒,可倘若人家真下狠手打在你胸口,不要半个时辰,你定翘辫子。”
由旬闻言,沉默许久。
天月女司发现他的古怪,便问道:“谁对你下手的?”未免仁慈,就是手段太小孩子气。
鹰珀抬头笑了笑:“莉言。”
天月女司叹气:“果然,那孩子是个好的,但……”话讲到一半又咽回去。
鹰珀对此,也不接话。
因没规矩管着,他们三人坐在房门外,各怀心事,没多少心思说话,安静得很。
影卫回来时还带着昏迷不醒的两名空迹,天月女司都给把过脉,安排间厢房叫影卫抬他们进去。
当中影卫道:“六皇子打发人来催,问为何莉言还没回蔓娪院,还有,那边被莫名其妙劈开的墙,是怎么回事。”
天月女司端起茶盏问:“六殿下消息怎听得如此之快。”
影卫如实答道:“他自己有安排眼线在王府里头,六殿下近几年,早已不是我们能瞒的。”
“今回再锁住莉言内力,恐怕十分棘手麻烦,今日估计都回不去蔓娪院,你叫人将消息堵死了,别给六殿下听见分毫。”天月女司这次,是被宗主和元辰长老授权管事,所以此刻便吩咐道,“我们铭天宗的事没皇上准话,还是不必告诉六殿下,若他再问下去,就说莉言看见长老欣喜得很,暂时要陪长老,所以在西进院里头住着,何时离开还没个定量。”
影卫颔首出去了。
天月女司不禁再叹气,这回可糟糕,本以为力六殿下应不管莉言见长老这件事,谁知道还会来催,按六殿下性子,他看重莉言,她重伤之事,被他得知,非过来算账不可。
“由旬,你……”天月女司按按眉心,话刚说出口,却被“哐啷”一声打断了。
突然,屋里又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吓得他们立马站起来。
“怎么回事?”由旬看向天月女司。
他们来得晚些,根本没看见莉言情况如何是好本以为有元辰老者在,事情坏不到哪里去,但听这动静,似乎不容乐观。
“别急,要我们出手帮忙的话,苏格和长老会出声的。”天月女司示意他们别轻举妄动,“锁住内力这件事本来就凶险,出现什么副作用,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