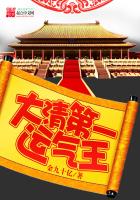那男人朝他挥了挥手,君原就恭恭敬敬的退下了,只见妖冶男人看向窗外,眸中跳跃着嗜血的光芒。
在云良恍恍惚惚转醒之时,宋景卓正一脸复杂的看着她,云良立即警惕的坐了起来,“你是何人。”
宋景卓一手抱拳,半跪在地上,“我这一生征战沙场,从未求过任何人,只求姑娘帮我一个忙。”
云良惊讶道:“你就是宋景卓?”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着他。
宋景卓以为云良是顾及他的身份,便急忙解释道:“姑娘,我并没有以权压人的意思。”
云良想起阿栈给的纸条,开口说道:“大叔,你可是认得我?”
宋景卓起身看着她,“姑娘,此前我并不识得你,可今后你就是我的女儿,宋唯情。”
云良错愕的看着他,“你,你在说些什么,我怎么会是你的女儿。”
宋景卓眼神复杂的看着云良:“孩子,你所担负的是一个世家以及王朝的兴衰,有些事情,谁都无法选择,这就是命运。”
云良揭开被子,起身就往外走,“我不信命,我就是我,我听明白了,你说我是你的女儿不过是你的一个幌子罢了。”
宋景卓急忙拉住她,“孩子,你别急着走,有的话我还没说完呢。”
云良气愤的甩开他:“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凭什么要去做别人的棋子。”
宋景卓沉声开口:“那姑娘你可是认得一个叫阿栈的人。”
云良回头看着他:“什么,你认识阿栈?”
宋景卓点着头,“孩子,你也不必太过紧张,是他让我务必留下你的,守护你也是我的使命,而且他告诉我,你一定会乐意帮我的。”
云良疑惑道:“什么?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宋景卓回答道:“他说了,一切的真相都将由你去揭开,你难道不想知道你是谁吗,你难道不想找到你彻夜辗转的原因吗?”
云良心中一震,又转而冷静道:“阿栈所说,我自然是信的,可你呢?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宋景卓指着云良脖子上挂着的玉哨,“就凭你这迷迭笛,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云良秀眉紧蹙,拿起那枚玉哨,“迷迭笛?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宋景卓回答道:“姑娘,这迷迭笛会去寻找自己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就是容家家主的命定之人。”宋景卓看了云良一眼,这孩子的眼中流露出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冷静。他又接着说道:“历任家主都有一世劫,也只有命定之人可以保其性命助其渡劫。”
云良看着宋景卓,没有说话。
宋景卓见她没有说什么,便接着说道:“姑娘,现在你要做的是,忘掉之前的身份,重新开始。”
云良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给我三天时间准备,我会把一切安排好,再来寻你。”
宋景卓开口道:“此地只是暂居,姑娘去往将军府寻我就好。”
云良微微点头,扭头走了出去。
她从马厩中牵来一匹马,沿着河沟旁的小路渐渐走远。
“张品,蒋晋呢,骆宸来过了吗?”云良一到霖园就急忙问着。
“回姑娘的话,小侯爷一大早就出城了,王爷此刻还在宫中。”张品显然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何事。
“都不在啊,那你帮我转告骆宸,我已经找到我要找的人了,此刻就启程离开上京了。云良再也不会回来了。”云良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脸平静。
张品倒是听的心惊,“这,姑娘还是等王爷回来亲口和他道别吧,我...”云良打断他的话,“不必了,有些事情说不了太清楚。”云良一边说一边向外走,那声音轻的像一片羽毛,瞬间也就飘远了。
云良漫无目的的走着,本来想好好道个别,可老天爷偏偏不给她这个机会。
突然她的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上马,直走到德馨街良居,我在里面等你。”是传音入耳!没想到,这容笙居然有如此功力。
“驾!”云良骑着马很快就到了德馨街,那良居两字笔锋凌厉,字字入目,虽说不是鎏金大匾,但也格外有气势。想来这题字之人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云良提起裙摆走进了良居,这里面看起来不过时文人墨客吟诗诵歌,喝酒吃茶的风雅之地,并无其他独特之处。奇怪的是,那些个书生模样的人并没有因为突然闯入的女子而受到影响。
“云小姐,请随我去采杏厅。”一个掌柜模样的人恭敬的开口。
云良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惊讶,只是轻声嗯了一下便跟了去。那院子中有一颗两人高的杏花树,孤零零的立在那里。
“云姑娘你再往前走个几步就能看到采杏厅了。”那人恭敬的行了一礼没等云良回答就转身离开了。
云良嘎吱一声打开了门。她一进去就看到容笙背对着她站在那里,“你这四方庭院,中间一颗树,这是个困局啊。”
容笙回过头笑道:“什么困局,不过是想藏住一个人,困住一颗心罢了。”
云良盯着他看,没有说话。
“适合你的功法不好寻,这几天我一直在找...”云良打断了他的话,“你是这良居之主?”
“嗯,你要是没地方去了,可以来我这里。”容笙避过她的目光。
“住在哪里都是寄人篱下。”云良的心里有些憋闷。“你呢,你帮我可是有什么目的。”
“没有,为什么要有目的呢,你是我的朋友,我当然可以帮你。”容笙笑着回答。
“如果我想要离开,你会帮我吗。”云良的眼圈有些泛红。
“当然。”容笙轻轻的拍着她的肩膀。
“算了,我说笑的。”云良吸了下鼻子问容笙:“你给我找的什么功法啊。”
容笙拉着云良,“走,我带你去看。”容笙走向书柜,把手伸进装画轴的瓷瓶中摸索了一会儿,只听咔嚓一声,书柜移动了一下,容笙把它推开,拉着云良进去了。随后那门又自动关上了。这地方都不能叫做密室,这些白玉地砖,鎏金壁灯,奢华而又不失高雅。只见容笙拿出了一只竹简递给云良,那上面还有这隐隐约约的符文,像是尘封了很久的样子。
“这功法的年代太久远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记录它的名字。”容笙解释道。
“管它叫什么呢,我何时能够练呢?”云良兴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