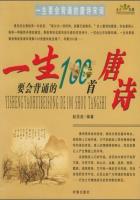从审美意识上看,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具有明显的泛现代主义特征。他们反对形成某一固定的现代主义形式,而鼓励在现代主义大旗下作各种有益的探索。从《无轨列车》开始,泛现代主义审美意识开始萌动,①到《新文艺》时期这种意识日益强化,并体现在外在的文学行为上。在1929年版的《新文艺》杂志上登有一则关于丛书《现代作家小集》的广告,他们计划同时出版横光利一的《新郎的感想》、显尼志勒的《牧人之笛》和劳伦斯的《二青鸟》等。由此可知他们当时的审美情趣不仅仅倾向日本的新感觉派,而且也与西方的意识流、象征派、未来主义等多种现代主义流派相关联。到1932年施蛰存办《现代》杂志时,这种泛现代主义审美意识达到了高度的自觉。施蛰存在《现代·创刊宣言》中明确表示,《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自觉的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这表明他们虽然大力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在创作上进行艰难的试验,但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固定的现代主义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泛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纵观《现代》一至六卷,我们不难发现它对国外现代主义流派与作品的译介相当广泛,如意象派、后期印象派、精神分析主义、象征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日本的新感觉派等。在《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上的《美国文学专号·导言》中,施强调:“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的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显然,他反对专门模仿、学习某一国家或某一种倾向的现代主义文学。他所看重的是反传统与自由创造这一现代主义文学的共性。不仅如此,施蛰存还通过自己的编辑倾向,向读者和文坛昭示自己的泛现代主义意识。他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组《意象抒情诗》和小说《将军的头》,之后,他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了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和意象派似的诗歌,于是便在一卷六期的《编辑座谈》中反对文坛只朝这两种倾向发展,希望中国出现多种形式的现代主义作品。这表明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具有一种自觉的泛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与追求。
注释:①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28。
那么,他们当时何以会形成这种泛现代主义审美意识呢?我以为原因有三。其一,他们当时的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还不可能建构起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主义理论体系。其二,这种泛现代主义审美意识与“五四”文学传统不无关系。“五四”文学高举“打倒偶像”、“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倡艺术的独创性,这些对后来者主要的启示是反传统、反因袭的独创精神与宽容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不可能只因袭某一种现代主义传统,而必然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其三,这种泛现代主义审美意识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即从整体出发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影响了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只可能对西方各种现代主义作整体综合,领会其普遍存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西方各种现代主义进行细致入微的辨析。所以,他们虽体悟出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精髓,却无法真正深入某一种现代主义思潮,更无法真正辨认出各种现代主义之间的细微区别。这种直观的思维,对于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从创作内质上看,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作为其审美意识的对象化,具有泛现代主义特征。
首先,从1930年代现代派创作群总的创作倾向来看,他们虽然基本走向相同,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但不同作家的风格各不相同,我们不可能用某一种现代主义流派特征来概括他们。刘呐鸥1930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其中的一些作品是师承日本新感觉派的探索之作,它们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作品的出现。继刘呐鸥之后,穆时英创作出了某些更适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新感觉派作品,从而被誉为“中国的新感觉派的圣手”。所以从创作的一种倾向上看,称刘呐鸥、穆时英为新感觉派,大体上是准确的。但是,如果继续沿袭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观点,将施蛰存也纳入新感觉派,便与史实不符。施写小说“最早受影响的是奥地利的显尼志勒”,①对日本新感觉派作品,他并不感兴趣。1933年他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就否定了自己是新感觉派。他的小说主要是在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下的一种心理分析小说。②1930年代现代派的其他作家也各具特色,如叶灵凤可谓是中国特有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别具一格。所以,我们泛称1930年代那些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家为现代派而非新感觉派是符合文学史实的。
其次,从具体作家或作品来看,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具有泛现代主义特征。一方面,同一作家往往兼具多种现代主义流派的因素,我们无法用某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去指称其全部作品。譬如刘呐鸥在译介横光利一等人作品的同时,对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等现代主义也极感兴趣。他当时的文艺观是极为复杂的。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并不尊于某一派,虽然他更喜欢“象征的新感觉派”,③并写出了一些新感觉派作品。但是,他的整个创作却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泛现代主义特征。《残留》是一篇十分地道的中国式意识流作品,全文写未亡人“我”的性意识流程,有对往昔幸福的追忆,有对丈夫昔日温情的再体验,有对恋人的性透视,更有对未来性生活的推论、期待与羞愧,风格上不同于他种现代主义。《游戏》写都市人的人生游戏。作品中的都市并非客观的写真,而是作者对现实都市的瞬间印象,表现的是声、光、色变幻中的整体氛围,具有印象主义特证。而《风景》的主调则是对现代都市女性的讴歌,具有反文化的倾向,在风格上近似于未来主义。另一方面,同一作品往往也兼具多种现代主义特征。如叶灵凤的《第七号女性》既有海明威简单明快的个性,又有新感觉派对直觉、瞬间感觉捕捉的特征,同时还运用了《尤利西斯》中那种写无意识活动时不加标点的方法。我们很难说它属于那一具体流派的作品,但必须承认它是一篇地道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小说。
再次,从文本总的精神内质看,由于对意识流、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的广泛综合,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具有泛现代主义特征。也就是说,它拥有西方多种现代主义流派共同的精神特质。
注释:①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75。
②施蛰存:《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62。
③刘呐鸥:《色情文化·译者题记》。
其一是对于现代都市人逃避孤独与恐惧的表现。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人物,大都处于一种精神无所依傍的孤独、恐惧状态。“夜总会里的五个人”、“ModernGirl”、蓉珠、刘有德等大都生活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都市,是一群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他们“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的,或是全部的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①孤独、恐惧是他们性格光环的底色。不过,这种孤独、恐惧又不同于传统文化下小农式的孤独,它是1920、1930年代都市文化派生的一种新的市民心理,其根源在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宗教、人与人这四重关系的崩溃。譬如《旅舍》中的丁先生神经错乱,对他人对自我均感到怀疑和恐惧,其原因在于都市竞争中人际关系的险恶。这些人正如穆时英在《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中所坦露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这种由信仰崩溃而来的孤独、恐惧,正是一种泛现代主义情愫,所以在对孤独、恐惧情感的认同上,中西现代主义小说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孤独、恐惧的具体描写上,1930年代现代派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性。他们笔下的人物不象西方小说家如卡夫卡、萨特等笔下人物那样,对孤独、恐惧本身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与认识,没有迷恋于孤独、恐惧的情景中深入体悟自我存在的意义,很少进入形而上的境界。相反,这些人物在意识到自我的孤独、恐惧处境后,便设法逃避孤独与恐惧。而且人物的逃避方式也没有西方式的精神探索性,他们只是在夜总会、酒吧间、电影院等场所放浪形骸。他们似乎只有在灯红酒绿的闹市中,在肢体的扭动中,在原始的性本能的发泄中,才能逃避孤独。勿须讳言,他们这种驱除现代孤寂、恐惧心理的方式与西方现代派相比确实显得较为肤浅,但我无意指责他们,因为这种不敢面对孤独的行为,这种逃向群体以摆脱孤独的方式,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①
注释:①穆时英:《公墓·自序》,《南北极·公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75。
其二是对人生游戏的表现。这些孤独的都市人,难以在逃避孤独中发现本身的价值,于是,只能以游戏人生取代对孤独的体验,在游戏人生中作践自我与他人,放逐对自我与社会的责任感,消磨时光几乎成为人生惟一的目的,从而由孤独的失败者演变为社会的多余人。刘呐鸥的《游戏》对都市人游戏人生的表现最为典型。它写一对个性解放的都市青年,似乎相爱了,但又无法真正进入对方世界。于是在“探戈宫”里寻找刺激。但同时,她心里想的却是自己并不爱却甘愿嫁予的未婚夫。她不同于“五四”时子君式的女性,没有任何外在的势力阻止她选择志同道合的伴侣,她是自由的、幸运的。然而,她并不珍惜历史赋予她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不像子君们那样视爱情婚姻为神话,而是将一切视为游戏。“个性解放”意味着一种孤独,一种人格的实现,但她却害怕孤独.不惜一切方式去摆脱自由孤独的处境。她自由地选择了没有爱情的丈夫,以诙谐的方式解构了“五四”青年爱的神话,将神圣的爱情不着痕迹的演化为情爱游戏。自由带来的孤独没有将她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相反,使她在匆匆摆脱孤独的努力中跌入了游戏人生的误区,从而真正与自由无缘。这可谓是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中女性的一大特征,类似的作品有《方程式》、《礼仪和卫生》、《夜》、《黑牡丹》、《被当作消遣的男子》等。
注释:①参见邓晓芒:《灵之舞·作为外在表演的人格》,东方出版社1995,83~152。
其三是对生命的偶然冲动与遭遇的表现,且呈现出两个基本的情节模式。第一模式是写某一对男女的偶遇,在简短的对话后作爱,然后不留姓名地分手。刘呐鸥的《风景》、徐霞村的《英雄》、穆时英的《夜》、施蛰存的《宵行》、黑婴的《帝国的女儿》等均属此类作品。他们之间只有一时的媾合,没有灵魂的相遇,只有当下的言行,没有性格发展历程,他们不愿思索,更不善于思索,所以他们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都市文化符码。另一模式是写人物的意识或无意识的偶然冲动。施蛰存的《四喜子的生意》写车夫四喜子拉着外国女客时潜意识的突然勃起,使他企图强暴车上的外国女客。刘呐鸥的《赤道下》写“我”与土著人菜茄偶发的性行为,“这行为,这激情的来源我自己是不懂的。我只知道我心窝里有海一样深的孤独,而她是我这时惟一的对手。一切都在狂奔的无意识中经过了”。这一模式的特点是注重对人物潜在心理的分析,所以人物在性格上与第一模式中的人物不同,他们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内心独白是他们存在的一种主要方式。他们的性格变化虽没有太多的外在逻辑可寻,但性格的偶然变化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
其四是对生命矛盾性的揭示。《怀乡病》、《赤道下》、《夜叉》、《旅舍》、《热情之骨》、《风景》等,无不表现出了人物在现实中无法摆脱的矛盾情绪。在他们的感觉中,都市的快节奏是那样地富有魅力,他们仿佛依恋母亲一样依恋都市,但都市并不像母亲一样给予他们爱与希望,而总是令他们失望,让他们做荒诞的游戏。他们一面对这种游戏感到厌恶,另一面又认为它是合理的,认为生活本该如此,因而常常处于矛盾的煎熬中。而且不只是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如此,许多历史题材作品所揭示的也是生命的矛盾性。如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表现的就是历史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它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其中,“《鸠摩罗什》,宗教和色欲的冲突;《将军的头》,信义和色欲的冲突;《石秀》,友谊和色欲的冲突;《阿褴公主》,种族的冲突”。①这些历史题材小说,是对叙事的叙事,但已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叙事文本。在对叙事的再叙事过程中,作者看取的是人物性格中的矛盾,是原有叙事中所蕴藉的冲突性。他是从自己的心理感受出发,将古人现代化、自我化,借古人古事写自我,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心态。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的,“我们每个人也有一部个人的历史,我们自己生活的叙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②施蛰存正是通过这些历史故事抒写自我复杂矛盾的心灵世界。以上我们分析了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所揭示的生活与历史中的矛盾性内容与主题,那么这一内容与主题走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一方面应归之于作家对现实的矛盾态度和作家的矛盾人格。1920、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历史的主潮与暗流不断地冲击着每位进步的青年,使他们在看取社会历史,确立自己的人生追求时常常充满着矛盾。穆时英在谈到自己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情绪时说:“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许多人
非难我的原因。这矛盾的来源,正如杜衡所说,是出于我的二重人格”。①在另一场合他说:“我是过着二重,甚至于三重、四重......无限重的生活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②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人格,它与麦克法兰所概括的现代主义公式:“‘亦此/亦彼’以及/或者‘或此/或彼’”③,在精神深处是完全吻合的。这种矛盾的二重人格在1930年代现代派作家中具有普遍性。④另一方面与作者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广泛吸收亦有关系。西方现代主义流派中有对机械文明歌颂的,也有向往自然厌恶都市文明的,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将这些糅合在一起,必然加剧他们思想上的矛盾,并最终影响其创作。另外,生活本身的矛盾性也决定着现代主义小说的内容取向与主题走向。
注释:①《现代》1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