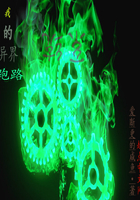黎明前的黑暗终于过去,肆虐了一整夜的风雪归于停顿,当萧郎睁开眼,一缕温暖的阳光打在脸上,看到洞外的冬日红彤彤的太阳,他有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接着他感觉身体有点热,低头看到兰珠的俏脸伏在自己胸膛,她像孩子一样地睡着了,表情很奇怪,眉头微皱,可是嘴角却有一丝笑容,好像刚经历一场让她痛苦又让她幸福的选择。
他慢慢抬起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喂,你好吗?”
她睁开了眼,看着近在咫尺的萧郎面孔,声音有些朦胧,“我们还活着吗?”
萧郎不解其意,只是茫然地点点头,她眼角滑下一丝泪水,把他抱得更紧,可是萧郎此时因寒气带来的伤口麻木已经消失,她一用力,被冰箭穿破的内伤立时剧痛起来,他呻吟了一声。
“怎么了?”她再度紧张,掀开盖在身上的衣服想看他伤得怎么样,然而一掀开她又紧张地盖上,她忘了两人都是赤身裸体。
萧郎也看到了,看到她已经脸红到脖子根,隐约记起她所谓的男女大防,小心地问,“我们……能这样吗?”
她忽然把头深深地埋进他臂弯,低声哭泣,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身体接触,她明白自己已经不得不属于他了,如果说第一次她还有过杀死萧郎永保秘密的念头,可是现在她明白连心都被他掳走了,昨夜的经历,让她明白了即使自己死亡也不想他受伤害的少女情怀,她已经爱上他了。
听着她的哭声,萧郎莫明其妙地忘记了伤疼,对昨晚他还有些依稀的记忆,他知道她昨晚为自己做了怎样的牺牲,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就像动物之间的安抚一样,他低头吻着她的面孔,舔去她脸上的泪,手臂不知不觉用力地抱紧她。
她有点喘不过气来,可是又乐意他这样抱着自己,萧郎感觉到她姣柔的身体慢慢在怀中发热,动情地把腿缠上自己的身体。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与这个雌性动物偎在一起,让萧郎想起在森林中见过的一些动物原始的求偶仪式,他心中响起一种声音,就像公狼在求偶期那种不安狂燥又极为期待地吼叫声,这声音让萧郎身体某个敏感的地方涨得发疼,一种不需要指引而且又极为神圣的需求在体内肆无忌惮地漫延开来。
她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她惶恐起来,她想到父亲的话,她是属于萧郎的,她还肩负着家族的使命,作为豪门子弟,她是没有自己选择归属权力的。她挣扎着想离开他的怀抱,可是他把她抱得很紧。
“放开我……”她声音在颤抖,这要求如此无力,她甚至潜意识中盼着他拒绝。
他的鼻息变得粗重,虽然听到她的要求,可他同样能感觉对方身体某种原始的渴求。他不是受过礼教的谦谦君子,他的动物性远在人性之上,只要觉得自己需要他就会付诸行动。
“放开我……”她声音更低了,还带着一丝哭腔,因为他已经吻着自己的脸、颈、肩膀……
“放开……”她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下沉沉的喘息声,他已经吻上她的唇,他并不确切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只知道想她近一点,再近一点,而吻就是两人间最近的距离。
最后一丝抵抗的念头像冰山一样轰然崩塌,情苗深种的少女再也抵挡不住如此彪悍的旷野雄风,她迷失了,不管头脑有千头万绪,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她的手无意识的搂住他的背,在他如钢似铁的肌肉上抓出了道道血痕。
外面的太阳更高了,两只野獾从草丛中匆匆跑过,公獾在追逐着,母獾且走且停,像等待更像引诱,最后它们翻滚在一起,像撕咬又像在互相****,最后双双躲进了草丛的最深处。
春天到了,每种动物都在寻找着最原始的欢愉,万物复苏,干裂冻土融化,涌出一缕清泉,生命奇迹般在清泉两侧出现,花花草草争先恐后地钻出泥土,在春风中摇曳着身姿,就连沉默的大地仿佛也被春风唤醒了心脏,绽放出泥土的芬芳。
一只雀鸟停在了洞口,发出响亮的鸣叫声,刚刚经历了渴求、刺疼、温柔和极乐的兰珠缓缓睁开双眼,目视着雀鸟五彩的羽毛,露出一抹幸福的笑。
“你还好吗?”他从后面抱住她的身体,她刚才颤抖得太厉害,他担心会不会自己太过粗暴弄伤了她。
她把手抬向肩部,抚摸他的脸,扭头吻着他,用行动告诉他,自己多么喜欢刚才那缠绵的时刻。她试图站起来,可是双腿发软,她朦胧记得他动作是多么地刚劲有力,那时她以为自己会融化,事实上可能真的被融化了,她都站不起来了。
他吻着她的秀发,心中更多了对她的依恋,他很感叹造物的神奇,能制造出让人如此沉迷的终极欢愉,如果她要融化,那自己刚才就像经历了能让身体爆炸的快乐,这是她给予的,他自然而然要心存感激,他记得母亲教过他这种感觉的形容词——爱。
外面春风轻拂,兰珠离开了山洞,在泉水边席地而坐,她看到水中自己变得更加美艳惊人,虽然衣裳褴褛,虽然发丝凌乱,可能感觉到与从前的青涩截然不同之美在身上弥漫开来,连旁边的野花都映照得更为明艳。
她手指在泉水中划过,对着自己笑了,经历这一刻,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兰珠,有此一遭,她觉得不枉此生,至于以后,管它天塌地陷,她渴求这一刻能到永恒。
“好看吗?”他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她回头看到他手中拿着一个野花织就的花环,他轻放在她头顶,“我娘教我做的。”
她看看倒影,这花冠让她像个公主,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执起他的手,泪水缓缓滑下。
“你难过吗?”他拭着她的泪。
“不,我很开心。”她靠在他怀里,“可是我又很害怕。”
“怕什么?”
“怕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她牢牢地挽着他的手。
他怀抱着她:“我需要你,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吗?”
她脸色微红,“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怎么能离开你呢?”
“没人能把你夺走。”他安心了,只要她自己愿意,他就没什么可担忧的。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是郡主,我总要回去,将来……”她不敢说下去,她不敢,也怕他担忧。
他自信地笑着,“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她望着他,终于破涕为笑,她知道自己倚靠的是个能保护她的男人,她相信他有能力解决一切,那自己还担心什么呢?
放下最后的担忧,她变得热情,主动亲吻着他,几乎又撩起他的冲动,他有些犹豫,想到她刚才娇不受力的样子,他怕她吃不消。
她察觉到他的关心,笑着,“我没那软弱,我已经属于你了,如果你想要,那……”她手抚上他的肩头。
“可你刚才流了好多血。”
“那是因为……”她不敢说下去,她也只是从娘那儿对这事了解一星半点,何况也羞于出口,忸怩着道:“总之没事就是了。”
“可我有事。”萧郎坐下来,她看到他衣服上有血迹,她惊呆了,她忘了他还有伤在身,她急了,“你还有伤刚才就不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时我伤疼都忘了。”
“老天爷。”她急忙撕下裙边,解开他的衣裳为他包扎身上伤口,叫人着急的是他身上有二十多处血洞,虽都不在要害,可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她一边包扎一边嗔怪,“你也真是的,有伤在身还要对人家……你不要命了。”
“这不没事嘛。那样的事我很喜欢啊,现在再来我也可以。”
“不行。”她断然拒绝,“先把伤养好,那事……以后再说了。”说完她自己脸先红了,这都说些什么呢。
忽然一个非常好听但叫人惊恐的女声传来:“真是郎情妾意啊,那事是什么事呢?”声音中带着调笑。
次山和远水的身影魔术般从草丛后出现,萧郎瞳孔收缩,他对任何敌人一向能预警,可唯独这两名祭司说来就来,毫无征兆。他看到她们身后还有几条狗,显然是狗的嗅觉带领她们一路找过来的。
萧郎把兰珠往身后一推,“快走。”
“我不走,要死死在一起。”
“谁说要死?”萧郎怒道:“你在这我得分心照顾你,我能对付这两个家伙,你先走,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不,你骗我的,你想独自应付。”兰珠无论如何不肯走。这时远水道:“如果我没猜错,这位应该是良成玉总兵大人的千金,有西梁侠女之称的兰珠郡主对吗?”
兰珠道:“是又如何?”
次山道:“我们也不想多增死伤,良成玉总兵是我们敬佩的将领,为表敬意,我们可以不把你怎么样,但他……”次山指向萧郎,“必须同我们走。”
看得出次山说话时有些气喘,脸色也很苍白,看来萧郎上次那一记重拳让她受创不轻,不得不说鬼戎祭司的体质也极为怪异,这一拳就是一头大象也打死了,可她居然只是受轻伤的样子。
“不……”兰珠正要拒绝,萧郎道:“照她们说的做。”
“我不能……”
“不要婆婆妈妈的。”萧郎怒吼,“你留在这只会坏我的事,你真的想我们两个都死在这吗?”
兰珠被他吼声一震,打了个寒颤,纵然万分不舍,她也确实清楚留下来于事无补,毕竟也是西梁侠女,即使柔肠百结也不得不当机立断。“你一定要小心,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放心,我会的。”萧郎拥抱她,指向远方:“走!”
兰珠一步三回头,最后一咬牙,含着泪向远方跑去。
直到她身影消失,萧郎才回过头来,次山和远水双手高举,行了个鬼戎族特有的礼数,这是她们对英雄才施的礼赞。
“风雷静,寒霜动,狼牙出,天下哭。今天能目睹大祭司传说中的人物,不胜荣幸。”
“你们一早就知道我是萧郎。”
“是的,问句题外话,郡主知道您的身份吗?”
“这重要吗?”
“说不上重要,只是我们的神喻祭司曾预言良成玉会有将其女嫁给阁下的意愿,如今看起来似乎阴差阳错,您二人珠胎暗结,这是不是证明,凶狼将并非纯粹的野兽?”
“这话怎么说?”
“情之一物,向是害人不浅,阁下一代英雄,如今刚出道就困于儿女私情,似乎于皇图大业有碍。”
“这用得着你们操心吗?”
“当然操心,凶狼将既然也能为情之所钟,那我们就该反思一下对阁下格杀勿论的作法正不正确,现在看来,我们有谈判的可能。”
“谈什么?”
“据我们所知,西南一域是您生长的故土,我们可以答应不再焚林狩猎,不再与狼族为敌,可以今天放您一条生路,条件只有一个。”
“什么?”
“百兽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