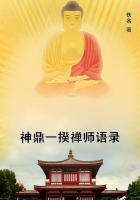“是谁?”
秦氏向后退了几步,一跤坐倒,伸出双手捂住了脸,那声音中满是绝望:“是老夫人。”
南宫咳嗽一声,淡淡道:“秦氏,说这话要有依据。”
“你们都不知道,二少爷他,对着自家人到底是有孺慕之情的,大少爷每次来找他,他都很高兴,为了家人的一句话,他可以做任何事。”略略有些失神似的,秦氏苦涩地道,“二少爷虽是与世无争,天资却很高,大少爷都无法突破的家传绝学,他轻易就能学会。”
这倒是奇事了。既然他这么有天分,那么当初算命先生所说的光耀门楣之人应当是这个二少才对。
只是杜老太太既然认定了大少爷,那么为了面子或是别的也断然不会承认。所以,杜慎言天分越高,越显得杜老太太当年的失算。
于是恼羞成怒了吧。
我负了手,来回踱了两步,走到南宫跟前,拿胳膊拐了拐他:“你怎么看。”
“这案子恐怕可以结了。”
“几成把握?”
“最少七成。”
我点了点头,稍稍放心:“秦氏,你来过县衙,还能再回去杜家么?”
秦氏眼中有热切的光,似是极为期待,闻言越是微微一愣:“只要能让二少爷沉冤得雪,小妇人什么事都无所谓,至于杜家,没有了二少爷,还回去做什么。”
“这样么?”我看了看秦氏,能这样对待不是自己亲生子的孩子,她也算是很上心了,“不如你现在县衙住下,等案子结了再走不迟。”
秦氏略略有些迟疑:“这样好么?”
“也就多双筷子而已。”我笑了笑。
“大人,”秦氏热切地握着我的手,“一切就仰仗您了!”
我刚点了下头,就觉一阵袖风拂过,南宫的脸色像是吃了臭鸡蛋:“放手!”
秦氏应声放手,看了看南宫,又看了看我,有些了然地点了点头。
我又觉得头开始大了。
将秦氏安顿好之后,我已经无心躺在床上休息了,这个身体是弱了些,但是还不至于小小风寒就卧床不起。
只是,无咎在看到我之后,那脸色黑得跟锅底似地。
当然,此刻他还是我的义弟,怎么说也还是会给我面子,所以他转了头,对着南宫一脸的不悦:“你怎么让他起来了?”
南宫摊了摊手,又撇了撇嘴,似是无限委屈:“我是嘱咐他好好休息的,谁知道杜家居然来了人,那个楚歌是个大嘴巴,居然去告诉了清渊。”
楚歌是个大嘴巴,我心中大乐,转头去他的表情,果然见到一直纹风不动的表情居然有了裂痕。
瞧那嘴角抽的,我有些高兴起来,也就不计较无咎那甚不友好的口气。
“无咎,你不是去大牢了么?”
无咎转头看着我,伸出手在我额上摊了摊,吁了口气,然后从袖中摸出一张纸,递给我:“这个是花容写的,说是谢谢你这段日子为她所作的一切,只是那人确实是她所杀,她认罪。”
我慢慢展开那纸。笔墨并不算新,应该不是今日所写。字写得比并不算好,但是足够清隽。
她的手被伤的很严重,那素来不沾阳春水的手,几乎全部变形了,还能写出这样的字,实在是难得。
想花容也是大家出身,虽是误落风尘,却也知洁身自好,那杜慎行在遇到她之前,根本就是个纨绔子弟,相形之下,本是自惭形秽。
他何德何能,得她全心喜欢。
纸上总共只有两句——鸳盟既散何辞死,三生缘尽争不见。
这哪里是认罪,分明是诀别书了。
我无言地拎着那张纸,递给了南宫:“如何?”
南宫看了一眼,淡淡道:“不错,寓意清晰,表达得十分明白,不如成全了她吧。”
我点了点头:“似乎只有这样了。”
无论死的那个是谁,花容所作所为确实已经是构成了杀人罪。
无咎睁大了眼睛:“三哥,你开玩笑的吧。”
我眨了站眼睛:“我哪里有开玩笑?”
“可是,可是……”无咎有些结结巴巴道,“你不是说死的那个不是杜慎行?”
“但是终归是死了人。”我淡淡笑了笑,“就算死的那个不是杜慎行,难道便不需要有人来偿命?”
“无咎,这世上,没有谁的命比谁贵。花容也一样。”
“可是,他们可能是要殉情的啊。”无咎有些失神。
我叹了口气:“可是,现在谁能证明,他们是要殉情呢?如果真是殉情,为何花容会中毒较浅,而身怀绝技的那个人却死了呢?”
“这……”无咎皱着秀气的眉,“难道真的要让花容偿命?”
我眯起眼睛,看着无咎眼中那纠结的小烦恼:“你对她很有好感?”
“她是个勇敢的人。”无咎咬了咬唇,慢慢道,“她受了那么重的伤,却从来不喊痛。她——比很多人都勇敢。”
“所以她敢承认,她杀了人。”我叹了口气。
其实以花容目前的心境,恐怕不是勇敢那么简单。死的那个人不是杜慎行,那么她精心准备的殉情便成了笑话。
有多少的缱绻柔情,就会有多少的失落。
最后活着的那个人,将是输得最彻底的一个。
“好了。”南宫拍了拍无咎的肩膀,看了看我,“我们似乎还欠杜家一个说法。”
“这便去吧。”我笑了笑,“真想知道杜老太太知道这消息后是什么表情。”
南宫悠悠吐了口气:“我倒是很想知道杜家‘二少’的表情。”
他刻意在二少俩字上加重了口气。我暗自摇了摇头。他对卫清渊也是一番长情,遇到像杜慎行这样的,大概是相当鄙夷的吧。
到得杜家,仍是看门的先去通报,以杜家之大,怎么着也得一刻钟。
仍是那朱红大门,在这夏日里透出些森冷的味道。杜家离县衙不算远,我也不是什么娇弱的人,所以也没叫用软轿,此刻,南宫站在身边,撑着把素花的折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