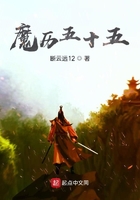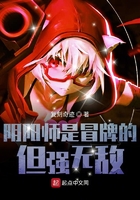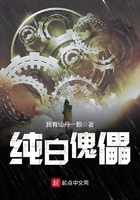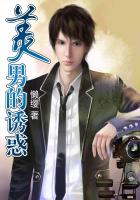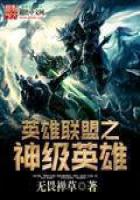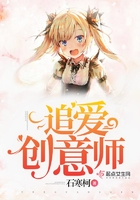农民工是现阶段党的最基本的群众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一个先进的政党,之所以先进,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能代表人民、依靠人民,有自己的基本群众。
什么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人民”的最终标准是生产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人民是指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劳动群众。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统称为生产资料,其作用是吸收活劳动,只有当它吸收了活劳动,即通过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的劳作,才能产生新的社会财富。由于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各个历史阶段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民的主体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民是农民、工人,而不是掌握土地、机械和金融的地主、资本家和银行家。在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这其中人数最多、最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是农民工。因为现在我们还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过去我们主要依靠的群众——农民,现在变成半工半农的了,他们是这个时期社会财富的主要创作者。看看我们的城市在很短的时间盖起了那么多高楼大厦,谁盖的?建成了那么多码头、机场、铁路、桥梁,谁建的?城镇中的保安、保姆、清洁工、服务员他们是谁?农忙时他们还要回家干农活儿,这些都是农民工。可以说农民工是我国现阶段中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劳动大军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他们是当前我们党的最基本的群众。
既然农民工是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群众,那么我们党就应该忠实地代表他们、广泛地团结他们、真心地依靠他们,充分保护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人民群众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过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每实现自己的一个阶段的利益,历史就前进一步。只有搞明白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才能团结和依靠他们去实现其既定目标。那么我们能否用心了解和正确地看到农民工的利益是关键的关键。不抓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能跟你走吗?你能够团结他们吗?你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历史作用吗?不能。过去我们依靠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是农民,农民的利益是土地,我们带领他们解决了土地问题,这样我们既解放了生产力,又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曾经历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承包”的成功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农民变成农民工,他们既在城里做工、又在农村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利益在哪里?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保证不失去土地的前提下,他们的利益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这就是“进城”。农民工进城的本质是进入二、三产业,他们进入二、三产业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抓住“进城”这个关键,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能使绝大多数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党就有了执政根基。当然进城不是指全部进入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包括小城镇,尤其是在农村二、三产业集中的地方就地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如果现在看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策就应向这方面倾斜,特别是公共财政要多往中小城市、小城镇投入,搞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二、三产业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多地走进去,同时加快完善他们的户籍、医疗、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制度。可以说,抓住了这个问题,许多社会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现阶段我国人数最多的劳动群众感谢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你发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并且把他们的利益告诉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使他们有望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积极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又好又快地完成,我们的事业发展就会更有力量。
解决生产关系滞后的问题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眼里,人民群众要生活、要生活得更好,这是生产力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最终动力。因此,我们说发展生产力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要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取决于相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设计的是否正确,其根本标准要看是否同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以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我们先后做了两件最大的事情:一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件事概括起来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即解决超越当时相对低下生产力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解决生产关系中“所有制”超前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就赢得了这30多年的大发展。现在,改革又遇到了新瓶颈,我们搞了好多年,就是迈不过去。这是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与30多年前遇到的问题恰恰相反,即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生产力相对发展了,而生产关系却相对滞后了,有的环节已不能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这除了所有制的一些问题外,主要体现在“分配”问题上。
由于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的滞后,从而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脱节。马克思讲,经济运行的环节、结构可以很多很多,但最终都要归结到生产与消费这个基本结构上来。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你没有东西我没法消费不行,你有了东西我买不起也不行。如果消费跟不上去就必然造成产品积压、生产过剩,货币回不了笼,经济运行不起来。我们常讲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当前来讲,第一驾马车应该是“消费”,第二驾才是“投入”,第三驾“出口”只是补充,把13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做起来才是根本,这个市场比欧美市场都要大。但有人担心,提高消费水平就是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而普遍提高工资就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反过来又阻碍企业的生产。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C+V+M构成的,现在就总体而言是利润(包括税收)与工资(包括二次分配所得)的不平衡(不排除一些例外:如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薄利小企业、一些企业员工工资过高等),利润过高,而工资偏低,带来的是再生产规模的相对膨胀与消费市场的相对萎缩,购买力不足,企业后继乏力,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只有实现利润与工资、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平衡,对二者才都有好处。因此,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当前改革最为关键的一环。一切市场都是依据需求来建立的,所有产业结构都是要根据市场来构建的,生产与消费结构调整不好,以市场为导向的其他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难以奏效的。因此,只有打开了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合理这个症结,其他产业结构中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党和政府是他们的利益代表。生产关系的分配环节出了问题,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是: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相脱离。这些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视为收入差距悬殊。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连续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人民群众是在实现自己的利益过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不能相应享有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久而久之必然会丧失对其领导者的信心,与党和政府渐行渐远,最终会将他们创造历史的力量由生产力转向生产关系以至于上层建筑。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实践是我们的本能,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不能失去这个“本能”,应自觉地顺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信群众的选择、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调整生产关系,冲破改革的这一瓶颈,实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