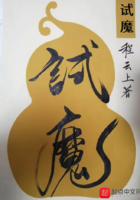她立刻去****每天早晨该干的事。她身上带着那枚金路易。它使她分了心。她不敢去触它,但不时地看它,每次都得看上五分钟。她扫一会儿楼梯,便停下来,看一阵子。她把她的扫帚和整个宇宙全抛在了一边,一心只看着那颗在她衣袋底部闪闪发亮的星。唐纳德夫人找到她时,她正在凝视着那颗星。“珂赛特,过来。”她尽量把声音放低。不多时,珂赛特便走进了那矮厅。这时,那个外来人解开了他带来的包袱。包里有一件毛料小上衣、一条围裙、一件毛布衫、一条短裙、一条披肩、一双长筒毛袜、一双皮鞋,一套7岁小姑娘的全身装束,统统黑色。
“我的孩子,快去穿上这些衣服。”那人说。一天渐渐亮起来,孟费梅的居民,有些已经开了院门。他们在巴黎街看见一个身穿破旧衣服的汉子,领着一个全身孝服、怀里抱着一个玫瑰色大娃娃的小姑娘。正朝利弗里方向走去。
这个可怜的、柔弱的小生命,直到现在才解除掉被压抑的痛苦!
珂赛特表情庄重地向前走着。她睁开一双大眼睛,仰望着天空。她已把她那枚金路易放到她新围裙的口袋里了。她不时地低下头去看它一眼,接着又看那个老人。她似乎觉得,眼下,自己是在慈悲上帝的身边。
十、自食恶果
唐纳德夫人已经习惯,一切由丈夫做主。那人把珂赛特领走足足一刻钟以后,唐纳德才把她拉到一边,拿出那1500法郎。“就这些?”她说。
这是她结婚组成家庭后头一次对家长采取批评行动。“你是对的,”他说,“我是个傻蛋。把我的帽子拿来!”
他把那三张钞票折好,放在衣袋的最下面,匆匆出了大门。他顺着人们所指的方向,一边迈着大步向前走,一边自言自语。
“这人虽然穿件破旧的黄衣,却是个百万富翁,而我,竟是个畜生。他先拿出20个苏,接着又拿出5法郎,接着又拿出50法郎,接着又拿出1500法郎,全不在乎。也许他还会拿出15000法郎呢!所以我必须追上他。”事先替小姑娘准备好了衣包,这也挺奇怪的,里面大有文章。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他的脑子里回旋着。“我是个畜生。”他又骂自己。
离孟费梅不远便走上了通往利弗里的公路。这条公路在高原上蜿蜒曲折,很长。他来到岔路口,走上公路,觉得能看到那个人和珂赛特。他极目远眺,什么也没有。他向人打听,人们告诉他,他们朝加尼方向的树林那边走去了。他赶紧追过去。
他们走在他的前面,由于孩子走得慢,他走得快,并且熟悉路途,这样,他也就能赶上他们了。
“我应该把我的长枪带来!”他自言自语道。
唐纳德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半明半暗度过一生的。唐纳德在平静、平常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当一个诚实的商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当某种动力拨动他那隐藏起来的本性时,他便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恶棍。
犹豫了一阵以后,他想:“唔!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就已有足够的时间走掉了!”
于是,他便继续快速地向前奔走,一副极有把握的神气。
果然,他走过池塘,斜着穿过美景大道右方的大片旷地,走到那条长满杂草、环绕一个土丘而又延伸到谢尔修院古老水渠涵洞上的小径,这时,有顶帽子从丛莽中露了出来。唐纳德判定那人和珂赛特是坐在那里的。那孩子小,他看不见她,可他看见了那只娃娃的头。
唐纳德猜的猜的没错。那人果然在那里坐着,因为珂赛特需要休息一会儿。唐纳德绕过丛莽,突然出现在这两个人面前。
“先生,请原谅,这是您那1500法郎。”他气喘吁吁地赶上去说。
他边说,边把拿着那三张钞票的手伸过去。那人抬起眼睛,问:
“干什么?”
唐纳德恭敬地回答:“先生,我是说,我要把珂赛特带回去。”珂赛特浑身战栗,紧紧偎依在老人怀里。他呢,目光直刺唐纳德的眼底,一字一顿地问:
“你——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是这样,我要把她带回去。我考虑好了。我没有权利把她随便送人。您知道,我是个诚实的人。这小姑娘不是我的,她有母亲,她嘱托我照顾这孩子,我只能把这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如果这孩子的母亲死了,那我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她母亲托付的人。我要看到她母亲亲笔签字的委托书。这是明摆着的理。”
那个人没有说什么。他把手伸进衣袋,随后,那个装满钞票的钱夹又一次展示在唐纳德面前。
客店老板高兴得浑身颤抖起来。那陌生人打开一个皮夹。可是他抽出来的,并不是唐纳德所希望的那样是一叠钞票,而是一张普通的纸片儿。他把那张纸整个儿打开,送到客店老板眼前,说:
“您说得有理,请过目。”唐纳德接过那张纸,见上面写着:
唐纳德先生:
速将珂赛特交与来人。零星债款由我偿还。
顺致大安。
芳汀1823年3月25日于滨海蒙特勒伊
“您认出了这签字吧?”那人问。唐纳德认出了,那的确是芳汀的签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唐纳德这时感到强烈的憎恨,他恨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那种期望,还恨自己被击败。那人又说:
“您可以留下这张纸,解除你的义务。”唐纳德在向后退却,但章法不乱。“这签字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咬紧牙咕哝着,“不过,让它去见鬼吧!”接下来,他试图再作一次无望的挣扎。“先生,”他说,“这挺好。既然您是‘来人’,那‘零星债款’就付给我吧。”那个人站起来,一面弹去他衣袖上的灰尘,一面说:“唐纳德先生,她母亲在一月份计算过,欠您120法郎,您在二月中寄给她一张500法郎的账单,您在二月底收到了300法郎,三月初又收到300法郎。此后又讲定,15法郎一个月,过了9个月,共计135法郎。这样,开头您多收了100法郎,我们就只欠35法郎了,而刚才我给了您1500法郎。”
豺狼被捕兽机的钢牙钳住时的滋味儿正是唐纳德现在感受到的滋味儿。
“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他心里暗想。他像豺狼一样行动起来。他把恭敬的样子丢在一边了,斩钉截铁地说:“不知姓名的先生,我一定要领回珂赛特,除非您再给我1000埃居。”
这陌生人温和地对珂赛特说:“来,珂赛特。”
他左手牵着珂赛特,右手捡起了放在地上的那条木棍。
唐纳德端详着那根粗大无比的棍棒,又望了望那片荒凉的旷野。
那人带着珂赛特进入了森林,把呆若木鸡的唐纳德丢在了旷野里。
唐纳德的目光一直盯着那越离越远的人,眼前晃动着那两只稍微有点佝偻的宽宽的肩膀和那两个大大的拳头。
他想道,“出来打猎,却忘了那支长枪!我真蠢。”客店老板却不肯善罢甘休。“我要看个究竟,他到底去哪里。”他远远地跟着他们。
那人领着珂赛特,朝利弗里和邦迪方向走去。他低着头,走得很慢,这表明他在思考。他确实在思考,而且表情极其伤感。入冬以后,田野显得十分疏朗,因此,唐纳德虽然离他们很远,但可以看见他们。那个人经常会回转头来,看看是否有人跟着他。他发现了唐纳德。他急忙领着珂赛特进入矮树丛中,转眼工夫两人就没了踪影。“见鬼!”唐纳德叫了一声,加快脚步追过去。
树丛太稠密,他不敢走近他们。那人走到枝叶最密的地方,转过了身子。唐纳德即使想藏也没有办法躲开了。他被发现了。那个人的神情是那样的阴沉,唐纳德见后认为“不便”再跟上去了。万般无奈,唐纳德只好打道回府。
十一、时来运转
冉阿让还活着。他掉进海里时,他已经解脱了脚镣。他在海里潜水,兜了一个圈子到了一艘停在港里的海船下面。他躲到了驳船里,直到天黑。天黑后,他跳下水,泅向岸边,在勃朗岬附近上了岸。因为他身上带着钱,所以在那里弄到了一身衣服。在巴拉基耶附近有一家小酒店,经常会替逃犯们提供服装,以此谋利。这之后,冉阿让和所有逃避法网和社会厄运的人一样,走了一段隐蔽曲折的道路。他在普拉多找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随后,他走上了去阿尔卑斯省布里昂松大维拉尔的路。提心吊胆的逃窜,摸索着行进,像田鼠在地道中,说不定哪里会出现危险。此外,他还到过比利牛斯省的阿贡斯、沙瓦依村附近的都美克山峡,又到过佩利格附近勃鲁尼的葛纳盖教堂镇。最后,他到了巴黎。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他又到了孟费梅。
到巴黎之后,第一件事便是给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买身丧服。第二件事是找个住处。做完这两件事以后他便到了孟费梅。
大家不容易看破他的秘密,因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在巴黎偶尔得到一张登载他死亡消息的报纸,也就放了心,而且几乎可以说,他稳定了下来,好像自己的确已经死了。
当天黄昏的时候,冉阿让把珂赛特从唐纳德夫妇的魔爪中救出来以后,回到了巴黎。他带着孩子从蒙梭便门进了城。当时,天刚刚黑下来。他们上了一辆出租马车到了天文台广场。下车后,黑暗中,他拉着珂赛特,穿过乌尔辛和冰窖附近的一些荒凉街道,向着医院路走去。
对珂赛特来说,这一天是一个奇特的、充满激情的日子。他们在某家篱笆的后面,吃了从地方的客店里买来的面包和干酪,徒步走了不少路,换了好几次车子。她不叫苦,可她疲倦极了。冉阿让也感觉到了,因为她走到后来,越走便越拉紧了他的手。他把她背了起来。
珂赛特,怀里抱着卡特琳,头靠在冉阿让的肩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