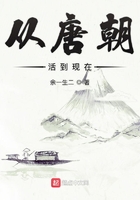在珂赛特这个黑洞的旁边,有一扇门,门里是一间黑洞洞的大屋子。屋子里摆着两张洁白的小床,爱潘妮和阿兹玛正安静地睡在那里。小床的后面还有一只不挂帷帐的柳条摇篮,那个一夜啼哭不停的男孩睡在那里面。
那人猜想这里一定与唐纳德夫妇的卧室通着。他准备退出时,忽然看见一个大壁炉旁边有两只孩子穿的木鞋,式样各不相同。这时,那客人才想起,每到圣诞节,孩子们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一只鞋放在壁炉里,好让他们的好仙女暗地里送些闪闪发光的礼物给他们。爱潘妮和阿兹玛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客人弯下腰去。他看到,仙女——她们的妈妈,已经光顾过了:每只鞋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全新的、闪闪发光的、值10个苏的钱币。
客人直起身来,正想离开,却看见了另一件东西:在炉膛的一个最黑暗的角落里,有个东西,那是一只木鞋,一只粗陋不堪、已经开裂、满是尘土和污泥的木鞋。这是珂赛特的木鞋。
一个从来就处处碰壁的孩子,居然还不失信心。不过那木鞋里却是空的。那客人在自己的背心口袋里摸了摸,弯下身去,将一个金路易放在珂赛特的木鞋里。
九、唐纳德施展伎俩
离天亮大约还有两个钟头,唐纳德老板已经在酒店的矮厅里。他捏着一支笔,伏在桌子上给那穿赭黄大衣的客人编造账单。
那妇人俯下身子看着他。他们不说话,一方面是在思虑,另一方面则是在自我鉴赏。百灵鸟在打扫楼梯。大约有一刻钟的工夫,经过了几次涂改之后,唐纳德编制出了这样的杰作:
一号房间贵客账单
晚餐费3法郎
房间费10法郎
蜡烛费5法郎
火炉费4法郎
服物费1法郎
共计23法郎
“服务费”被写成了“服物费”
“23法郎?”那妇人喊了出来。她有些不敢相信,但还是很兴奋。唐纳德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感到满意。
“没错儿,唐纳德先生,你开得对,他的确应当付这么多。”那妇人叽里咕噜地说,心里正想着昨晚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送给珂赛特的那个娃娃,“只不过数目过大,他不一定肯付。”
唐纳德冷笑了一下,说道:“他肯付的。”
那冷笑表现了自信心和家长派头。那妇人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开始整理桌子。丈夫则在厅里来回走动。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还实实在在地欠别人1500法郎呢!”他走向壁炉,坐下来,把两只脚踏在热灰上,细细盘算。
“也是!”那妇人随后又说,“我今天要把珂赛特撵出大门,你忘了吗?这妖精!她那娃娃……她让我伤透了心!我宁愿让她嫁给路易十八也不愿让她在家里多留一天!”
唐纳德点着他的烟斗,在吸烟的空当跟她说:“去,把账单交给那个人。”他刚出门,那客人就进入厅堂。唐纳德立即转过身,跟在他的后面。那个穿赭黄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他的木棍和包袱。“先生您起得这么早!”唐纳德夫人说,“您要立即上路吗?”
她一边用指甲掐着那账单,折了又折,一边与客人搭话。
在她看来,把这样一张账单送到一个显然是个地道的“穷鬼”的客人手里,是件为难的事。
他回答说:“是的,大嫂,我就走。”
她问:“先生到孟费梅来办事?”“路过,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可办。”他接着又说:“我该付多少钱?”唐纳德夫人一声不响,把那账单递了过来。客人打开那张纸,望着它。“大嫂,生意还好吧?”他接着说。“马马虎虎,先生。”唐纳德夫人回答。她用一种缠绵的声调接着往下说:
“唉!先生,日子过得真够紧的!您知道,在我们这地方,很少有富户,全是些小户人家。我们很少遇到像您这样慷慨有钱的过路客人。我们的开销又这么大。比方说,这小姑娘,就使我们穷得底儿朝了天。”
“哪个小姑娘?”“就是那个您知道的小姑娘珂赛特呗!这里大家叫她百灵鸟!”“啊!”那人说。她接下去说:
“那些乡下人多蠢,起了这样的小名!请您说说,我们倒不求人家布施,可是也不能老布施旁人。营业执照费,消费税,门窗税,附加税!您知道,政府讨起钱来吓死人的。再说,我还有自己的两个女儿。”
这时,那人说:“要是有人肯替您把她带走呢?”说这句话时,他极力想使声音显得平静些。“把谁带走?珂赛特?”“对呀。”
店婆子的那张横蛮的红脸上马上眉飞色舞起来。
“啊,先生!我的好先生!抓住她,带走她!愿您得到仁慈的圣母玛利亚和天国所有圣人的保佑!”
“就这样定了。”“您带她走?真的?”“真的。”
“马上?”“对。您去把那孩子领过来。”“珂赛特!”唐纳德夫人大喊了一声。
“这会儿该付账了,”那人紧接着说,“我的账是多少?”
他望了一眼那张账单,不禁一惊。“23个法郎!”他看着那店婆又重复了遍:
“23个法郎?”
唐纳德夫人对这一质问早有准备。她沉沉稳稳地回答:
“啊!圣母!是这样,先生,是23个法郎。”那外来客人把五枚各值五法郎的钱放在桌上。“请把那小姑娘领来。”正在这时,唐纳德出现在厅堂的中央。“先生付26个苏就行了。”
“26个苏?”那妇人喊起来。
“房间20个苏,”唐纳德冷冰冰地接着说,“晚餐6个苏。至于小姑娘的问题,我得和这位先生谈几句。”
唐纳德夫人的心头一亮。她觉得那里似乎有灵光在闪动。
厅堂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唐纳德给客人搬了一把椅子。
“是这样的,先生,那孩子,我喜爱她。”他说。那陌生人盯着他说:
“哪个孩子?”
“真是滑稽!谁会喜欢这几个钱?这几枚值100个苏的钱,您请收回吧。我所喜爱的是这个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那陌生人问。“啊,我们的这个小珂赛特嘛!您不是要把她带走吗?可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同意。这是真话!我们离不开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我们为她花了许多钱,她有许多毛病,我们不是有钱人。她常生病,看一次病我们就得付400法郎的药钱,人总得替慈悲的上帝做点好事嘛。这孩子没爹没妈,我把她养大了。我赚钱买面包,填饱她和我们一家四口的肚子。我舍不了这孩子,您明白吗,我们彼此有了感情。我是一个傻好人,我爱她,我也不晓得什么道理;您看到了,她好像是我们的亲生女。我需要她待在我家里,叽叽喳喳,有说有笑。”
那陌生人一直用眼睛盯着他。他接着说:“对不起,请原谅,先生,不见得有人肯把自己的孩子就这个样子送给一个过路人吧?您懂吗?假如我让她走,割爱牺牲,我得知道她去了哪里,我希望能知道她在谁的家里,好时不时地去看看她。我连您的姓名还不知道呢。您带着她走了,至少也总得先见到一张令人讨厌的小小的身份证什么的吧?”
那陌生人用一种坚定沉稳的口吻对他说:
“唐纳德先生,从巴黎来这里,才五法里的距离,不会有人带身份证的。我打算带走珂赛特,我就一定带她走。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让您知道我的姓名,不会让您知道我的住址。”
唐纳德认识到,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手。当他听了这陌生人的那种干脆而坚定的回答、看到这神秘的人物竟神秘到如此简单的时候,感到自己实际是弱的一方。唐纳德原本就是那样一个能一眼便可看清形势的人。他估计,单刀直入的时刻到了。在这关系成败的紧要时刻,突然揭开了他的底牌。
“先生,我非得到1500法郎不可。”他说。陌生人听完,从他衣服侧面的一只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黑色的旧的皮钱包,取出三张钞票,把它们放在桌上。接着,他把大拇指压在钞票上,对那店主人说:
“去把珂赛特找来。”珂赛特早晨一睁眼,便跑去找她的木鞋。她在鞋里发现了那枚金币。那不是一个拿破仑,而是王朝复辟时期的那种全新的、面值为20金法郎的硬币。珂赛特看花了眼。她乐得不得了,感到自己转了运。她不知道金币是什么,她还不曾见过。她飞快地把它藏到了自己的衣袋里,好像它是偷来的。她快乐,然而,这快乐之中又充满了恐怖。她感到满足,而又感到特别惊恐。从昨晚起,无论是在她惊喜交集时,还是在她的睡梦中,那个好像又老又穷,而且那样忧伤,但又那么有钱,那么好的人的影像,一直在她那幼弱的小脑袋里闪动。她感到,自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和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