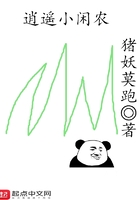我珍藏着一方普通印章,并非出自名家之手。然而,在我藏用诸多名家及华贵章料的金石篆刻之中,却被格外地看重。
常作书画者,必镌金石名号,钤于作品之上,更显儒雅增色。
有名分者抑或托人讨以名家刊刻,则更令他人看重,身价倍增。我同样也求得多方名人镌刻姓名、斋号的印章。并每每于书画作毕,择一合适印章钤于落款之后,或引首,或压角,悬于粉壁,把玩品味,喜不自胜。但偶得佳作,我却偏爱选此印章钤于其上。这样已久,有朋友不解,我自会讲起有关印章的故事,众友愕然……该印章石料只不过是一般常见的青田石,一块方方正正的普通章料,在我这些名贵的材质兼有极美的饰钮和华丽包装锦盒的印章之中,实在显得很是平常。若论其治印的艺术水平,也非能与大家相媲美。细细赏鉴,印文“耕香”二字朱文,择用字体为常用的小篆体。刀法、章法布局经营有明显“邓派”风格,循规蹈矩,不失法度。
往事如烟,不能释怀。先父喜作书画,我自小耳濡目染,常常站立于木凳之上,翘企案前,见父亲秉笔勾勒,不多时便满纸烟云,树木怪石,一片山野清气,沁人心脾。作罢择一印章,小心钤于画作之上,黑白之间立时显出一点艳红,看上去格外精神。黑色、白色、红色,深沉浑茫中现出灵气,有着特有的美感。自此我便对那印章、对那一点艳红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记。十几年来我也用生命去苦苦追寻、经营着那一点艳红了。
有一天,父亲带我去见邻乡的一位老者。老者鹤发童颜,身着对襟青衣,方口布履。其案几、床头堆满了各种章料、印稿,满室清气。我肃然立于父亲身侧,聆听二人的谈话。在回答过老人的一番询问后,我见老人随即取出一块石料,奏刀嘎然有声。我凝神细观,光滑的石面在以刀代笔的切削中显露出几条柔美的或直、或曲的阳线,很是神奇。窗外不知何时秋雨淅沥,屋檐上的雨水滴落声和着金属刻刀划破石料的清脆声,铿锵充实的重奏,缠绵柔和的吟呓声色,似是一片柔美的和声中间断生出清劲,使得我至今受用不尽。
以后许久,我再未见到过那位仙人般的老者。有一天,父亲苦涩地告诉我,那老人某日安祥地坐在木椅中去了,是他的邻人整日未见其踪迹,进屋寻视,但见老人呈睡眠状,面色毫无苍白,却已飘然辞世。亲朋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有用洁白宣纸整齐包好的一方印章,印文乃是我所向老人求治的“耕香”朱纹闲章。这当是老人留在世上的绝迹了。我只向老人恳求过一次,他却在临终前满足了一个孩子的要求。
我真不知道,更不能体悟到老者对世间万物的淡定超然,但我总在努力使自己达到生命释放中的安静。老人身处僻壤、不求功名,对艺术执着追求,不,那是他对生命的追求,对生命的表达。如今我身处喧闹的市井,应酬着各色人事,深夜里万籁俱寂,不免常常念起儿时乡村那独有的宁静与幽渺,念起那位超然物外的老者,于是这方普通的印章便不再普通,因为它给了我对生命的希冀。
那黑,那白,那红,能呈我生命气息。那里是我精神的家园!
(原载1996年7月15日《文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