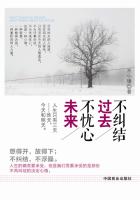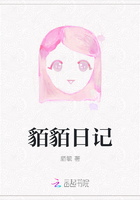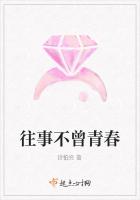这种制度在宋代遭到理学家的抨击和社会各阶层的抵触。如程颐就认为,不准官民祭祀五代祖先不仅不合宗法和情理,也不利于孝道伦理的推行和孝治天下的贯彻。民间违制私祭先祖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出现祭祀始祖的僭礼行为。宋徽宗时不得不徇流俗之情,放松祭祖方面的有关规定。明朝初年规定,官僚贵族可以设立家庙,祭祀高、曾、祖、祢四代先人,士庶人只能祭祖、父两代。嘉庆时又扩展为士庶人也可以祭四代祖先,同时允许官民于冬至日祭祀始祖。
至于祭祖的办法,二程有详尽的描绘:“设席坐位皆如事生。……太祖之设,其主皆刻木牌,……每月告朔,茶酒。四时: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阳,冬以长至,此时祭也。”时祭中,民间最重视的是清明和冬至两次家族祭祀。其他各种形式的特殊祭奠,如科举题名、升官进爵时都要去祠堂行礼等,就不一而足了。
一般地说,木主(又称神主、牌位、木牌、神牌等)和画像作为祭祀对象的化身象征,被恭奉在祠堂正中接受子孙的膜拜。至今有些家族仍然保留和供奉着先人的牌位,许多流传下来的宗谱前面也可见先人逼真的画像。至于祭祖的参与者以及供品、程序、礼仪等,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其三,与从观念上突破大小宗法制对官民祭祖的限制相应,宗族祠堂始现于宋元,昌盛于明清,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一个可观的社会现象。
唐末五代动乱之后,以前用于祭祀的家庙也随着士族的消失而几尽毁绝,四时的祭祀只能在宅内进行,这远远不能适应日益扩展和越来越频繁的祭祖活动的需要,于是宋元出现了居于庙祭与寝祭之间的过渡形态的家族祠堂。祠堂本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到了明清时期,它还兼成为族长施政、族人集体活动的主要场所。所以,凡是有经济力量的宗族,都设有宗祠。尤其到了清代中期以后,祠堂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即所谓“族必有祠,合姓祖先统萃于此”,以至市镇乡村祠堂林立。如乾隆时福建、江西、湖南人“皆聚族居,族皆有祠”;浙江奉化人也“多聚族而居,每族多建族祠以供主”;广东番禺“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宗,族人不满百户者,亦有祠数所。”有些地方甚至把祠堂看得比自家房屋还重要,如广东潮州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福建莆田人也是“营室先营宗庙,盖其俗然也”,以至莆田县城内五分之一的地方被宗祠占据了。祠堂的兴盛是宗族规模扩大的表现,“祠堂的功能是对祖先作季节性的祭祀,并对族中的重大事件作自治的决定,其对子孙们的行为,特别是对孝行的监督,自然是主要的作用之一。祠堂及其功能的出现,保证孝道实践的贯彻。”
其四,私修谱牒活动兴起。
谱牒是宗族活动的文字记录,兴修族谱与宗族活动的兴盛是一致的。唐代以前,主要是官修族谱,即由政府指定史官或专人治谱,体例上以世系为主,分列宗族渊源、世系、地望、代表人物传记等等,其时的族谱主要表达宗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
宋以后私家撰谱盛行,且体例、内容方面也由简约而渐趋完整乃至繁杂,如北宋欧阳修修撰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洵修撰的《苏氏族谱》都完好地留传下来,中有序、跋、世系图、世系表、传记等,成为后世修谱的范本。明清时代谱例大发展,类目众多,祠堂、坟茔、族规、祠产、画像、文书等,都各以专类进入谱书。私修族谱所包含的宗族史和宗法伦理的内容,既可以增强宗族凝聚力,防止异姓乱宗,又可以激发族人效法先人,光宗耀祖,特别是孝道方面的内容,“被宗族上层用作对族人进行思想伦理教育的教材,也是个人修养的工具,起着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家族和家庭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时族谱主要能够发挥社会功能。当然,家谱维护族权,进而维护政权,从这个角度看,近古族谱也有着某种政治功能。”目前保存的种类繁多的族谱,是研究我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
总之,无论是宗族的组建、宗族活动的开展,还是祭祖范围的扩大、方式的增多,乃至祠堂的兴建,族谱的修撰,都是宗法制兴盛的表现形式,是平民家族制度过程的完成。宗法精神以全社会规模的重新高涨,既是封建社会后期孝道“变本加厉”、空前昌盛的体现,又是传播孝道理论和促进孝道实践的得力工具,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孝道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
同时,为维护宗法统治,维护大家族的团结,五花八门的家范、家书、家礼、家训等也竞相问世,泛滥成风。明清以后,几乎所有的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家法、家规。保留至今的清代家训仍然汗牛充栋。
二、愚孝的泛滥
随着理学正统地位的日趋巩固,孝道被极端异化,愚孝之风愈煽愈烈,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孝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孝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的顺从已经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这既是极端专制集权在道德领域的体现,也是张载、程朱等理学家赤裸裸地鼓吹愚孝的结果。
理学家当中,以张载对孝道的论述最少,却最带有“愚孝”的性质。他强调对父母之命要无原则、无条件地顺从,“聚百顺以事君亲,故日‘孝者畜也’,又日‘畜君者好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异,然后能教人。”他举例说:“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顺从父命自缢而死的申生,尊亲保身的曾参,被父驱逐而无怨的伯奇,张载列举的都是些宁肯自己受委屈而死,也不对父母申辩、不校君亲之命的孝子,其旨就在于要人们服服帖帖地顺从君亲之命,而不管父母的意志是否正确合理。张载还把这种“孝顺”的原则加以推广‘,认为人们安于天地父母的安排,逆来顺受而不加反抗,就是“纯乎孝者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之意志、命令总是最合理的,贫贱富贵都是天地父母对人的恩泽,人只有感恩戴德,顺从天命,恬然处世。
理学家认为,孝是人子的本分,纯孝的人不问父母是否慈爱,只须对所应尽孝的对象尽孝悌之道,即使不能博得父母的慈爱欢心,也丝毫不应有怨怼不平之情。所以,当“人不幸处继母兄弟不相容,当如何”这样的问题摆在朱熹面前时,他随手拈起“以父顽母嚣而克谐以孝”的舜为例子答日:“从古来自有这样子。公看舜如伺。。后来此样事多有。只是‘为人子,止于孝。’”二程对“事兄尽礼,不得兄之欢心,奈何?”的回答也是:“但当起敬起孝,尽至诚,不求伸己可也。”更何况历史上许多卓越的孝子,其孝行都是通过父母的拂逆意识而愈益彰著的。因而,“为人子不幸而事难事之亲,则于舜与薛苞事,可不勉而师之乎?”子的义务就是父母的权利,而父母的权利是可以无限制地膨胀的。所以,朱熹甚至把万章的问题拿来设问道:“且如父母使之完廪,待上去,又捐阶焚廪,到得免死下来,当如何?父母教他去下井,待他下去,又从而掩之,到得免死出来,又当如何?”朱子认为,即使父母真的这样做了,也不能怨忿不满,而是应该象舜那样,“一心所慕,惟知有亲”,老老实实地尽为子的孝道。这分明是在公开地大肆宣扬“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且还要对父母无怨无尤、感激涕零。
个人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个人的意志当然更是属于父母、家庭、家族的。个人的理想、追求、一切行为都应该以家庭利益,以孝道为中心,不可违逆父母之心。比如,理学家虽然明知“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又认为个人必须为践履孝道而牺牲自己:
家贫亲老,仰事俯育,或先祖遗愿,父母责望,“故不可不勉尔。”若是“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则两败,父子相夷矣,何以为学!读书是读甚底?”
不过,程朱与张载还是有所区别的,程朱不是以百依百顺的曾子或待烹的申生作为行孝的典范,而是处处把舜当成孝子的榜样。
有问:“曾子之孝与舜之孝,优劣如何?”程颐日:“家语载耘瓜事……孔子闻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些失处。若是舜,百事从父母,只杀他不得。”有问:“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答日:“此只是恭也。若舜,须逃也。”可见,程朱对张载所主张的走向极端的孝行,即“愚孝”,还是稍有修正的。这与程朱的“贵权”原则是一致的。
无论如何,宋代以后,在统治者的褒奖和理学家的倡导下,封建孝道作为纲常礼教的核心,已经暴露出其钳制人性的一面。“盖父母者,子之天地也”,若违背或怠慢天地的意愿,则必有“雷霆之诛”、“幽明之谴”,所以,对父母的任何无理要求,人子都只有俯首贴耳,垂目而受。“母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尽子道,……母生之身而母杀之死者,且不敢怨……孝子之于亲,纵受其虐,不敢疾怨。”封建社会后期,“天下无不是底父母,父有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观念,并被列入《幼学琼林》等蒙学教材中。子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自我,沦为父家长的奴隶:“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为朋辈,事事欲论曲直。……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封建孝道完全堕落为“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蒙昧主义:
“子弟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父母即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甚至连黄宗羲也说:“故父行未必尽是道,在孝子看来,则尽是道,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实实如此。就如世俗之父母,嘻嘻嚆嚆,非是望我太切,则是虑患太深,原无有不是处。未有舍父母而别求所谓圣贤者。从来弑父与君,只见得君父不是,遂至于此。”这是封建孝道理论和孝道实践发展的必然,是封建孝道走向没落的表现,也是封建制度行将就木的预兆。
其二,造端于唐代的割股疗亲的愚孝之风到宋元时代越刮越剧,而且花样翻新。失去了理智的孝子们把孝道作为自己生命的精神支柱,对行孝表现出一种宗教信仰式的狂热,如同宗教徒为证明自己对造物主的崇敬而斋戒、禁欲一样,自伤、自残、自戕以全孝心、成孝道,遂为屡见不鲜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孝道,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孝道,在世俗社会的确具有宗教的功能。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登峰造极的地步。
传统儒家孝道认为,身体发肤,皆是父母所遗,毁伤乃是不孝的行为,因而才有乐正子春伤足不出、自怜涕泣的故事。粗略地翻检前代史书,也没发现有以自己体肉为父母药饵的记载。唐代以.后,随着三教合流趋势的明朗化,随着佛教对孝道宣传力度的加大,佛教传说中舍身供养、以血肉疗病的习俗也随之而脍炙人口.并导致中土民众的由信仰而仿效。佛经里有许多以己身布施众生的本生故事,如“萨埵舍身”、“尸毗割股”、“割肉贸鸽”等。据《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载:“有王太子,……道见一人,得疾困笃,见已有哀伤之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得疗即痊?病人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尔时太子,即以利刃刺身出血,以与病者。至心施与,竞无悔恨。”重庆宝顶山大佛湾所见的《大方便报恩经变相》中,有忍辱太子剜眼出髓医父王疾病的故事画,图中所刻经文日:“释迦因地行孝,剜眼出髓为药。大藏佛言:忍辱太子知其父身婴重病,……太子问日:药是何物?大臣答言:是不嗔人眼睛及其骨髓。
若得此药,病可得救。”也许是在此类传说影响下,唐人遂以为人肉可以疗痼疾。更兼“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赢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到股肉而进。”盛行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割肉疗亲的愚孝行为由此而滥觞、蔓延。
《新唐书?孝友传》中列举了“京兆张阿九、赵言,奉天赵正言、滑清泌”等共29位割肉疗亲的孝子。“孝友传”中也有数例此类孝行记载。如池州何澄粹,“亲病日锢,俗尚鬼,病者不进药。澄粹剔股肉进,亲疾为疗。”安丰李兴,“父披恶疾,岁月就亟,兴自刃股肉,假托馈献,父老病已不能啖”。后来柳宗元为之作《孝门铭》。
涪城章全益,“少孤,为兄全启所鞠。母病,全启到股膳母而愈。及全启亡,全益服斩衰,断手一指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