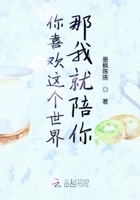如果说割股疗亲在唐代尚属“新生事物”,甚至往往能够惊世骇俗、起到轰动效应的话,那么,宋代以后,这种少数人的“特立卓行”已经演变为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行孝方式,只要父母顽疾染身,久治不愈,孝子不仅割肉啖亲,或抉眼断乳、剖腹探肝以为药饵,甚至自焚、自殉以祷天显灵,祈愈父母。
仅《宋史?孝义传》就载有十多个这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孝子事例。如刘孝忠“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寻愈。”张伯威九十八岁的祖母患痢疾而生命垂危,“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接着继母因姑病而惊急成疾,“伯威复剔臂肉作粥以进,其疾亦愈。”他的妹妹也剔臂肉作粥为其公婆治病。另有一个叫杨庆的,为父病割股之后,后母又“病不能食,庆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药进焉。”这些孝子孝女往往受到立“纯孝坊”、“孝妇坊”、“崇孝坊”等形式的嘉奖。
《金史?孝友传》中孝友见于旌表者仅有六人,其中三人皆是以割股疗亲而载于史册的。这既表明金王朝对孝道观念的倡导,也显示出孝道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和影响。元代一边以严刑禁之:“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到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一边大肆旌表宣扬。仅《元史?孝友传》中就载有七例,甚至还有惨不卒读的“凿脑”医亲者。《元史?烈女传》云:河南秦氏二女,“父尝有危疾;医云不可攻,姊闭户默祷,凿己脑和药进饮遂愈。父后复病欲绝,妹到股肉置粥中,父小啜既苏。”迨至明朝,剖肝剔臂依然是行孝的重要方式,如沈德四“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已而祖父疾,到肝作汤进之,亦愈。”姚金宝、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三人都受到旌表。
被载人正史的仅是极少数受到“国家级”表彰者,至于地方旌表或不闻于世的就更多了。据李飞《中国古代妇女孝行史考论》一文依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嫒典?闺孝部》所作的统计,明代622个孝女孝妇中,除少数割胸、膝、肋以及割耳、割乳或断指者外,割股者257人,割臂者30人,割肝者19人,共计306人,占总人数的49%;清代342个孝女孝妇中,割股者233人,割臂者4人,割肝者8人,占总人数的72%。这是一组令人怵目惊心、不敢置信的数字!真德秀《潭州谕俗文》中提到:“数月以来,累据诸厢申到,如黄章取肝以救母,刘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周)宗强割肱救疗,母遂平复。”仅数月时间,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就上报了数例割股探肝者,管中窥豹,可知当时剔肝剐股疗亲孝亲已经成为社会风气,这也证实了49%、72%比例的可靠性。
这种“越礼以加敬,轻生以致养”自摧自残的愚孝行为,在唐代即激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强烈反感。诸多的抗议声中,韩愈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父母疾,亨药饵,以是为孝,未闻毁肢体者也。荀不伤义,则圣贤先众而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安可旌其门以表异之?”陈尧也对这种“折体断肢,密置于味”的愚孝行为表示愤慨:“荀居疾以剥肤,由味而丧躯,则所谓陷之于不义者也。禽之相食,尚曰无有,安在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显然,韩愈、陈尧等是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认为毁伤父母所遗是大不孝的有罪行为,决不应该去表彰。史官虽然也同意韩愈的观点,但同时又为愚孝行为开脱日:“委巷之陋,非有学术礼义之资,能忘身以及其亲,出于诚心,亦足称者。”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今人割股救亲,其事虽不中节,其心发之甚善,人皆以为美。”这种开脱中溢满称道之情,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遍看法,再加上“旌表门闾”、“名在国史”的官方鼓励行为,越发使得这种愚孝行为泛滥起来。
明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
祷岱岳神,母疾疗,愿杀子以祀。已果疗,竟杀其三岁儿。”为作孝子不仅自伤,还殃及无辜幼儿,毁伦灭嗣之罪不容诛。皇帝闻讯震怒日:“父子天伦至重。《礼》父服长子三年。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并诏令众臣议旌表之例。礼臣议论日:
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医药吁祷,迫切之情,人子所得为也。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无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
自此,明朝官方虽然没有严令禁止割股卧冰之类的有伤身体的愚孝行为,但一般也不再公然表彰。
当然,一纸空文并不能阻止此类孝行的发生。《清史稿?孝义传》中仍然有近二十例剐肝剖心以疗亲疾者。如汪灏四兄弟相继为父兄割股、割臂、断指,有司表其门日“一门四孝友”。七岁儿吕某因“母病将殆,思肉食”,即割股啖母,被称为孝童,其父也曾割股愈父疾。直到福建的李盛山割肝救母,伤重而卒,这种行孝方式是否应该得到表彰的问题才再次提了出来。礼部以其轻生愚孝而不予旌表。接着世宗谕日:
视人命为至重,不可以愚昧误戕;念孝道为至弘,不可以毁伤为正。……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若因己病而致其子割肝到股以充饮馔、和汤药,纵其子无恙,父母未有不惊忧恻怛惨惕而不安者,况因此而伤生,岂父母所忍闻乎?父母有疾,固人子尽心竭力之时,倘能至诚纯孝,必且感天地、动鬼神,不必以惊世骇俗之为,著奇于日用伦常之外。……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
但是,孝子们对此充耳不闻,依然是我行我素。究其原因,一是愚孝观念对人性之束缚,已经使人不能自拔;二是孝感传说的神异灵验令孝子们心动;三是社会舆论对此从来都是褒扬有加;四是宋代又复设了隋唐废止的“举孝廉”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声名利禄的内在刺激不可忽略,“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五是官方“虽未定例,仍许奏闻,且有邀恩于常格之外者”,所谓的“听其所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怂恿和鼓励。古人自己总结说,割肉愈父母疾者,“大者邀县官之赏,小者集乡党之誉。讹风习习,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执政不以禁。”所以民间割股取肝者仍乐此不疲。直到清末民国,这种事情在民间仍然时有所闻。
三、其他
其一,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宋明理学孝道观的影响为甚。
救死扶伤、悬壶济世本是医生的职责,但父母生病时,孝子却除了寻医问药、奉孝病榻,除了寄希望于孝感而去祈祷、割肝、卧冰之外,就无能为力了。尤其是若把生病的父母交到庸医手中,则与亲手戕害父母性命无异。在宋代极端强调孝道的社会背景下,孝子们深感这是对父母的大不孝。理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二程就认为:“疾而委身于庸医,比之不慈不孝,况事亲乎?”所以,“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人子事亲学医“最是大事。……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二程的这段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宋明医学界流行的知医为孝、医孝合一观念的反映。
这种观念对传统医学所发生的影响是双重的。
从正面看,一大批儒者弃学从医,投身杏林,如元代名医朱震亨本为朱熹四传弟子许谦的门人,连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也曾行医救世。他们都把医学看作济众救世的“仁术”,强调以仁孝为行医准则,这无形中从整体上提高了医德水平。同时,医家无不谈“孝”,视知医为孝子份内之事,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就直接把其医学著作命名为《儒门事亲》。还有不少孝子学医的动机是出于“孝”。这些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医学的发展。
孝道对传统医学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权且不论“人肉治赢疾”一言,就引得闾阎相效割股,使多少人丧生毙命于愚孝之下;只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语,就直接阻碍着解剖学的发展,进而阻碍传统医学的发展。解剖是对身体的直接毁伤,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为儒家孝道所不容。清代名医王清任对此深为反感,但囿于礼教压力,也只能扼腕长叹。中医之所以不能象西医那样精确无误地“对症下药”,与此不无干系。愚孝的枷锁就这样拖住了传统医学发展的步伐。
其二,与前代相比,明清有关代父母兄弟受死方面的孝行明显地多了起来。不计其他各种笔记、杂录在内,仅《明史?孝义传》中就载有数十个例子,《清史稿?孝义传》中也有不少。
这种孝行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为保护父母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由于倭寇作乱、盗贼滋事、农民起义等原因,社会动乱频仍,时常殃及无辜。许多孝子在父母遭到强人盗匪或散兵游勇杀戮时挺身而出,引颈代死,有的感动贼寇而被两释,有的双双被杀,有的则自己身亡而保全了父母。二是在父母遭遇不测时,舍生救护父母。比如父母身陷虎口时,孝子们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孤身赤膊上阵,与之进行殊死搏斗。三是代父兄受刑。这个内容我们在“传统法律与孝道”一章中已经述及,此不赘言。
其三,哭泣、悲伤的程度亦为孝心轻重多寡的标尺。明清因悲哀过度而身殉亲丧的记载大大地多于前代。仅《清史稿?孝义传》
就载有近二十个闻丧殒命或身殉父母的孝子例。如五岁曹孝童“呜咽匍匐死父侧”;薛氏兄弟哀母丧,“数日皆死”;丁某母卒后谛视母肖像良久,“仆地遽绝”;襄城“尝粪孝子”刘宗洙母殁后,“五内裂”而遂卒,其兄亦呕血而死;潘氏姊弟“家遇火”,因母亲未及被救,遂入烈焰中与母同归于尽;林氏兄弟在父亲被海潮溺死后,双双自沉。前引《中国古代妇女孝行史考论》一文统计,明代622个孝妇中,殉死者为47人,清代342人中殉死者为21人。
《孔府内宅佚事》上提到一个孔府本家,在八国联军时期父亲战败后自刎殉国,儿子为对父亲尽孝而上吊自尽,儿媳收夫尸后也自缢殉夫,为此而得到皇帝一块“满门忠孝”的赐匾。于这些连篇累牍、不绝于书的所谓的孝子事迹中,愚孝对人性的摧残,礼教杀人的本质了然可鉴。
另外,宋元明清时期民间所流行和官方所旌表的孝行与中古时期并没有多大区别,无非还是“亲存亲殁能尽礼”,比如:
“亲存,奉侍竭其力;亲殁,善居丧,或庐于墓;亲远行,万里行求,或生还,或以丧归”;“或遭家庭之变,能不失其正;……或为亲复仇,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或吮疽尝痢,或乞佣养亲,或自鬻葬亲,学老莱子作孺子婴儿状悦父母者也大有人在。
总之,视孝道为人生之全部意义的孝子们为尽孝而挖空心思地自摧、自惨、自虐,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和社会启蒙思潮中,封建孝道中也注入了若干积极的因素。例如黄宗羲的孝道观中就浸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针对曾子“保身”的孝道主张,黄宗羲认为,守孝道应该“如城守之守。父母生我,将此降表之理,完全付我。……故须血战孤城,待得夕死,交割还与父母,始谓之全归。
不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已矣。”也就是说,为抗击外族侵略,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生取义,这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才是大孝。
王夫之从“辱大臣为辱国”的角度提出:“子之于父母,可宠、可辱,而不可杀。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宠辱听命而不惭。至于杀,则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为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为子也。臣之于君,可贵、可贱、可生、可杀,而不可辱。”袁枚对“郭巨埋儿”的尽孝方式进行可激烈抨击,嗤之以“贪诈”:“不能养,何生儿?既生儿,何杀儿?……杀所爱以食之,是以犬马养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杀子则逆,取金则贪,以金饰名则诈,乌孝乎?”戴震的批判尤为激烈,他认为愚孝之论是以理杀人,比之酷吏杀人更为残酷恶劣:“尊者以理责人,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种前所未有的理性反思,在大力倡导愚忠愚孝的专制时代,无疑是振聋发聩之论,也是近代文化批判中检讨孝道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