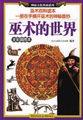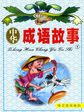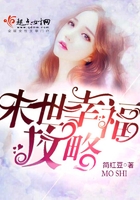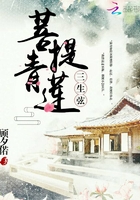一一朱熹依然沿袭二程的观点,他讲:“有这性,便有这仁,仁发出来,方做孝弟”,仁就理就性上说,孝弟就事就用上说,“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后有是孝弟”,“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发出来底。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仁乃是性中之事,孝弟乃是仁性之发用。性中只包含仁义礼智,并没有孝弟尊贤之类,但孝源自于人之仁性:“孝根原是从仁来。仁者,爱也。爱莫大于爱亲,于是乎有孝之名”。“孝弟满体是仁。……若说孝弟非仁,不知何从得来。”仁可发而为各种德行,如在父则为孝,在君则为忠等等,孝弟只是仁性中的一事而已:
“百行各有所属,孝弟是属仁者也。”自亲亲至于爱物,都是性之用、仁之用:“道理都自仁里发出,首先是发出为爱,爱莫切于爱亲,其次便到弟到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于他,都从这里出。如水相似,爱是个源头,渐渐流出。”若不以仁为根、为源,则孝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粟之苗,无根之木,“譬如一粒粟,生出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为孝弟之本。”“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发得孝弟出来,无仁则何处得孝弟?”若是把孝弟唤做仁之本,就是本末倒置,把枝叶当作了本根。
正因为孝弟与仁性不二,所以当有人问为何“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时,二程回答:
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事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至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故举孝弟,是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时非无孝弟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2.“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
孔子对孝作为行仁根本途径的论证,总体上偏重于实践的方面,或者说,主要是从形而下的道德实践层面来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程朱承认而且强调孝乃是为仁、行仁之本。二程指出,“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于其家,而后仁爱及于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弟是行仁的起点,“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谓孝弟为行仁之本则可”。朱熹继承二程的仁孝观,认为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他把仁比作水之流,孝则是流水所必经的第一池,“仁如水之源,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三坎也”。行爱行仁自亲自孝始,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亲亲是第一件事。朱熹重点重申了“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的儒家传统观点:
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
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如亲亲,仁民,爱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须先从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
又如木有根,有干,有枝叶,亲亲是根,仁民是干,爱物是枝叶,便是行仁以孝弟为本。
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但是爱亲乃是切近而真实者,乃是仁最先发去处;于仁民、爱物,乃远而大了。
朱熹还在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说,孝弟不仅是仁之本,也是义、礼、智之本。他说:“只孝弟是仁之本,义礼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亲从兄得宜者,行义之本也;事亲从兄有节文者,行礼之本也;知事亲从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舍孝弟则无以本之矣。”
“知得事亲不可不孝,事长不可不弟,是为义之本;知事亲事长之节文,为礼之本;知事亲事长,为智之本。”王阳明则以树之抽芽来形象地比喻孝对行仁的本源价值:“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孝在儒家哲学中乃是一切仁心流行之根源”,因为“一切仁心之流行固可遍及一切,然仁心之起点,必原自一人始。”仁以孝为逻辑起点逐步扩展开来,最终达到物我一体、“民胞物与”的最高境界。这也正是程朱极力推崇《西铭》“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用意所在。
对仁孝关系,朱子一言以蔽之日:“‘为仁以孝弟为本’,这个‘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为孝弟之本’,这个‘仁’
字,是指其本体发动处言之。”总之,不论如何,如同“性即理”一样,仁与孝弟也是相通无碍的:“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见于事。”尽得仁之理,方可尽得孝弟之行;有了孝弟的自觉行动,才能达到和实现仁:“尽得仁,斯尽得孝弟;尽得孝弟,斯尽得仁。”
三、从认识论上为孝道提供哲学基础
理学家认为,理是万物的原理和原则,是事物之“所以然”。理及其所体现的孝道等伦理纲常是认识和实践的客体;穷究天理,臻于至善,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修养的最高目标。人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先验的天理;人的实践,就是要践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人的修养,就是要使自己的行为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封建纲常伦理之矩的境界。
(一)格物致知理学家把“明庶物”与“察人伦”结合起来,所谓“格物”,“格”的对象,即认识的对象虽然并不排除草木虫鱼等物理,但归根结底重点是后者,即忠孝仁义等事理。这是因为,求学明理的“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爱亲敬长为先”,若只务观物理,则如游骑无所归。
因而,程朱要求人们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道求理,即穷究三纲五常之理。
所谓“致知”,即认识的目标,“便是要知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知止,只是知有这个道理,也须是得其所止方是。……知止,如知为子而必孝,知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亲为忠孝之事。”而格物的极至就是践履三纲五常、孝悌忠信:“至言仁则当如尧,言孝则当如舜,言敬则当如文王。”即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知至,谓天下事物之理知无不到之谓。……谓如亲其所亲,长其所长,而不能推之天下,则是不能尽之于外;欲亲其所亲,欲长其所长,而自家里面有所不到,则是不能尽之于内。须是其外无不周,内无不具,方是知至。”也就是要达到张载所谓的“民胞物与”的崇高境界。
为通过“格物”而实现“致知”,程朱还提出了类推的方法:“格物非谓尽穷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以孝为例,朱熹指出:“尽得个孝底道理,故忠可移于君,又须去尽得忠。
以至于兄弟、夫妇、朋友,从此推之而无不尽穷,始得。”类推到一定程度,就会脱然领悟,豁然开朗,“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从而达到认识的理想境界:“遇事触物,皆撞着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亲便遇孝,……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这就实现了认识上的贯通和实践上的自由,从而完成了对形而上的天理的体认。
(二)知先行后。
程朱还提出了认识过程中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里的“知”和“行”主要是指道德认识和道德践履。
从先验论出发,程朱认为理在事先,认识事物必须先认识事物的理,否则就会如瞎子摸象,无所适从,甚至迷失方向而误人歧途: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不致知,如何行得?勉强行得,安能持久?”若不明道德知识,纵使有最好的道德行为,也不值得推崇。
“行”必须以“知”为前提,比如欲行孝道,则必须先清楚为孝的道理,如何为孝,然后才能去尽孝道:“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所以侍奉如何,温清当如何,然后能尽孝道也。”朱子讲:“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若不学文,则无以知事理之当否。如为孝为弟亦有不当处。孝于事亲,然事父之敬与事母之爱便别了。”这里,程朱看到了理性认识对人的自觉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但却把认识和理论的来源归为天理,而不知道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理学家不仅不否认行的作用,相反,他们极为强调道德伦理实践的重要性,认为行重于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既知此理,更须是审思而行。且如知孝于事亲,须思所以为事亲之道。”忠孝之道最终还是要落实在“钟鼓铿锵之节、进退揖逊之仪”之类的实际行动上。“若无事亲事君底事,何处得忠孝!”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孝之处,“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将此小心依古礼而行之。”程朱认为道德践履是道德认识的目的。若没有事君孝亲的行为,则满腹经纶、满口忠孝皆是徒然无用的,“若徒知这个道理,至于事亲之际,为私欲所汩,不能尽其孝;事君之际,为利禄所汩,不能尽其忠,这便不是能得矣。”朱子有时也把“知”放在具体的“行”之后,如他认为曾子之所以理解孔子的忠恕之道,是因为他“遇事必反诸身,所谓孝,所谓礼,必穷到底。若只守着个约,却没实处。”“件件曾做来,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践履,如何识得?”可见,程朱所谓的先于行的“知”,只是指那些先验的“理”,如三纲五常之类,并不包括具体的知识。
(三)诚孝与至善。
就道德修养而言,理学家特别强调“诚”。所谓“诚”,就是不杂一丝私欲,内外一致,表里如一:“诚是天理之实然,更无丝毫作为。”诚是孝中应有之意,“孝而不诚于孝则无孝,弟而不诚于弟则无弟。”为此,必须扫尽气秉之私欲,使胸次洞彻虚灵,方可臻于诚孝:“诚,实也。且如人为孝,若不实是孝,便是空所,无这孝了”,“不诚,是不曾有此心。如事亲以孝,须是实有这孝之心。若外面假为孝之事,里面却无孝之心,便是不诚矣。”圣人与天合一,自然“诚”,而一般人则须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直待得仁义礼智与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无非实理,然后为诚。”要通过“致曲”,即逐事上著其力,逐事上致其极的工夫,“件件致得到诚孝诚弟处。”程颢本人就是“诚”的典范。《明道先生行状》日:“先生得圣人之诚者也。……故推而事亲则诚孝,推而事君则忠,友于兄弟则绰绰有裕,信于朋友则久而不忘,修身慎行则不愧于屋漏,临政爱民则如保乎赤子,”程朱认为,若能于日用言动中涵养至“诚”
的境界,就离天理不远了:“理之实然者,至简至易。既已至之,则天下之理,如开目睹万象,不假思虑而后知,此之谓诚则明。致知以穷天下之理,则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简易实然之地,而行之所无事,此之谓诚则明。”
理学家还把孝感说融入其理学体系当中,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理学家看来,孝悌神明不二,孝悌之行中就有神明之理在,而“诚”则是孝悌神明贯通合一的中介。匹夫至诚感天地,人们只要能够诚心诚意地行孝,自然就会感格神明,昭彰天理。二程日:
“事天地之义,事天地之诚,既明察昭著,则神明自彰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神明孝悌,不是两般事,只孝悌便是神明之理。”比如针对王祥孝感故事,程朱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天理道德,神明感格就是从王祥的孝的至诚中来的:“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诚中来,非王祥孝于此而物来于彼也。”孝感虽然是自《孝经》、董仲舒以来封建孝道的传统观念,但理学家的论说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这是封建社会后期愚孝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格物穷理、修身养性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达到“至善”。所谓“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也”,“至善是个最好处”即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且如孝,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虽然是孝底事,然须是能‘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方始是尽得所谓孝。”程朱认为,自君臣父子推之于万事,无不各有所止,至、止,都是言要到那极至处而后止,“如欲为孝,虽有七分孝,只中间有三分未尽,固是不实;虽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尽,亦是不实”。人子“须要如舜之事父,方尽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尽,便是道理有欠阙,便非子之道矣。”朱子进一步举例说:
孟子说“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此是不孝。到得会奉养其亲,也似煞强得这个,又须著如曾子之养志,而后为能养。这又似好了,又当如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不遗父母恶名”,使国人称愿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于尊亲,其次能养。直是到这里,方唤做极是处,方唤做至善处。”
“至善”中还包含着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精神在内,也就是朱熹所谓“只恰好地便是”,既不能未当止而止,也不能当止而百不止,“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当然之则。不及固不是,若是过其则,必有到股之事。须是要到当然之则田地而不迁,此方是‘止于至善’。”程颐认为尧舜之行是孝弟的极至:“孝弟非尧舜不能尽。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至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四海,非尧舜大圣人,不能尽此。”不难看出,所谓“至善”,无非就是忠孝仁义封建伦理秩序。
总的来看,理学家对孝道的哲学论证主要是围绕着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展开的。
天道和人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终极性支柱,它们是一切理论、观念、价值、行为规范合理性的来源和依据。“天”是一个有意志的道德实体。从本质上看,“天”是人间生活的写照,天的道德属性来源于人伦之理,天道秩序是人伦秩序的“副本”;但从形式上看,天道又高于人道,人道来源于天道,因而“天”常常被置于人道之上,作为最终极性的价值根据。于是,把人道上升为天道,上升为神圣的先验的本体,然后再从天道中派生引申出人道,就成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下思想家们惯用的思辩技巧,而天人合德,即伦理是由人性决定的,人性又是由天即自然决定的,就成为儒家道德思想的理论基础。道德理论、伦理规范若能被追溯为天道和人性,便获得了神圣不可怀疑的支持。这正是历代思想家论证孝道合理性的方向和目标。
由孔孟经董仲舒到理学家,对孝道合理性论证的一脉相承性,就表现在他们都是试图由自然法则的实然中,推导出孝道的当然。
如果说,孟子沿着感性经验的途径,把孝道奠基于人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良知良能,即人的善性,其根据因缺乏理性而不够理直气壮;《孝经》中孝道“天经地义”性的逻辑推理环节被付之阙如;董仲舒循依天命论传统和阴阳五行为孝道张目,从宗教性的“天”中找寻道德根源和道德信仰的力量,其神学色彩又过于浓厚;那么,理学家从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对孝道的先验性、客观性、永恒性所作的哲学的、理性的、系统的、精致的论证,从客观法则与内在法则即天理与人性的结合上,给孝道提供的坚实的形而上基础,则克服了几者的弊端,消除了孝道来源理论上捉襟见肘的窘迫,使孝道的合理性、神圣性具有了天经地义、不可辩驳的性质,行孝完全被视为自然而然、勿庸置疑的事情。孝终于无懈可击地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更确切地讲,孝终于被思想家熔铸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从此,孝道只是被当做天然合理的规则来遵循,再也没有人去追问它的价值依据所在。这就是封建社会后期愚孝泛滥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