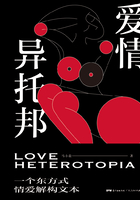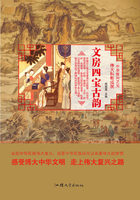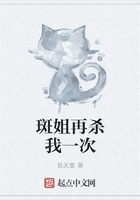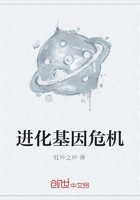汉承秦制,专制国家操纵对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法禁复仇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法传统很快就在封建制的庞大躯体内找到新的生长点,封建宗法制粉墨登场,复仇观念得到新的权力和理论支撑。儒家将作为原始心态孑遗和个体情感冲动的复仇意识与传统宗法制度相结合,赋予复仇以亲情孝道的伦理内核和肯定性的道德评价。儒学的独尊,礼对法的干预,法向礼的屈从,更使复仇者赢得了合法的道义依据。唐代荀悦云:“复仇者,义也”,直到王夫之还认为:“父受诛,子雠焉,非法也;父不受诛,子弗雠焉,非心也。”所以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重视复仇,因为有时这是完成孝道所不能或缺者。”
儒家的亲亲、尊尊原则是复仇制度的伦理基础。按照儒家的宗法伦理,五伦亲疏等差观念决定了报仇责任轻重缓急的不同。
五伦之中,君最尊,父最亲,所以,《公羊传?隐公十一年》上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礼记》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若居父母仇未报,则“寝苫枕块,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复仇的主导动机是尽孝,复仇成为尽孝的极至。儒家带有强烈宗法家族主义色彩的复仇观,奠定了复仇意识作为传统文化心态有机组成部分的根基。
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社会心理所普遍接受认同,复仇意识深入民心,复仇之风甚嚣尘上,“俗称豪健,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仇怨结,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以至于汉人把“怨仇相残”列为汉代百姓七大死亡原因之第五。汉章帝建初年间,有孝子为复父仇而杀人,章帝免去其死刑而予以宽大,以后发生的类似案件,均依此从轻发落,并由此而形成一个正式的法律——轻侮法。轻侮法的实施,使正在蔓延兴盛的复仇风气愈发不可遏制,“‘轻侮’之比,寝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和帝时不得不诏令废止此法,恢复杀人者死之旧制。
二、法律对复仇的禁止和纵容:礼与法的冲突
在诸多的复仇案件中,为父复仇作为礼法冲突的焦点,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种。据统计,汉代已知的为父复仇的有26例,男子所为22例,女子所为4例,其中最有名的却是赵娥的故事。赵娥杀死父仇后诣县自首,在守尉预备弃官解绶而释放她的情况下,她却执意不肯贪生以负朝廷,“偷生以枉国法”,情愿为“肃明王法”而“陨身朝市”。礼与法的冲突开始凸显。
连卑微民女也深知复仇与国法的不相容,可见汉代法律是绝对禁止此类行为的。以后列朝也多次为此颁布诏书,屡加严禁。
如曹操、魏文帝、梁武帝都曾诏令禁止复仇,魏律对于复仇的处罚重至诛族,北魏律对于复仇者的处罚更严酷,诛及宗族和邻伍。除元律外,唐宋以后的法律也都严禁复仇。明、清律稍加变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后,若子孙出于激忿而立即将凶手杀死,则无罪;若事过境迁再杀仇人,则要论罪杖六十。总之,在生杀权操于主权的封建君主专制下,“国家设法,焉得容此?”禁止私人蔑弃国法、擅自杀人复仇乃是各朝政府必然和一贯的选择。
严惩私自复仇,是法律禁止复仇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还通过法律手段消极地从各方面防范复仇事件的发生,以回避孝道与国法的矛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杀人移乡”避仇的规定。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已经伏法的凶手,虽然国法已伸,私恨已泄,但若有幸遇上大赦,惟恐被害人家属于心不甘,为避免再度复仇,遂制定此法。移乡避仇与周代“调人”所司显然是一脉相传的。另外,自秦汉至清代,对复仇均有种种限制条件,力图使之回归并遵循公正的原则,同时把生杀之权牢牢地把握在国家手里,如“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是两千年封建社会复仇制度中不可动摇的原则。
又如“杀人而义”、“父受诛”,既父获罪该杀,子不得复仇;过失杀人,不得复仇;已受国法制裁、逢赦免者不得复仇;复仇对象只限于仇人本身,不能滥杀无辜,等等。
既然历朝政府都三令五申禁止复仇,甚至对复仇者严加惩处,为何人们依然对此置若罔闻,收不到杀一儆百的实效呢?
这是因为,首先,最主要的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宗法制国家。按照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为成仁可以杀身,为取义不惜舍生,“孝”为仁义之首,百行之先,若对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视而不见,则何以为人?何以面对列族列宗?
何以有面目立足于世?若不为被人所杀的父母复仇伸冤而荀且偷生,则不但于情于理所不容,而且为世人所谴责和不齿。在这种情况下,有父母仇者除了为报仇雪恨而以身试法、为成全孝道而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外,别无选择。其次,在以孝治天下的社会氛围下,为行孝道而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就使复仇行为本身染上了一抹悲壮、亮丽的色彩,“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因而极易博得舆论的同情和赞誉,甚至获得执法者的矜怜和宽宥,更何况在许多执法者看来,“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另外,作为人类最具恒常性质的恩怨情感纠葛,血亲复仇意识中正义对邪恶的无畏讨伐,经过先秦儒家的伦理定位和理性阐释,逐步酝酿产生了以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为表现模式的复仇主义文学主题。对邪恶的鞭挞,对正义的向往,对复仇者的同情、褒美和讴歌,是复仇文学,特别是武侠小说的核心内容。这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普遍的复仇心理,造成了有利于复仇者的社会氛围。
道德的自我肯定和社会的赞许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如果说,从道德的自我肯定讲,尚有孝子迫于孝道伦理的内在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外在压力,从而不得不选择复仇的话,那么,社会的赞许,即众人的誉美褒奖、法律的宽大处理、圣上的赐爵赏物,无疑等于对复仇行为的纵容、鼓励和怂恿,从而使居父母仇的孝子们更加有恃无恐,并且义无返顾、甚至怀着一丝侥幸奔赴复仇之途。复仇的习俗本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再加上孝道伦理的深入人心,朝廷官吏的宥赦纵容,这样,即使朝廷三令五申,法律严惩不贷,仍不能根绝复仇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从历代正史《孝义传》、《孝行传》皆载有为父复仇的孝子事迹来看,各朝政府也从来没有真正去禁止复仇,复仇禁令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在《清史稿?孝义传》中,我们还看到十多个为父复仇的孝子案例。复仇事件的屡禁不止,原因盖在于此。
当然,复仇本是一种自发性的惩恶行动,它带有蔑视政权法律、无视官吏权威的意味,若自首则表达了对法律、权威的尊重,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既尽了一个孝子复仇的伦理义务,又尽了一个臣民守法的责任,“挥刀酬冤,既申私礼;系颈就死,又明公法。”所以复仇者受宽宥一般是以自首为前提的。
复父仇而被宥的案例历代皆时有所闻,即使在法律严惩复仇的时代也不例外。例如前引赵娥复仇自首后,乡人“为之悲喜慷慨嗟叹”,“海内闻之,莫不改容赞誉,高大其义”;汉郅恽替友复父仇后坦然就狱,县令为其倾倒,竞至以拔刀自杀相要挟,逼令郅恽出狱;晋代桓温因手刃父仇而扬名光祖,一时尊宠无比;魏孙男玉、孙益德、刘宋钱延庆、隋孝女王舜、唐王君操、梁悦、宋刘玉、金张锦、明何竟等等,举不胜举,书不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