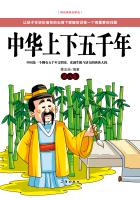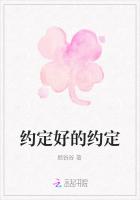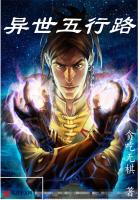还有一个父亲要求将亲生儿子断足流放到蜀郡边远地,叫他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刘宋法律,“母告子不孝,欲杀者皆许之。”唐时李杰为河南令,有寡妇告子不孝,其子虽然并无不孝行为,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李问寡妇是否后悔,寡妇日:“子无赖,不顺母,宁后悔乎?”父要子死,子不死为不孝,不孝还是必须死。这样,伦理上的“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这就是封建法律所维护的父权。清代父母还有呈送发遣之权,即要求官府将其不孝子女发配之云贵或两广。这一类的犯人为常赦所不原,但若父母呈请,则可望得到释放,“凡触犯祖父母、父母发谴之犯,遇赦,查询伊祖父母、父母愿令回家,如恩赦准其免罪者,即准释放”,以顺衰老之情。从清代遗留的案牍中,可以看到父母呈送触犯之案多系情节较轻者,大抵是因不服管束、酗酒滋事、出言顶撞或偶缺供养、窃父母钱财一类小事。父母借助法律的力量,可以剥夺或给予子孙身体的自由。于此可见,个人是完全属于家族、属于父母的。
除了法律条款的明文规定外,引经决狱、原心援情定罪量刑的法律操作活动,也无不以孝道为准绳,即所谓为孝屈法。《旧唐书》
说:“《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劝之,慎测深浅之量以别之。”如唐长庆二年,对为救父而杀人的康买得一案,即原于孝道而从轻发落:“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明史?
刑法志》也说,立法断案要“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对一些出于孝道却触犯法律的案例,司法官员在决狱时,往往曲法全孝,或以疑狱上报,最终多得到宽宥赦免。接下来就要讲到的为父复仇问题中,更突出地表现了法律对孝道的屈就。
(第三节传统法律对“不孝”的惩罚
与“孝为百善先”的伦理观念相对应,有“罪莫大于不孝”的法律意识。因而,惩罚“不孝”,就成为保护孝道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内容。
资料显示,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宗法制农业文明国度里,以“不孝”为罪,并对不孝行为实施法律上的制裁,是很早的事情。迄今为止,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成熟文字可考的朝代。《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说:“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如果此说可引以为据的话,则说明商朝已经定“不孝”为罪,只不过这时“孝”的对象不是祖父母、父母,而是已死的祖先神而已。从神治时代的殷人对于鬼神的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推测,殷人对亵渎祖先神的不孝行为施以最严酷的惩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西周时期,“尊尊”、“亲亲”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的指导思想,所以“孝”自然也就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而且,由于西周主要依靠以孝为基础的宗法道德来维护其世袭统治,所以“不孝不友”被看作“元恶大怼”,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如《周礼》列“不孝”为“乡八刑”之第一刑,从而开创了以刑罚手段来维护宗法伦理的先例。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宗法道德以孝为本的基本精神,一方面把“孝”提升为众德之本、百行之先,另一方面,视“不孝”为大逆不道,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法家也主张以威严、暴力等高压政策来“禁暴止乱”,包括以法律手段惩戒不孝,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秦建立后,沿着严刑峻法的方向将法家学说推向极端,秦始皇独操权柄,对不忠不孝者自然不会心慈手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不孝罪处死的规定,殴祖父母、曾祖父母,“黥为城旦舂”,即受黥刑并到筑城的地方舂米五年。当然,秦律处死或重惩不孝,只是为了威吓儿子服从父亲,以利于安分守己地耕战纳租。由两汉至于清代,历代封建王朝都竞相标榜以孝治天下,并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致力于礼法结合,所以“不孝”就被正式定为罪名列入律书。汉代萧何所作《九章律》祥细内容已不可考,但汉律中有不孝罪却证据确凿。汉武帝时,太子爽等人“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即为其例;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载有关于处置“不孝”的律文:“孝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这显然是对秦律的继承。由此看来,《礼记》所言“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当为时人及后人的普遍观念。魏晋以“不孝”罪名处死或贬谪者更是比比皆是。《魏书》载,高祖十一年诏日:“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遂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南朝刘宋律规定:“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纳“不孝”罪于其中第八,成为“十恶”之罪的雏形,也是后世法典的重要内容。北周、陈律中也都有“不孝”之罪。隋<开皇律》正式确定了“十恶”之罪名,“不孝”列第七。此后“不孝”就成为“十恶不赦”的重罪,标明于卷首的名例中,“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沿用“十恶”罪名。《唐律》中,“不孝”
仍被列入“十恶”罪之第七。《唐律疏议》明确地规定了“不孝”的内容及相应的刑罚,即下列几项:
1.“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
子之事亲,有隐无犯。若父母有违失,理当谏诤,无使其陷于罪恶。所以,《唐律》规定,除祖父母、父母犯有谋反、大逆、谋叛等罪可例外开禁之外,至若其它罪责,子女若忘情弃礼而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元英宗时,斡鲁思攻讦其父母,驸马许纳的儿子速怯告揭发其父亲谋反、母亲跟人私奔,英宗日:“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复讦于官,岂人子之所忍为?”遂下令斩首处死。明清律对子孙控告尊长的所谓“干名犯义”罪的处罚较前代稍轻,诬告论死,得实则杖一百,徒三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规定,虽然控告尊长、干名犯义的子孙要受刑,但被告的尊长则同于自首而免罪。这就使子孙可以为免陷亲于刑戮,不惜以身触犯告言父祖之律,换句话说,这就给子孙以死救亲尽孝提供了机会。法律为保护孝道,真可谓殚精竭虑、面面俱到了。子孙詈骂祖父母、父母者,也要处以绞刑。明、清律甚至把“骂詈”专列一门,不仅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连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也“并绞”。
2.“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礼记》上屡屡提到“父母在,不有私财”,禁止子孙拥有私有财产,可以说是儒家礼治的一贯要求。《唐律疏议》认为,子孙本应出告返面,就养无方。若有异财、别籍,则“于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此俱沦,情节于兹并弃”,所以罪恶难容。宋代有时处罚更重,可以论死。明律在这一条上稍微宽松些,经祖父母、父母告诉始受理,且只是杖一百,清律杖八十。同居卑幼若无家长应允,擅自使用家庭财产,要按所动用的财物的价值当笞杖之刑。为保护家长财产,《大清律例》还特别规定:“有服卑幼图财谋杀尊长、尊属,各按服制依律分别凌迟、斩决,均枭首示众。”
3.“若供养有阙。”
赡养父母乃是孝道的基本要求,如果家道“堪供而故有阙”,能赡养父母却不尽为子之道,只要“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4,“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
“作乐”指自己或遣人击钟鼓、弹丝竹之类;“释服从吉”指丧制未终,就换衰裳为吉服。依据唐律,居父母丧的二十七月内,身自嫁、娶者,徒三年。释服从吉、忘哀作乐,徒三年,即使遇乐而听者,也要杖一百。居父母丧生子,即在居丧的二十七月内妊娠生子者,以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5.“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由于父母之丧“创剧尤切”,所以“闻丧不举”之罪流二千里。
若诈言余丧不解官居丧,则徒两年半;妄称祖父母、父母死,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孙及妻妾作乐者,以其不孝、不义罪而徒一年半。
6.殴毙祖父母、父母,杀无赦。
“十恶”中的第四条“恶逆”,是情节最为严重的不孝行为,即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父母之恩,昊天罔极。……五服至亲,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甚至连“诅欲令父母死及疾苦者”,也“以谋杀论”,为“恶逆”罪。犯此罪,除元律规定殴伤者处死刑外,各代都是不论故杀误杀,不论有伤无伤、伤势轻重,只要有“殴”、“杀”的行为,一律斩而不赦。如清律规定,“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案件,审无别情,无论伤之轻重,即行奏请斩决。”若殴父母致死,元、明、清律加至凌迟处死。唐宋明清律,过失杀父母者,流三千里;过失伤者徒三年。乾隆时定例,过失杀父母者立绞;殴死父母者,即使已经畏罪毙命,也要以尸示众。同时,明律规定,若子孙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则依殴祖父母、父母罪问斩。清律更具体地规定,若因子孙触忤干犯以致祖父母、父母自尽者,斩决;若因违反教令而使祖父母、父母轻生者,绞候。有这样两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案例:
某甲因不听母亲喝阻,其母欲禀官送究。甲苦苦哀求,其母不允。赴县呈控后,其母又追悔莫及,投井自尽。甲因此而被判绞监候。
刘某平日极为孝顺。其母索要非分之财,刘某力谏不果,遂私自凑钱退还,其母得知后羞愤自杀。按律应拟绞。后来实因情有可原,才“照违犯教令致母自尽例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即使父母并非故意寻死,只是无意跌毙,只要起因于子孙,子孙也仍要负同样的刑事责任。这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观念在法律领域的典型体现。
综观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罚,皆采取加重主义的原则,即所谓“‘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谓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才听其曲直之辞,对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都严惩不贷。例如依前所讲,骂人在常人不算什么,但骂祖父母、父母,则要处绞;常人过失杀伤罪可以收赎,但子孙过失杀伤祖父母、父母则科以重罪。皇帝在对不孝罪的申报批复中也往往任意加重刑罚。如唐代京官李均、李锷兄弟,二十余年不回故里,母死不报,被宪司上报后,皇帝令处以当时早已经废止的车裂之刑。这正是儒家家族主义、伦理本位原则在法律领域的体现。
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家法族规。家庭、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法律赋予族长、家长以治族、治家的特权。《唐律疏议》开篇总论就引古语日:“刑罚不可弛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家法族规同封建国家的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家规族法除了维护家族内部秩序、调整族里关系、履行国家的包括法律义务在内的诸项义务外,还用严厉的惩罚手段从道德思想上控制着家族成员循规蹈矩,不犯上作乱。在维护孝道方面,有时甚至起着国法所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权鞭长莫及的的法律真空地带,如闭塞的边隅山区,家法族规更是惩治非礼、禁恶扬善的主要手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不孝的处罚。例如安徽《刑氏家谱?家规》日:“若有不孝舅姑、不和妯娌,……必惩之。”《江西临川孔氏支谱家规条例>:“诛不孝。不孝之罪:游惰、博奕、好酒、私爱妻子、货财与好勇斗狠、纵欲,皆不孝之大。一经父母喊出、族长察出,重责革并,犯忤逆,处死。”借助法律的强制,家与国进一步沟通,伦理和政治进一步结合,家(族)长既是家族内的立法中,又是裁判者,父权和族权完全成为专制王权的缩影。
(第四节 为父复仇:情与法的冲突
礼法都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出礼则入刑,即举凡悖礼、违礼的行为,也就是违法的行为。这表达了情与法、刑与礼的统一,也是法律儒学化的旨归。但是,法律和伦理同归而殊途,它们毕竟分属于两个领域,具有不同的形式、标准和特点。法律规范注重人的社会性,旨在调整普遍存在的一般社会关系;伦理规范则适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并赋予关系人一种超社会的亲情义务。
因而,伦理和法律在实现各自功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历代法律,尤其是《唐律》,把以礼人律作为解决亲情与法律冲突的基本途径,并用一系列法律条文规定作为处理孝道与国法矛盾的基本模式。但是,繁缛的律文在多样复杂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一切努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矛盾的客观、必然存在。为父(母)亲复仇,就是典型的虽违法却合礼的行为,它集中体现了家族与国家、孝道与国法的对立,是一个令历代统治者都伤脑费神,却始终没能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
一、血亲复仇的渊源
“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复仇的观念和习惯,普遍地存在和流行于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中,由个人复仇到家与家、族与族之间的复仇,规模大小不一。远古时期,复仇甚至是一种为子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例如印第安人的复仇观念如同宗教信仰一样牢固而神圣;在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子不报父仇,是不能享受继承权的。历史上的希腊人、希伯莱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都允许复仇;古代许多国家象罗马、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也都曾有过准许复仇的法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一个缺乏政治力量维持公正的社会中,只能允许私人自行平冤矫枉,“以直报怨”,寻求公正的赔偿。因而复仇本身就带有正义的性质。当国家的权力发达到足以主持公道、限制自救时,禁止复仇的法律才会出现。
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血亲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社会习俗,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约定俗成的正当报复行为。
上古时代的文献中依然保留着许可复仇的记载。唐代韩愈说:“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西周宗法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不仅使作为氏族社会孑遗的血亲复仇之风延续下来,而且使之得到了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说明,得到了国家政权和法律的合法性保护。《周礼》对于报仇有专门的规定,有法定的手续,即只要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然后再杀之,就可无罪(反复复仇者无效)。西周还设有专司避仇和解的官职。《周礼》云:“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兄弟。”《周礼>同时还规定“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复仇的原则一般是:
父不受诛即父罪不当至死而死,为子是可以为父复仇的,如伍子胥躬耕待时,志在雪父兄之仇;父受诛即父若犯死罪,则不准复仇,否则必然招致反复仇杀。法律的许可,更助长了一直延续不绝的复仇风尚,至战国后期,复仇依然蔓延风行于东方诸国。孟子所谓的“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就是对当时复仇状况的真实描述。唯有法家强调国家法律高于一切,坚决反对复仇。及至重刑法而轻经义、行专制而蔑人伦的秦一统天下,给奴隶制宗法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一度使与宗法制相伴的复仇风尚几近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