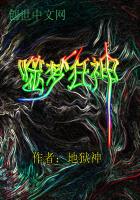太常寺的人只是赔笑,说给上官妃添麻烦了,道歉的话说了一大堆。上官染烟也不好再呕下去了。毕竟是自己家里人不争气,怨不得别人。
等到那边人走了之后,染香又出去打探了一番,回来才告诉上官染烟,“娘娘,我听说是下午那会儿,长秋君去太常寺那边安排今年女官探亲的事情,听到那边殿所的动静,过去走动了一遭,老太太才走。”
说着又感慨道:“真是没想到呢,太常寺的人也说,长秋君小小年纪,没想到那般威势凛然,她人移驾过去,还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吓得嗖的一声消失不见了,动作那叫一个快。”
话说出口才意识到自己僭越了。那位老太太再怎么扶不上台面,也不能嗖的一声消失啊,那不成鬼了。再怎样,也是上官染烟的长辈。轮不到她说。
只能住口赔笑。上官染烟想了想,道:“那也是应该的,易总宪在前朝就以铁面无私著称,长秋君是他的女儿,风骨自然是有的。”
就想想当初能为了几千斤炭火地龙的事情,跟季游陌一板一眼的讲道理,又跟北辰郁秀莲闹冷战,就知道这位长秋君不是好惹的对象。上官瑾在前朝也算是威风八面了,偏偏她这个做妹妹的,没有跟人家争长短的心思。因此才被这么欺负着。
随口又问道:“季更衣也回来了么?”
染香回道,“下午那会儿就已经回来了,说是身体不舒服,进了偏殿就没出来过,照奴婢看,怕是没脸见娘娘了。娘娘这般照应她,还是没半点良心,拿那样的话说给娘娘找气生。我要是她,也不敢出来见人。”
“再怎样也是主子,轮得到你说三道四?什么家教?这话是我教你说的么?”上官染烟刚平下来的气,险些又被勾起来。
染香不仅是明成殿的主事女官,还是她从家里带过来的陪嫁。管事实怎样,在别人看来,她们两个都是一条心的。染香说什么做什么,哪怕是她自己的心思,别人也会想着一定是上官染烟指使的。上官染烟向来对她管束甚严,一时急了,话说重也是有的。染香早就习惯了,吐吐舌头,立刻闭口不言也就罢了。
上官染烟又叹口气道:“她说不舒服是吧?传太医过来给她看看吧。在这宫里,无外乎就是要讲个体面。管她怎样呢?咱们做事不能出错。万一真是病了,回头白招陛下责怪一场,何苦来的?”
天大的事情,也要用海一样深的涵养兜着。入宫这么多年,她早习惯了。同季妃共事,什么零零碎碎的腌臜气没受过,要计较,早就气吐血了,哪还轮得到算那口不择言的几句话的账?
打发染香去传太医之后,又将随太子一起迁过来的柳尚宫和太子乳母叫了过来,仔仔细细问了太子的起居,一整天,也没见哭闹过,吃奶也挺好的,药也是乖乖吃了的。内伤么,虽然还没有好完全,但太医也说了,脉象一天比一天强健,看来是稳稳当当往好的方向进展了。
大约是已经离去的小玫在保佑着这个孩子吧。太子搬过来也有两三天了。从没听见深夜哭闹扰人过。白天什么时候去看,也见他乖乖的躺在摇篮里玩自己的。给药就喝,喂奶也是按时按点按量吃着。半分麻烦都不给人添。
从前还听北辰郁秀莲说太子挺能闹腾的,小玫在宫里的时候,从来也不曾去看过他,旁的人怎样哄也哄不好,又怕生人,又怕吵。为了这些缘故,上官染烟还特意将明成东正殿那边清空了,只让原来出身东宫的伺候人照料,殿内的人,但凡走到东正殿附近,都得轻手轻脚不得发出任何惊扰的声音。但如今却听说,自从搬到这边,太子乖得跟换了个人似得,连哭都没有再哭过。
明明还不到一岁,还是个无知无觉的婴儿,但好像,是真的什么都有数似得,大概知道母亲已经不在了,再闹,也得不到那个人的怜惜了,因此连哭都懒得哭了吧。
早前就听钦天监的人说,太子是北辰廉贞,天命之君。看来是有些道理的,要不然,怎至于还在襁褓之中就这样心思灵透,明明不会说话,却像是什么都知道。
上官染烟从前也是看过孩子的,钟情生下来之后,虽然没有在她身边养着,但是身体虚弱,三天两头生病,连太医都说周岁之前凶险万分,让她担足了心事。如今长得大一些了,身体也渐渐好转了,上官府那边隔两三个月,还是会叫乳母进宫来,同她讲一讲孩子的近况。这样一直提心吊胆挂念着,才像是母女的情分。
如今北辰郁秀莲将太子交给她,便是有养子的名份了。这么个可恶的小婴儿,住在明成殿,安安静静就跟不存在似得,存心不让她操心劳累,反而觉得冷淡疏远了。
谁知道呢,也许只是她多想,同一个婴儿,又能讲出什么道理来。
话问到差不多的时候,御医也传过来了,在偏殿那边给季游陌请过脉,过来报给她,说是季更衣身上有内伤,大概心脉与肺脏都有受损。因为伤势来源有些古怪,不好对症处理,因此,只能以温补的汤药暂且养着了。
上官染烟听了,说让染香拿张纸进去,叫季更衣自己写个方子,送太医院抓药过来,她亲自熬就行了。
心里明的跟镜似得,不就是受到了咒法的反噬么。简直是活该来的。但上官染烟终究心软,不愿任由她忍受折磨。
她自己并不怎么修习术法,因此也没有受过反噬之苦,倒是从前照料他哥的时候见过。是挺难受的,连她哥那样强硬的人,都会忍不住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想想季游陌那纤弱的身子骨,如何受得住?居然还觉得她满可怜的。上官染烟自己都想着自己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药方子送过来了,杜太医又犹豫道:“娘娘,方才老臣为季更衣请脉的时候,隐约总觉得,脉象似是有些滑脉的感觉。可能是有喜了,但胎象不是十分明显,老臣也不敢确认。”
上官染烟不由怔住了。
叹口气道:“杜太医若是不能确诊的话,就再传宣太医过来一起看看吧。”
宫里的老太医统共就那么七八个。其中贵为院判,且资历最老的,也就郑太医,宣太医,杜太医,陈太医四位。郑太医年轻的时候,受过长秋君祖父的栽培,医术最好,亦最得皇室信任,是太医院首座,如今年事已高,又蒙主上隆恩,准了无事不必上宫进太医院,因此只请天子的脉。陈太医与皇甫世家是世交,多数时候是照管皇甫家的人。至于杜太医,则是专门为正妃请脉问诊的,若不是看在上官染烟的份上,眼下季游陌生病,都没资格请他过来。至于宣太医,则是产妇人科方面的名医圣手,遇到生产上有关的事情,才需要叫他过来。当年上官染烟生钟情,小玫生太子的时候,都曾仰仗他的医术。
以季游陌如今的身份地位,叫两位院判过来会诊,可见上官染烟待她真是仁至义尽了。即便如此,也是只求自身无过,对得住良心就行,不图别人感激或者报答什么。
上官染烟这人品,基本上能打到满分了。也难怪这么些年,稳稳坐着正妃的位置。人么,若是原本没有什么野心,处事又已经做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就算不主动与别人争什么,旁的人,也必然难以撼动她的地位。
季游陌吃亏就吃在没有安全感上。没事总怕小玫抢了她的地位,上蹿下跳的折腾,到最后终究是坑了自己。
宣太医七十多岁了,眼看已经到了傍晚时分,早就下班回府了,又被跑腿的小厮从半路上给叫了回来。
心里有数,知道宫里这阵子没人急着要生孩子,用不着赶命一般的催,再加上又是年龄老迈的人,还得顾着自己的一把老骨头,生怕轿子颠着,一路上说了好几次让抬轿子的人动作慢些稳当些。这么磨蹭着,进宫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上官染烟心里放着偏殿里的事情,连晚膳都没有胃口吃。在殿内等着宣太医的时候,御膳房那边送过来的菜都凉了。
退回去,又再传了一次膳。老太医到的时候,正好赶上她吃饭。想到老太医半路被召回,想必也没有吃东西,存着体恤老人家的意思,就又叫御膳房那边加了两个菜过来。等宣老太医从从容容将饭吃完,再去偏殿问诊的时候,眼见季游陌流出来的血都已经将身下的锦榻浸透了。
问偏殿的伺候人,都说季更衣自己一直一声不吭的,以她们的身份,又不能近身伺候,当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宣老太医当即上前诊脉,探过脉象之后,只说:“上官妃不必自责太过,季更衣气血双亏,身体虚弱,脏腑又受重创,这个胎儿,原本是保不住的。与其千辛万苦养着,等到七八个月的时候,落胎更为伤人。现在这样没了,也是无可奈何的。”
失血过度的缘故,季游陌已经没有力气说话。宣太医叫了太医院的女医官过来,将锦被掀开,解开衣衫以白色宽绸束缚止血,又让季游陌靠在床边,熬了补血的汤药过来给她喝。
人虽没有力气,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的,知道孩子没了,又听上官染烟说让染香立刻遣人去持中殿那边将事情经过报给北辰郁秀莲知道。
她懒得理会别人,就静静躺在那里任人摆布着,心想北辰郁秀莲就算为之前的事情,再生气,经受了这样大的劫难,也该过来看看她了吧。
只要还能再让她见到北辰郁秀莲,她就有把握,能让北辰郁秀莲想起昔日旧情,哪怕只是一分一毫,都是翻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