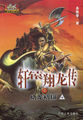朱淑真在魏夫人家里小住几日后,心情好了些,知道如今身份不同,身为人家媳妇,就必须事事顾及夫家面子,于是匆匆告别魏夫人,返回施家。
这时的施砾因为城门在修,并无多少事做,所以天天在家呆着。见朱淑真回来了,他冷冷地说道:“还知道回来呀?我还以为魏夫人会养活一你辈子呢,到头来还不是得回我们施家,哼,丢人现眼!”
朱淑真不理他,径直回房。
施砾最见不得朱淑真不理自己,他总感觉朱淑真是高高在上,轻视自己。所以,他一上子跳得老高,骂道:“摆什么架子!你以为有魏夫人替你撑腰,我就怕你不成?!”
朱淑真将房门关上,表情淡漠地整理旧词,看到自己先前作的不甚工整,便拿起纸笔,细加修改,改至满意时,一抹似有若无的微笑抚上脸庞,那抹笑令在窗外观颜察色的施砾大受刺激。
最见不得的就是朱淑真对自己的这种漠视,施砾忍不住火气,一脚揣开房门,进到房内,一把拉过朱淑真,强行施暴,被赶过来的魏贤赶紧拉开,平素吃喝风流的施砾并无太大的力气,被魏贤拉开后,他把怒气全施加到了魏贤身上,差人找来棍棒,对魏贤左右开打。朱淑真上前护住贤魏,骂道:“施砾,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自己不成气候,倒拿下人来出气!要打,打我吧!别欺负下人!”
施砾更加来气,他气哼哼地指着朱淑真说道:“你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怕了你!说到底,你还是我施某人的妻子,我的!我的!”
朱淑真此时异常镇定,每次看到施砾这般疯狂,她都感觉像在看戏,与已无关似的,不痛不痒,又万般好笑。
施砾见朱淑真还是不说话,说道:“你!哼!不守妇道的东西!等着吧,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大踏步地走进了二房的房间。
朱淑真被施砾最后的话骂得莫名其妙。
这时,魏贤从地爬起来,说道:“魏贤多谢少夫人救命之恩。”
朱淑真忙扶起他,问道:“快起来,你没事吧?”
魏贤揉了揉挨打的肩膀,回道:“少夫人,我没事。”想了想,又说道:“有件事,我要告诉少夫人。前几日有个书生模样的人来过府上,说是找少夫人。”
朱淑真问道:“可是我娘家人?”
魏贤想了想,说道:“好象不是,小人不曾见过他。不过听他说,好象是少夫人儿时的邻居。”
朱淑真听了,一脸疑虑,问道:“邻居?不是找错人了吧?”
魏贤回道:“我想不会,他走时还曾给少夫人留过一封信。只是......”
朱淑真见魏贤欲言又止,忙问:“信?在哪呢?”
魏贤回道:“我看到家丁把信给了二少爷,所以......大概,二少爷发火也是为了此事。”
朱淑真听了,冷笑道:“这有什么好火的?谁没有几个儿时的伙伴?”话刚说完了,她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这人,会不会是柳莫寒呢?可想了想,她很快又否定了,自己是亲眼见过他的名字在乱民之中被处决了的,就算他逃了出去,也不至于寻到施家来。
魏贤见少夫人不语,他说道:“少夫人,您还是好好想想吧,别真是亲戚却错失了。”
朱淑真听了,叹气道:“儿时已逝,哪还来的亲戚。算了,你下去敷点儿药,好好歇息吧。”
夜里,她却怎么也难入睡,那头二房跟施砾哭闹得厉害,惹得耳根难静。只好,披衣下床,脑子里词句凌乱,如同她的心情,写道: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