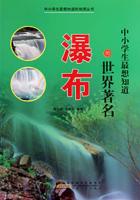叶子的飘落,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那段时间,网上很流行上面这句话。如果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的话,那秋天大概就是失恋的季节吧,或者,是生育的季节?
我觉得我差不多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了,而且精神也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的。这时候有个以前在成都见过面的网上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在贵州和爸爸开煤矿,很赚钱,现在缺一个得力的助手,问我有没有时间,能不能过去帮帮他,钱是小问题。
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刻去。我不想立刻投入到一天到晚跟钱打交道的行业里,进入那种行业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放弃自由放弃写作。虽然我明白自己迟早也会进去的,只要不死,棱角起早要被生活磨平。可是进去之前,四处走一走的自由我想我还是有的。
我去了长沙。那是七月末。整个长沙城像一个大蒸笼,走在街上,坐在房间里,总有一股子热浪包裹着你。连风扇里吹出的也是热风,只有空调下面会好一些。
但我还是在街上走着,虽然感到热,但并不见太阳,热浪不能将皮肤晒脱皮,不能将脸晒成古铜色,却可以让人发晕。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看到有人中暑,晕倒。可我却一直没晕倒。晕过去是什么感觉?我一直没有体会过。有时候,死的都是怕死的人。
离开长沙后,我又去了南宁。去的时候依旧是买的靠窗的硬座,依旧是我一个人,依旧是那个随身携带了六年的草绿色背包,包里还装着楚楚朵朵莫莫的照片,和染染的手机挂件。和染染分开之后我只留了她的手机挂件这一个关于她的东西。她的照片全被我烧掉了,她的模样我看一次心痛一次。
我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娇小瘦弱的少女,她怀里依偎着一只白色的和她的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耳朵小狗。那小狗看起来不像是特别名贵的品种,可是它无疑拥有这世上最纯洁的娇宠。人对动物,常常比对人要好得多。
我想起在盱眙的时候,和染染一起逛街,染染被路边的一群小狗吸引,执意要卖下那只白色的小狗,取名卡拉卡其。
把卡拉卡其买回来时它只有猪蹄儿那么大。卖狗的人说如果给小狗打上一针它就永远长不大。可是染染不愿意。我说等它长大了就会变得很丑,现在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随便带到哪里,等它长大了你就管不住它了,那时你只好丢掉它。
染染后来把卡拉卡其带到了上海,再后来她说她爸爸不喜欢小狗,再后来,卡拉卡其就变成了流浪狗。也许有一天我会再在街头遇见它,那时候大概已经认不出它。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它了它怎么样。它是又被人逮到了当作商品在卖,还是一身脏污的和另外一条一身脏污的狗在抢一根骨头,一块馒头。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去想那些和我在一起然后又分开的人或者动物或者东西。去想和他们久别重逢的情景。可想归想,却是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到南宁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了,到处都是水果,荔枝和芒果便宜得惊人,但依旧没什么人买。我有时候一整天都在公园里躺着,醒了睡,睡了醒,饿了就摘树上的果子吃,像个猴子一样。无聊的时候我就哼那首外国歌,可是我只记得一句,那句是这样的:一个孤独的没有爱的男人,每天醒来就开始心碎。
哼着哼着我也就不心碎了。
那个说自己在贵州开煤矿的朋友,名叫阿文,在得知我到了南宁之后,他说他现在也在广西,离南宁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他说他在的那个地方叫bs。
于是我便去了bs。
下了火车,看到阿文和一个陌生的男青年坐出租车来接我,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来之前,阿文说他已经发了财买了新车。
两年没见,阿文瘦了许多,剪掉了长发,穿上了西装,看上去像个小白领一样精明强干,一点也看不出他昔日颓废的文学青年的样子。
随阿文到他的住处,见到了他的爸爸,还有两个年轻的衣着简朴的女孩子,她们自我介绍时说是某某大学刚毕业的学生。阿文买了很多荔枝给我吃,我沉浸在水果的甜蜜里,内心虽然有一些疑虑和不安,但并没有多问什么。
次日一早,我听到房门外有人悄声说话。等我起床时,阿文的爸爸和那两个女孩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我和阿文还有那个一起去接我的男青年。等那个男青年去卫生间的时候,我对阿文说,不是说只是在这儿办点事儿然后就去贵州么?怎么好像要在此地久居啊。
阿文说,等会儿你就知道了。阿文神秘莫测的眼神让我感到陌生和恐慌。这些年来走南闯北,没经历过传销,多多少少也听说过。就在来bs的火车上,临座的一个男青年问我去哪里,我说bs。他说你要小心,那里搞传销的很多。我说当地政府不管么?他说当地政府要靠这些外地人搞活地方经济。bs原来只是个贫穷的小县城,近年来为什么会不断的崛起高楼大厦并且升级成了市,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
吃过早饭,阿文说带我去见一个朋友,我说行。此时此地,无论阿文是不是在搞传销,我都得听他的话。如果不是最好,只当是来游玩,如果是,那么不配合的待遇肯定是打杀。我不怕死,只是不能死得这么窝囊。
我和阿文还有那个男青年坐出租车到城郊的一个居民小区里,见了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她给我讲了一个小时行业里的佼佼者的发财史。说有很多不识字的农民,入了这行后没多久就成了百万富翁。言下之意是,你堂堂一个文学青年,入了这行还不是马上就能成千万富翁。然后又说其实传销是合法的,只是没有公开化,存在暴利的行业一开始都是受到非议的,比如彩票刚在国内兴起的时候也是倍受打击的。她说的时候我一直很配合,该点头时点头,该微笑时微笑。但是我心里却在想,你长这么漂亮,干这行太可惜了。
之后阿文又带我去KTV唱歌,随同的还有两个陌生的姑娘还有那个去接我的男青年。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放松放松,不要太紧张。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绝口不提行业的事情。次日他们又带我去见另外一个人,讲的还是一些发财史,比前一天那个讲的好一些,但是我没有一夜暴富的心理,所以这次洗脑还是不成功。但是我很配合,所以他们以为我已经认同了他们的行业。
夜里睡觉时,我趁房间里只有我和阿文两个人,就对阿文说:我身上没钱,钱都在家里,我想入伙,能不能让我回家取钱?
阿文说你再看看听听吧,不要急。之后的几天,依旧是听那些前辈讲他们的经历。我表现的越来越积极,怎么看都是一副贪财恋富嘴脸。一周后,他们大概觉得我脑袋里的那些旧观念已经被洗的差不多了,就问我能拿出多少钱。我说我现在手上没钱,如果让我回家,应该可以拿到几万块钱。阿文的爸爸说你不能回去,你回去了拿太多的钱你家人会怀疑的,不如让他们把钱打到你卡上,或者你让你家人带着钱过来,就说你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这个机会具体是什么我们可以替你想。于是他们开始问我家里的事情,并着手为我的骗钱计划制作方案。方案一,我病了,而且是重病,急需用钱。这个太老套了,直接被我否定了。方案二,我在这里买卖煤炭赚了钱,如果再投入一些钱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个也被我否定了,因为我家人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并且我已经这么久没和家人联系了,一联系就要钱,他们肯定会怀疑的。结果想了两天也没想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阿文一开始也是被爸爸骗来的,阿文从小跟着妈妈过,他这个爸爸平时都不和他联系的。他这个爸爸以前是做木材生意的,赚了些钱,然后就被朋友骗进了这个行业,于是他就骗阿文过来帮他。阿文本来是在开咖啡厅,装修后营业不到一个月,效益不好,债主催着要帐,阿文发财心切,就上了父亲的当。现在阿文只有干下去了,不赚到钱不能回头。我是阿文骗来的第一个朋友。阿文现在几乎不和我对视,他总是拿着烟,看天看地,就是不看我。
我执意回家取钱,阿文的父亲死活不同意。最后他们觉得我脑袋没洗干净,又带我去听那些发财史,并且让这个传销金字塔更高层的人给我讲道理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钱。
之后我又被带到聚会的场合去,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像小时候上课一样,讲台上坐着两个主持人。他们先是念行业的规矩,然后轮流唱歌或讲述自己关于这个行业的经历。房间里只有几台电风扇,很热很闷,不能开窗户,怕声音传出去影响到当地人。
轮到我唱歌了,我就推辞说自己不会,让阿文代我唱,阿文每次都帮我解围,但是我一点也不感激他。是他把我搞成这样的,我心里很不爽,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说什么。
我也不能说什么,说什么也没有用。我想这也算是体验生活吧,以后写到传销了一定可以写得很逼真的。
在bs待了半个月左右,事情出现了转机,有新人被骗来,平时负责看护我的那个男青年被安排到别的地方了,出入只有阿文一个人陪着我。我和阿文聊起了文学,阿文说到现在你心里还想着文学啊,看来这几天那些给你洗脑的人白费口舌了。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没错,长大了,该懂事了。我说我到死都会守着文学的。阿文不说话了。
后来,我和阿文出去吃饭,阿文塞给我二百块钱,说,你走吧。我知道你一点儿也不打算干这一行。
我说,我走了,你怎么向你爸爸交差。
阿文说,他最多骂我一顿,还能怎么样,再骗别人进来就是了。
我说,不如我们一起走吧!
阿文说,我不能走,我答应了女朋友要风风光光的回去,我要不惜一切手段赚到钱带她去冰岛旅游,你知道么,冰岛这个国家名字听起来也许可怕,其实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地方。
我没有再说什么,拿了钱就去了火车站。可是我并不知道要去那里。天下虽大,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
最后,我还是去了网吧。
和颜夏分开以后,我就很少去my论坛了,我在rs网注册了个账号,发一些梦呓般的帖子。
rs网有很多社团,尤其是我去的那段时间,简直是百团大战。有个社团的社长看了我的文字后很喜欢,让我去做编辑。我答应了,虽然没有薪酬,但是和一群有文学梦想的人在一起,心里会变得很纯净。
我用阿文给我的二百块钱在一个地方狭小机子破旧的网吧撑了半个月的时间,用这段时间写了个长篇小说,卖给了一个整天嚷嚷着要出书却总是不下笔写一个字的朋友。然后用卖小说的钱,买了一台新的电脑。换了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偶尔还是会在网上遇到我喜欢的或喜欢我的姑娘,但每次都只是点到为止,在爱意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之前,我会及时的抽身。遇到不能自已的时候,我就暂时的离开网络,四处走一走。一年的时间,我走遍了江浙两地。一年之后,我认识了阿颍。
阿颍是我所在的那个rs网社团的专栏作者之一,同时也是颜夏的朋友,在得知我曾和颜夏在一起过之后,她就整天缠着我问东问西。
阿颍说:“你就告诉我嘛,你们当时是怎么谈恋爱的?又是为什么分开的?你们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你还爱不爱她了……”
我说:“我和她都分手快两年了,你现在才知道我和她在一起过,你跟她还真够朋友的。”
阿颍说:“我们只是在网络上交流嘛,要不是从你们俩的博客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我再过二十年也不会知道的。毕竟那么多人追她,她和那么多人在一起过。她从来不跟我讲她的爱情故事的。”
我说:“你等着吧,有生之年,我会写一个长篇小说,详细记载我的爱情史,最大程度的满足你们这些爱八卦的小姑娘。”
阿颍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你是在敷衍我吧?我可不是好糊弄的,赶快从实招来,你和她都干什么了?”
我说:“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生活在九零年代。”
阿颍说:“不许用唱歌来转移话题。”
我说:“你不要再八卦了,再八卦我就泡你!让你也成为八卦新闻中的一部分。把你也写到小说里去。”
阿颍说:“你真够坏的,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哼!”
看着阿颍的头像变暗淡以后,我突然有些心痛,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在经历了和颜夏的恋爱以后,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大流氓了。可是为什么,我突然又心痛了呢?难道爱情也有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