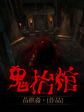玫丽是个寻求刺激的女人,而我是个甘于平凡的女人——当我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玫丽有着不同的着装品位,不同的美食偏好,也有完全不同的对于男人的钦慕理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成为要好的朋友。友情与爱情相比,前者远远没有后者那么多对于彼此的琐碎要求。
在爱情中,我们总是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努力发现对方拥有的我们所缺乏的品质。相似的地方令我们坚信我们有相似的灵魂因此得以彼此吸引,而不同的地方又使我们互生钦慕。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给少凡打电话。
“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我愉快地对他说。
“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他似乎不领我的人情。
“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和你一起庆祝。”
“我不喜欢过生日。”他冷冷地说。
我突然有些委屈,但也习惯了他偶尔为之的这种坏情绪。
第二天下班后我和玫丽约好一起去商场购物。
玫丽选了好几款不同颜色和款式的胸罩。
“为什么要买新胸罩?”在试衣间里我问玫丽。
“胸罩可以反映出一个女人内在的品味。”玫丽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女人是为了显示品味才穿胸罩的吗?”我笑着问她。
“难道是为了保暖吗?”她反驳我。
“不然为什么有的胸罩里会有厚厚的海绵?”
“胸罩里的海绵最重要的功能是弥补不足而不是保暖,羽绒的保暖效果最好,你听过里面装羽绒的胸罩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说。
“我无法忍受一个穿羽绒胸罩的女人。”玫丽说。
“这好像是一个男人说的话。”我笑着说。
“这款是不是很性感?”玫丽试穿了一件二分之一罩杯的紫色绣花胸罩,酥胸半露。
“这个只能显示出你一半的品味。”
“为什么?”
“因为是二分之一罩杯。”我嬉笑着说。
“你不需要买新胸罩吗?”玫丽付过款后问我。
我摇头。
“这是平胸女人的福音男人的噩梦。”我们路过另一个内衣专柜的时候,玫丽抓起一个有厚海绵垫的胸罩说。
“这叫机会与风险并存。”我笑着说。
我们走进电梯间,一群人涌进来,门关到一半时,一个女孩子冲进来,她手上提了好几个纸袋,另一只手在打电话。
“你到一楼电梯门口接我,我有很多东西呢!”她大声说。
我突然觉得她的声音有些熟悉。
电梯门开了,我突然看见少凡站在门口。我正想要叫他,却看见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女孩子迎上去,他们一起转身离开。我前面挡了很多人,等我走出电梯间已经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她一定是何青青,我想起她的声音和她的头发。
我失心疯似的丢下玫丽追到商场门外,外面却只有惨白的烈日和陌生的人群。
“小诺!”玫丽从后面追上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没事。”我用双手捂着脸说。
玫丽拉开我的手,“你的脸色很差,生病了吗?”
我痛苦地摇头。
“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不去。”我失控地大叫。
玫丽把我拖上一部出租车,我靠在玫丽身上奄奄一息。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给少凡打电话,却无人接听。我无法忍受心里的焦虑和难过,我现在就要看到他,问他一个究竟,我一刻也等不了。
我冲到外面跳上一部出租车,来到他的公寓,他根本就不在家。
我接着打电话,从屋里传出他的电话铃声,他压根就没带手机,我靠在门上痛哭起来。
天黑了,我已经哭得精疲力竭。我靠着门坐在地上,脑子里昏昏沉沉,我只能等少凡回来。我希望他告诉我这是一场误会,我希望他告诉我他是爱我的,我希望他告诉我他不会离开我。而在这一刻,我是多么的害怕,害怕失去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
“小诺!”隐隐约约我听见有人叫我。
我睁开眼,看见少凡在我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忍不住泪水喷涌而出,“你去了哪里?”我问他。
“和朋友一起。”他淡淡地说。
“和何青青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
他吃惊地望了我一眼,没有否认。
“你们一起过生日了吗?”我冷笑着问他。
他摇头。
“为什么你要骗我?”我流着泪质问他。
他不说话。
“你答应我不再和她见面,你为什么要骗我?”我声嘶力竭地对着他喊。
他还是不说话。
我拿东西扔他,把桌子上的书扔了一地,他坐在沙发上不发一言。
我把那张肖像画用力摔在地上,玻璃被摔成无数个碎片。我看见那张破碎的脸,突然有些陌生。
“我们分手吧!”我痛苦地说。
我本来希望他会挽留,结果他没有说话。
我哭着冲到门外,他追上来拉住我。
“我送你。”他说。
“我自己会走。”我忍住眼泪说。
他坚持送我。
已是深夜,街上车很少,他把车开得飞快。我闭着眼睛坐在副座上,只感觉到虚弱的肉体和垂死的心。我的脑子里一片混沌,我强迫自己停止思考,痛苦却汹涌而来。
车子终于停下来,但我不愿意离开,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好像在静候最后的宣判。
车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不禁流下泪来,曾经的兴奋与欢愉怎么变成了沉默与背叛?
“小诺!”他终于打破沉默。
听见他叫我的声音,我难以自持地啜泣起来。
“对不起。”他说。
“不要跟我讲‘对不起’。”我情绪激动地对着他喊。
他望着我,手足无措。
我突然上前抱住他,一边哭一边疯狂地亲吻他的脸颊、眼睛和嘴唇。我的眼泪流到他的脸上,我抱着他失声痛哭。
“少凡!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哭着哀求他。
我哀求他施舍给我一份爱,爱一个人原来是可以如此的卑微。
“不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回去睡吧!很晚了。”
我倔强地摇头,我要留在他身边,我害怕他一离开我就抓不住他。就像笼中的小鸟,离开了就再也不会眷恋回去的路。
我靠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我用同样的频率和他一同呼吸。如果可以,我情愿就此不再醒来,我迷迷糊糊地想。
天还是亮了,少凡一脸憔悴地望着我。
“对不起。”我有些内疚。
“你像一只小花猫。”少凡摩挲着我的脸说。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定是眼泪弄花了脸。
少凡把我送到门口。
“进去吧!”少凡对我说。
我有些不舍地望着他。
他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少凡!”他刚转身,我在背后喊他。
“我会找你。”他回头对我说。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在想我所爱的人是否还爱我如昔?
我站在浴室的喷头下冲刷着身体,我想用水温去温暖我僵直的身体,抚慰我疲惫不堪的灵魂。流水的声音可以暂时平息内心的喧哗,我发现这是一个安全的所在。
我裹着浴巾趴到床上。
“没事吧?”玫丽小心翼翼地问。
我无力地摇摇头。
“是因为秦少凡吗?”
“我想睡觉。”我用被子蒙着头说。
恍恍惚惚的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被困在一个小岛上,远远的我看见少凡划了一条船过来,我高兴地冲着他大喊,他却好像没有看见我,从我面前经过。我着急地喊着他的名字,他头也不回……
我喊着他的名字惊醒,泪水早已湿了枕头。
缺乏安全感的爱情,让人疲惫。
我很想打一通电话给少凡,最后还是忍住了。我希望他会挂念我,如果他挂念我,他会主动给我打一通电话。
玫丽推门进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不去。”我把头重新蒙上。
“你打算绝食自尽吗?”
“我没胃口。”
玫丽掀开被子把我拉起来。
“为了你我把郑超都推掉了,我可不是重色轻友之人。”
“你不必这么做。”
“但我已经做了。”
玫丽去拦出租车。
“就在附近吃不好吗?”我无精打采地说。
“是郑超订的情侣套餐,不吃就浪费了,他会负责结账。”
“那我更不去,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
“要不在胸前挂个牌子,上面写‘我只喜欢男人’。”玫丽坏笑着说。
我被她逗得忍不住笑出来。
“对了,你不是想看日出吗?下次我带团去南海,现在还有名额,你和秦少凡要不要去?可以给你们优惠呢!”玫丽说。
“我问问他有没有时间。”
从餐厅出来过马路的时候,正好是红灯,斑马线前停了一排车子。
“是秦少凡的车。”玫丽指着其中一部白色的车子说。
我跑过去,看见少凡和何青青坐在车里。他们也看见了我,在车里怔怔地望着我。
我站在马路中间望着他们,换成绿灯了,后面的车子被堵成一排不停地按喇叭。玫丽把我拉过了马路。
“该死的秦少凡。”玫丽愤愤地骂着。
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欲哭无泪。
玫丽扶着我的肩膀担心地说:“小诺!哭出来会好一点。”
“我没事。”我佯装坚强。
我的心在一阵阵地收紧又放开,痛得窒息。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也无法安慰自己。
少凡来了,玫丽开了门,我赌气跑回房间锁上门不见他。
“小诺!”他在门外叫我。
我趴在床上失声痛哭,我感觉自己快要晕死过去。
我不是不想见他,我只是希望拖延一点点时间,以此来弥补我丧失殆尽的尊严。
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已经黑了,我筋疲力尽地从床上爬起来。外面很安静,他大概离开了。
我开门走出去,少凡低头坐在沙发上。见我出来他站起来望着我,我用咄咄逼人的目光回望着他。
“对不起。”他首先开口。
“你走吧。”我收回目光。
“我并不想欺骗你。”
“但你已经欺骗了我。”我激动地说。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次。
“除了‘对不起’,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我问他。
他垂下头。
“为什么你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我对着他咆哮。
“我们分开吧!这样就不会再伤害你。”
“你来就是对我说这句话的吗?”我哭着问他。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沮丧地说。
“好吧!我不会为难你。”我强迫自己镇定一点。
“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你不用贬低自己。”我说。
少凡离开了,带着他的背影还有我的世界一同离开。
我回到房间里,少凡送给我的圣诞树还摆在角落里。我顺手打开圣诞树上的彩灯,却只有一半是亮的,我沮丧地把那串彩灯取下来。
灯泡是有期限的,只是我没有料到我的爱情也是有期限的。原本以为我会收获爱情里的所有美好,却不知道创造最大痛苦的便是爱情。
我把圣诞树整齐地折起来,放进一个盒子里。我望着曾经摆放圣诞树的角落,空荡荡地存在着。在那片空白里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漩涡,在吞噬我所有的爱与可能。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荒凉,如果他多停留一分钟,我怕我会再一次向他乞求。在他面前,我可以不顾尊严,而没有尊严的爱情大概也不会长久。
他悄悄走进我的生命,蚕食我灵魂的所有,然后弃我而去。如今,只剩下孤独的肉体在痛苦地呻吟。
好几天我都没有起床,玫丽像照顾坐月子的女人一样照顾我。
“过两天我要带团,你回家住吧,我不放心你一个人住。”玫丽给我端来一碗粥。
我摇头,“回家了便不能哭。”我说。
“为了那个放弃你的男人吗?”玫丽生气地说。
“哭我死去的爱情。”
“爱情还会再来的,天还没有塌下来。”玫丽说。
“我的天已经塌了。”我深呼了一口气说。
“要不跟我去旅行吧,散散心,反正你也请了假。”
我点点头。
出发那天,我随便套了一身衣服站在门口等玫丽。玫丽拖了一只很大的旅行箱出来。
“你是不是打算告诉所有的人你失恋了?”
玫丽把我拽到镜子前面,我一脸的苍白和憔悴。
玫丽掏出化妆盒,替我化了一个淡妆,我任由她摆布。
飞机上,空乘在介绍安全事项,我十分自私地希望飞机坠落摔得粉碎连同我的身体。
这是清晨的航班,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太阳缓缓地升起。飞机大概是向着东南方向飞行,把日出拖得很长很长。从窗口俯瞰,我看到最壮美的日出和云海。
我想到曾经和少凡一起看日出以及我们一起看日出的约定,不禁嚎啕大哭。
周围的人都诧异地看着我,我哭得很丑陋很不顾及形象。
空乘过来询问,我听见玫丽旁边的男人说:“她胃痛,有止痛药吗?”
整个旅行期间我都在酒店里睡觉,我没有看风景的兴致和力气。
玫丽把我像一件行李似的带回来,一肚子抱怨。
“你打算消沉到什么时候?”
“我明天开始上班。”
我没有永远不上班的理由,眼泪如果还没有流干,应当流到心里去灌溉那无边的悲伤!
半个月没来律师行,走进去时不禁心生怯意。
程亭娟正在收拾东西,桌子上的一只纸箱里装满了杂物。
“小诺!”程亭娟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我还担心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你要走吗?”
“我要结婚了,友邦的家人不希望我出来工作呢!”她幸福地说。
“恭喜你!”我对她说。
“对了,我想让你当我的伴娘。”
“什么时候?”
“两个月后。”
“你问问秦画家愿意当伴郎吗?他如果愿意我们就不再另外找人了,最好是一对情侣。”程亭娟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黯然地说:“你还是找其他人吧!”
“我希望你能做我的伴娘,我再没有合适的熟人。”
我点点头。
两个月后,程亭娟的婚礼在一座天主教堂举行。由于新郎是天主教徒,他们会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
“今天的客人里有很多青年才俊,说不定能遇到真命天子呢!”程亭娟对我说。
“哪有那么容易。”
“你今天很漂亮很打眼,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有人向我打听你的情况呢!”程亭娟一边摆弄着婚纱的裙摆一边对我说。
今天我穿了一件裸粉色的单肩荷叶边连衣裙,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脚穿一双三寸高的金色高跟鞋。我从镜子里打量着自己,两个月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容光焕发。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在教堂里我见到了少凡和何青青,这是我们分手后第一次见面。
两个月来我无数次地幻想和他重逢的场景,我以为我可以从容地面对他,现在才发现看见他我仍然会不安地心跳加速。我不敢去看他,因为我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情绪失控。
我突然想到脖子上还戴着少凡送我的项链,我慌忙取下来攥在手心里。我害怕他看见以为我还在思念着他,虽然我一直舍不得把它摘下来。
好不容易挨到婚礼流程结束,我想及早和新郎新娘告别,不过似乎有些晚了。
他们走过来,何青青向新郎新娘祝贺,原来她是新郎的表妹。接着她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她像是一个战胜的将军在向我炫耀她的战利品。
少凡有些尴尬,我突然坦然起来,我留给他们一个落落大方的微笑离开了教堂。只是这种坦然不会维持太久,当我离开教堂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两腿发软站立不稳。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踉跄着爬进去。
“小姐,你看上去很面熟。”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
“可能我坐过你的车吧!”我说。
“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你和朋友喝了酒,你哭闹着不肯上车,后来是你的男朋友把你背回去的。”司机笑呵呵地说。
我闭着眼睛想,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那时候一切还很美好,我还可以对着少凡任性发脾气。只是这一切早已过去了,想回也回不去。
“你的男朋友一定很疼你。”司机继续说。
我只能苦笑。
当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还在一个陌生人心里生长的时候,那份爱却早已荒芜。我们的痛苦在于爱情总是太短暂,记忆又太绵长。
回到家的时候,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项链弄丢了。
我突然有点失笑,爱情要完结的时候要拦也拦不住,连同这睹物思人的东西。我摸着空空的脖子,这一次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了,我似乎如释重负。
后来的一天,我和程亭娟约好在律师行附近的一个茶餐厅见面。自从上次婚礼后我还没有见过她。
我早到了几分钟,要了一杯咖啡等她。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程亭娟打来电话说突然有急事不能来了。
我一个人在啜饮那杯咖啡,一个男人走过来说:“我能坐在这里吗?”
我抬头望了望旁边的空桌,没有说话。
“你似乎不情愿我坐在这里。”他倒是很实在。
我没有说话,他不客气地坐在了我的对面。
“最近还好吗?”他像是在问一个久未谋面的熟人。
我抬头瞥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