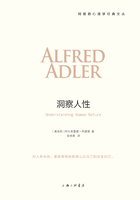但是,曹锐一心结好奉张,排斥洛吴,他把这四个条件带回保定,联络他家老七曹镆,见了三哥曹锟,却又有他的一套说法。曹锐和曹镆的意思,队伍、军械、粮台和战费,直系远非奉系之敌,这个仗打起来,直方决无胜算,既然打不过,那就不能打,而他俩把当前问题的着眼点,就放在吴佩孚下台的这一件事上,这两弟兄振振有词地说:
“现在咱们的队伍都在子玉手里,倘若要免他的职,他决不肯依,一个翻脸不认人,恐怕会对三哥不利。奉军入驻平津,正好制住吴子玉,他不遵守三哥的命令,咱们就叫奉军对付子玉去。”
曹锟一听,顿时便将脸孔一板,愤愤地说:
“你们两个这笔账是怎么算的?用奉军去对付子玉?子玉一垮,咱们不也跟着完了吗?”
然而,主和派吵吵嚷嚷,依旧呼声甚高,一天到晚絮聒得曹锟受不了,他这人素来耳朵根子软,尤且懦弱无能,和欤战欤,不得而决,于是他便断然地说:
“咱们还是开一次高级会议,要和的跟要打的,大伙儿面对面地商量。”
四月十一日,直方决定和战大计的会议,在保定督军衙门秘密进行,由曹锟担任主席。主战派以吴佩孚为首,主和派则由曹锐、曹镆领军。曹锟先让吴佩孚说话,他站起身来,扫视与会诸人一瞥,然后面容严肃,语气沉重地说:“头一件事我们得弄清楚,这么些年以来,我们唯有应敌之师,并无侵略之战。我们用兵,是实逼处此,不得而已,正当防卫不可谓之斗,吊民伐罪不能说是争,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渴望和平,我们又何尝不然?今天要讲和,条件很简单,仲帅干的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是仲帅的防区,张雨帅不是在当他的东三省巡阅使吗?双方河水不犯井水,我们请张雨帅把他的队伍撤出榆关去,再取消他那个‘北京司令部’,只要张雨帅肯这么办,那就绝对不会发生任何冲突。”
曹锐立刻反驳,他说奉军入关已为既成事实,逼他撤退,唯有造成亲家翻脸,而翻脸的结果,是“咱们一定打不过”,与其闹到不可收拾,何不此刻退让一点,多少还能保持实力。
双方的意见都说出来了,使曹大帅更加迟疑难决,戎服辉煌的将军席上,于是恼了一位吴佩孚的老把弟,北洋骁将张福来,他自动地站了起来,大声嚷嚷地说:
“仲帅您就不要心再犹移了,和跟战,其实都是仲帅您自己的事,您要当直系的领袖,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咱们就只有努力作战,拼命打仗。您要愿意凡事听着张雨亭的,那也不必讲什么和,干脆,咱们投降了他们,不就得了吗?”
几句话刺挠得曹锐、曹镆好疼,四爷沉不住气,光了火,啪地一拍桌子,破口大骂:
“张福来,你是什么玩意儿?胆敢说什么投降不投降的话!你说这个,便是造反,看我不毙了你!”
曹锐这么盛气凌人,吴佩孚当时便勃然色变,他正要发作,王承斌赶紧站起来,劝这劝那,说好说歹。曹锟也觉得老四老七的态度都太过分,端出兄长的架子,责备曹锐、曹镆几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度过,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趁此机会,表示他绝对支持吴佩孚的意见,他侃侃然地发了言: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责骂张作霖通日卖国,在这种时候我们该战不战,反而跟他们讲和,只怕全国民意,都要把他们对奉张的痛恨,转嫁到我们头上来了,对于仲帅的事业和声誉,必有重大的影响!”
接下来,便是全体高级军官,一致起立,齐声喊道:
“奉张一日不驱,国家一日不安,请仲帅立刻下令,我们决心效一死战!”
吴佩孚赶紧相机进言:
“将士人人愿战,仲帅就不必再迟疑了。”
直到这时,曹锟方始义形于色,慷慨动容,他伸手一拍大腿,毅然决然地说:
“好,打就打!子玉,还是你当前敌总司令!”
主和派那一边,曹锐、曹镆的和议为之粉碎,于是曹锐恼羞成怒,气得胀紫了一张脸说:
“明知道打不过人家,你们偏要胡来,是不是要大伙儿全毁了,方才遂你们的心!”
曹锟听他话说得重,深怕吴佩孚不受用,当时又抹下脸来叱责:
“老四,你少在这儿胡说!”
“我胡说?”曹四爷向来焦躁,此刻更是怒火冲天,双脚直跳。这一怒之下,他便干脆掼了纱帽:“好好好,你们要打,尽管请吧。对不起,四爷这次恕不奉陪了,我这个直隶省长,三哥,请你另选高明!”
说完,也不等曹锟答话,拉了曹镆一把,两兄弟掉头便走。
曹锟的脸上又红又白,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四爷的脾气,吴佩孚素来晓得,为了不使曹锟过于窘迫,同时遏抑他部下的忿懑不平,他故意转移目标,开始透露他筹思已久的驱奉之役大计,他即席说明:
“奉张必欲和我们付之一战,除开他们自以为力量大过我们,此外还由于梁士诒、叶恭绰这般政客的挑唆,奉方的部署,我已经了若指掌,他们最近和广东、浙江,订立了‘三角同盟’,由广东出兵攻打我们的江西和福建,牵制我们在这两省的队伍,再让浙江的卢永祥出兵,联络上安徽马联甲的旧部,有这支队伍足可扰乱我们的后方。再加上河南的赵倜、赵杰,我们能胜,还可以作为后援,我们一败,他俩无所依归,势必投向奉方,与我们为敌。”
曹锟听吴佩孚的分析,奉方声势,果然浩大,部署安排既灵活而又严密,他嘴上不言语,却是忧急之色,业已不期然地流露出来,吴佩孚见了,微微一笑,继续往下说道:
“奉方军械犀利,粮饷充足,军费方面,他们有多年的积蓄,倒皖时得的大笔横财,还有交通系梁士诒这一帮人作后盾,必要的时候,尤且可以取得日本人的援助,因为他们有钱,所以利于持久。我们呢,梁士诒扣了我们那么久的饷,士兵粮秣,都成问题,作战的战费,至今还不知如何筹措!两相对比,即使我们不动手打这个仗,队伍无饷无粮,一定会溃会散,所以说,今天我们是非打不可,而且非得赶紧地打,快快地打,能够一战成功,才是我们死里逃生的机会。”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曹锟望望吴佩孚说:
“子玉,你还是先说咱们怎么个打法吧?”
“奉张的‘三角同盟’,老实不客气地说,我已经略施小计,将它破了。”
“破了?”在座各人,异口同声地惊问。
“破‘三角同盟’,倒很简单,”吴佩孚从容自在,若无其事地说:“广东的队伍,都在陈炯明的手里,我已经跟他取得了联络,无论如何,他决不会出兵北上,攻打闽赣。他不动,我们在福建、江西的队伍就可以监视住浙江的卢永祥。釜底抽薪的结果,‘三角同盟’到头来还是奉张一个人的独角戏。”
曹锟捻髯微笑,十分得意,不过他又想起一个心腹之患来,于是他问:
“赵倜跟赵杰那两兄弟呢?他们万一来个乘虚北上,那要比卢永祥的浙军更麻烦啊。”
“这两兄弟是个问题,”吴佩孚点点头说:“我的应付之计,可得要花点儿代价,焕章(冯玉祥的号)在陕西的队伍,一共有两师一个旅,我想都拉出来,充作后军,一方面支援前方,一方面看住赵倜、赵杰。”焕章,他目视冯玉祥,直截了当地问他,“让你暂时放弃陕西,到河南来换一个位,你看如何?”
当时,冯玉祥对吴佩孚,不但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且,他还有条小辫子,抓在吴佩孚的手里,一声不对,吴佩孚立刻可以跟他翻脸算账。原来,直皖之役过后,民国十年五月,吴佩孚保举他手下的一员大将,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冯玉祥便在阎相文的麾下,当年八月,冯玉祥便迭施阴谋,逼迫阎相文自戕身死。吴佩孚佯做不知,卖了冯玉祥天大一个交情,从此冯玉祥对吴佩孚感激、畏惧,兼而有之。遇事巴结犹恐不及,这次军事会议,吴佩孚命他率兵出陕,却添了“换位”的一句话,使冯玉祥心知来日战胜他大有河南督军之望,怎不叫他连声喏喏,一口答应。——这便是直奉之战关键最重大的一着棋子。
大计已决,直系将领人人振奋,个个表示乐观,剩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宣战”,如何调兵遣将?当年内战之起,以发布通电揭露对方罪状为第一要务。直奉之役,照说这则重要通电应该由曹三爷领衔,却是曹三碍在和奉张是亲家,还有点儿不好意思露面。吴佩孚见他为难,于是慨然说道:
“仲帅如果不嫌我僭越,那就由我领衔。”
曹锟听了,如逢大赦,一迭声地说:“那好极了!那好极了!”
由吴佩孚率领“全体将领军士”。发表了一道有凭有据,指证凿凿的通电,声讨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列举事实,约略如下:
一、阻挠民国十年吴佩孚等筹备的国民大会,破坏全国统一,同时“勾结西南”,四出构兵。
二、举洪宪祸首梁士诒为国务总理,保复辟罪魁张勋为长江巡阅使。这是他“倒行逆施,危害国体”。
三、唆使耿玉田运军械给俄国人,诱致蒙匪。又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了青岛和胶州湾。——“勾通外人,贻祸祖国。”
四、招匪为兵,出扰山东,不理友邦劝请裁兵之劝。——“丧心病狂,负罪友邦”。
五、陈师入关,挟制中央。——“危及元首,破坏法纪。”
六、奉军入京,白昼劫掠。——“政以盗成。纵匪殃民。”
七、侵入直隶,肆意宰割,使直军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得陇望蜀,黩武逞兵”。
八、劫夺军火,剽窃金钱,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叶恭绰当交通部长,张作霖受贿三百万元,梁士诒入阁,又“报效”了他四百万,张弧发行“九六公债”,更所入无算。——“劫掠械饷,形同盗匪”。
九、“帝制”“安福”余党,无不收纳,使其盘踞要津、或为护符。——“招亡纳叛,作逋逃薮”。
十、赵尔巽、张锡銮、段有恒(段芝贵之父,张作霖当胡匪接受招安时的保证人),是张作霖的干爸爸,他曾先后背叛,孟恩远、冯德麟、段芝贵是他的八拜金兰之交,他百计驱逐,孙烈臣、汤玉麟跟他起于贫贱,他加以猜疑。暗使耿玉田诱致蒙匪,然后将他毙之于狱,以图灭口。——“残杀同类,凶逾朱温”。
由于直皖之战,曹镆在杨村吃过日本人的亏,使那一线反胜为败,险乎被徐树铮攻进了天津卫。这一回,吴佩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在用兵之先,特地向北京外交团发表声明,备述奉张的罪状,说明用兵的原因,他保证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并且强调:“战事一告结束,即行恢复交通,整理善后,用达亲爱诸友邦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之诚恳”,但是,他要求各友邦在战事进行期中,根据条约,按照公法,“毋得有资助匪军行为”,这便是措词相当严峻的警告了,最后,他更指着日本人的鼻子说:“其有外人在东三省军事上服务者,亦希先期声明,即行退出,不得参与战斗!”
很周到地,他旧事重提,再致电以前担任调解人的赵尔巽、张锡銮等六位先生,声明只要奉军退出关外,取消北京司令部,吴佩孚还是愿意讲和。此外,又打个电报给浙江督军卢永祥,再次明辨直奉之间的是非,最后一电则打给奉军将士。请他们“详审利害,明辨顺逆”,自由撤出关外,而后“我直奉袍泽,仍当恢复旧好,势若唇齿,情同手足。从此奠定邦家,俾能使张作霖为在野之伟人!”
自民国七年以至民国十五年,吴佩孚的全盛时期,他所发表的通电函牍,报章竞载,传诵一时,论词章固属情文并茂,掷地有声,日内容更是指证凿凿,义正词严,他通电讨伐“对方”,一定列举罪状,极少破口谩骂,滥施人身攻击。譬如他声讨张作霖,第十款责他“狠若吕布,凶逾朱温”,其中列举张作霖所背叛和驱逐的那些义父、结义兄弟与患难朋友,确实都曾吃过张作霖的苦头。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一手提拔张作霖,使他从胡匪头目一跃而为东三军旧军的领袖。张锡銮是袁世凯的老把兄,他在东边兵备道任上使新民知府满人增韫招安张作霖、冯德麟等部,张、冯之归顺俱由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慨然担任保人,这三位长者对张作霖都有大恩,但是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上终因张作霖锋芒太露,无法驾驭而请辞,张锡銮继任奉天都督,更受够了张作霖的气,民国四年八月他因移防问题,跟张作霖闹翻,被迫下台,改任湖北督军又受王占元之阻不克到任,当时他曾寄了一首感慨万千的诗寄段上将军芝贵,字里行间,不难寻出他在奉天十年吞下的气恼和苦盏,诗云:
武昌开府驰名久。百战功高上将才,
愧我筹边无善策,十年悬耻待君来!
段芝贵是张作霖的义弟,袁世凯的心腹爱将,素有“乾殿下”之称,他当时在作湖北督军,老袁为了敷衍张作霖,下的命令是“奉天、湖北两督军”对调,他以为段芝贵的父亲于张作霖有救命成全之恩,义兄弟俩关系不同,因此才派段芝贵出关与张作霖合作。张锡銮以父执辈地位寄这首诗给小段,“十年悬耻”大有叫小段来为他报仇雪恨的意味。讵料小段一到奉天便对他的义兄张作霖巴结奉承,无微不至,偏偏张作霖还不买这两代交情的账,时时予他难堪,最后则检举小段亏空公帑数百万,把小段给撵出了奉天。冯德麟跟张作霖同时出道,一字并肩,奉军编为两师,张是二十七师师长,冯是二十八师师长,张作霖继段芝贵为“盛京将军”,命冯德麟帮办军务,冯大为不服,处处杯葛,以张作霖之道还治其身,使张作霖尴尬万分,于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之役,冯德麟竟“莫名其妙”地赶去北京参加,一着错全盘输,终于复辟兵败成为阶下之囚,从此默默无闻,不得翻身。——孟恩远曾被张作霖逐出吉林,汤玉鳞、孙烈臣是他两员心腹大将,后来也同样的变脸、闹翻,以致拆伙。
吴佩孚通电声讨张作霖,十大罪状,一一列举事实。张作霖对吴佩孚下战书,可就毛焦火躁,肆意谩骂,而把孚威上将军,比做了李自成、张献忠、乃至于安禄山、史思明。他骂吴佩孚的妙句如下:
乃吴佩孚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指民国十年四月十四日河南彰德兵变,前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被开缺后潜赴安阳,唆使驻军团长孙会友,突于四月十四日占据彰德,十六日并窜抵汲县,由河南省军和吴佩孚派队前往剿办,而在四月十八日将乱事敉平。)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指援鄂之役,外间风传吴佩孚决金口堤防以淹湘军)。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指河南卢氏县之废金矿,因需资本一千万元,吴曾拟与美国企业家合作开采。计划未定,而后来发现含金量仅为十万分之一略强,并无开采价值,议遂寝。)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做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为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电战告一段落,战幕即将揭开,京津百姓,宛如大难临头,北京公使团,更一连三次,照会外交部,请警告奉军,不得步步进逼,占领辛丑条约订定的各国驻兵地点,“其破坏条约,如因乱事致外侨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由“中国政府负其责任”!
老百姓人心惶惑,闾阎骚动,外国人再三警告,措词严厉,夹在直奉两大派系之间的大总统徐世昌,纵使“号令不出于都门”,也唯有硬起头皮,“哀哀上告”,电请“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
可是,东海老人徐世昌所得到的答复,是第二天晚上直奉双方开了火。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