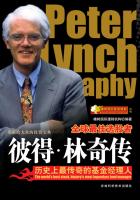战前双方布阵,则奉军方面,兵多械足,先声夺人,直奉一次大战于四月二十七日爆发,奉军自三月中旬,即已开始调动部队,积极准备。早先在关内的奉军,计有一师三个混成旅,三月中旬集中于预定作总司令部的天津之东军粮城,接着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等自四月初起,迄四月二十日止,分为八批,源源出关,人数多达十二万五千,南起马厂,北抵长辛店,连营百里,枪炮如林。重兵器配备,带得有大炮一百五十门,机关枪两百挺,打出来的旗子,系红黄蓝三色,表示这是汉满蒙三族的联合部队,士兵徽章,则一概用白的。三路大军攻击目标指向直系的根据地——保定府。
直军那边,吴佩孚调兵遣将,煞费周章,颇有捉襟见肘之苦。他以保定为总司令部,在下头一道命令之前,他还得挺为难的。赔着笑脸,去跟曹三爷和王孝伯(承斌)探个口气——
“仲帅,马厂方面的第二十六师……”
曹锟见他迟迟不往下说,立即会意,赶忙便接口说:
“我不是把咱们家老七给撤了差吗?如今换了张国镕当师长,子玉,我这么做就是恐怕老七逞意气,不听你的调度,张国镕他一定服从你的指挥。还有,老四(曹锐)的直隶省长,我也不让他干,免得碍手碍脚,我派警察厅长杨以德暂代。”
衷心感动,便也坦然地说: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仲帅这样安排。”
王承斌听说曹、吴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他便义形于色,自动找上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
“诚然,我曾经奉了保府之命,接连三次,到奉天去洽商和议,然而那是我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本意。如今大战将启,你是总司令,我是你部下,即令你让我赴汤蹈火,我也是万死不辞!”
“好极了,孝伯,”吴佩孚大喜过望,当下便说,“固安那边的中路一线,十分要紧,这千斤的重担,我只有托付给你了。”
在直隶省境驻防的直军,总计有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国镕接长的第二十六师,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和第十混成旅,此外便只有第二、第三,两个补充团。曹、王的态度一表白,吴佩孚的第一支主力,也就从此运用自如,如手使臂。
直隶省外的直军,散置湖南、陕西、湖北、河南四省,从四月十五日起,吴佩孚连续下令,渐次集中。在洛阳他自己的第三师先开保定。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岳州。葛豪、董政国、彭寿莘的第十二、十三、十四混成旅分防蒲圻岳州一线,这两支部队尽速开拔,直抵前线。陕军有冯玉祥的第十一师,阎治堂的第二十师,胡景翼的暂编第一师一部,吴心田第七师和刘镇华、刘镇嵩军各一部,还有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吴佩孚叫他们全体开出潼关来,进驻郑洛一带,作为援军后队,同时负责监视河南二赵,赵倜与赵杰。约略的算了算,全军约有十万人,计为六师五旅,又五个混成旅,却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陕军,得巩固后防,没法调上前线作战,因此之故,前线奉军就要比直军多出了一倍——重兵器咧,火力不及奉军猛,制式远比奉军差,数量既少,弹药补充更是难上加难,吴佩孚罄其所有,拼拼凑凑,只得大炮一百门,机关枪一百挺。
前线斥堠和侦探,派出去的不少,奉军布阵,吴佩孚可以了若指掌。他刚按照奉军的阵式和部署,定下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抵达军粮城总司令部,他和参谋长杨宇霆一看地图,立刻发现部队布署错误,头一桩战线拉得太长,三路纵队进攻,反而连成了一条长龙,指挥既不灵活,到处都可能被直军突破。第二桩,总司令部落得太后,奉军前线从马厂拉到长辛店,总司令部则设在军粮城,这便形成了一把扇子,越到后面,兵力越薄,发号施令不便,同时更不安全。
于是张作霖便下紧急命令,全盘更改作战计划,军粮城改作后路粮台,总司令部挺进到两百里外的落垡,由总司令张作霖、副总司令孙烈臣相偕坐镇。大军分为三路,每路三个梯队,东路沿京奉、津浦两铁路前进,第一梯队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二梯队暂编第三旅长张大帅的大少爷张学良,三梯队第七旅旅长李景林。
又以京汉铁道线为西路,一梯队热河都统奉军第一师师长张景惠,二梯队十六师师长邹芬,三梯队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中路是总司令部,拥兵五个补充旅,五千人,以及九个混成旅,由张作霖、孙烈臣亲自指挥。
奉军变更计划,人马大事调动,京汉、津浦两条铁路线上车辚辚,马萧萧,吴佩孚派出去的侦探斥堠,从早到晚,奔走不停。一批一批地回来利用电话报告敌情,总司令部的人员,由于情况急变,措手不及,大都紧张慌乱,唯有吴佩孚雍容镇静,他手持电话筒,注目大地图,得一次情报,他便下一道命令,兵来将挡,水到土掩,等到奉军改变部署已毕,吴佩孚这边照样的大计决矣,各路迎敌人马,一概部署定妥。
吴佩孚知己知彼,从容应付,他改以郑州、洛阳为后路粮台,仍以保定为总司令部,东路奉军张作相、吴俊升、李景林,他派王承斌、张国镕、张克瑶前往迎敌,西路奉军张景惠、邹芬、郑殿升,吴佩孚则令张福来、葛豪、董政国、彭寿莘拒之。中路有奉军正副总司令张作霖、孙烈臣,尤拥精锐之师许兰州、鲍德山等部,吴佩孚便拟亲往搦战,他带的是他那英勇剽悍的“怯薛军”,第三师之大部。
直奉第一次大战究竟是谁先开火?实实在在,奉军首攻,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马厂,奉军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动了手,他们向直军第二十六师进行攻击,二十六师沉着应战,枪炮互击,直军迫使奉军退出马厂,唐官屯,然后很快地将沧州与唐官屯之间,17英里的铁路一齐拆毁,阻碍交通,便能加强防务。
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双方前线哨兵不断地发生小冲突,起因都是奉军挑衅,直军奋起抵抗,然后奉军便告后退,双方互有死伤,却是与大局并无影响。
将战未战时际,谣诼特别的多,连日前方有些小接触,外间便说:奉军已经占领马厂,连德州兵工厂都给奉军夺了,因此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镆被吴佩孚免了职。还有什么山东督军田中玉来帮直军的忙,派鲁军第一旅助守兵工厂,等等流言,不一而足。吴佩孚便道这样不好,谣诼以讹传讹,会影响士气,于是,他下令张国镕:
“你好好儿地给我打一仗看。”
张国镕是直皖之战时皖军的降将,他得令以后,精神抖擞,立功心切,拉起队伍便扑向正面的敌军,当面之敌有奉军第七旅的两个团,实力强劲,阵地顽固。二十六师的弟兄前仆后继,几度冲锋,傍晚时分眼看着奉军即将不支撤退,让出第一线阵地来了。突然之间炮声连响,万马奔腾,远远望去只见烟尘滚滚,直冲云霄。张国镕一看便知道是奉军的骑兵炮兵大队来援。他迅即下令弟兄们往后退,赶紧撤出平坦空旷的地方,然后各找掩护加以还击。这一次奉军骑、炮、步合力大战张国镕,战场便在姚马渡,双方猛烈轰击互不退让,整整打了三个多钟头,直到日落西山,夜幕四合时方始各自收兵。
张国镕收兵回营好不懊恼,因为他觉得他这一仗实在没有打好,因此第二天一早,他便集合队伍,展开拂晓攻击,他要再接再厉,杀奉军一个措手不及。待第一波队伍高声喊杀,直奔敌阵,他便挥舞指挥刀,亲自率领一个团,身先士卒,大步向前。这一团人见师长领在头里跑。于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后面的大队不顾奉军炮火一捅而上,奉军料想不到直军会使用大部队打冲锋,排山倒海般直压下来。第一线奉军不战自乱,回头便跑,于是冲动了第二线以至第三线,奉军第一、第七两旅节节后退。张国镕大汗淋漓,足足追了十五六华里,奉军死伤累累,尤其被直军夺下了大炮一门,快枪三五百杆,让直军漂漂亮亮地赢了一仗。
黄昏,直军冲过陈官屯,直逼静海城,奉军因为再一退却,便要退到跟天津同在平行线上的独流或良王庄,于是据城死守,寸土必争。张国镕久攻不下,发了焦躁,他调集后队,继续增援,把一座静海城三面围定,只留下北门让奉军开城出走。静海城的攻防战从薄暮持续到深夜。枪炮齐鸣,曳光闪舞,深夜里直军枪炮密集扫射,使他们所在的位置因而暴露了,这时候独流、良王庄方面的奉军援兵适时赶到,又是推进迅速,凌厉直前的骑兵,千骑当先,几阵冲突,把张国镕的半包围圈,冲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奉军趁胜急追,张国镕在千军万马之中紧急下令,往西南走大城集合整顿。
张国镕想退守大城,重新整理部队,然后鼓勇再战,拿下静海,却是奉军转败为胜,怎肯给他喘息立足的机会?他们骑兵在前,步队在后,大声鼓噪,衔尾急追。这一路的奉军第一梯队长张作相,字辅忱,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即已投身绿林,成为胡匪。他跟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同时接受招安,当了满清的军官,可说是一身是胆,曾经百战,素为张作霖手下的一员骁将。当夜得悉张国镕夜走大城的消息,便认为这是消灭直军西路主力二十六师的大好良机,他急调第一梯队全部,夤夜开赴大城,同时通知第二、三梯队火速赶来助战,他决心趁此机会解决掉奉军东路之敌。
张作相还没有抵达大城之前,奉军骑步两军围攻甚急,有一位穆团长右臂中弹,受伤仆地,奉军的攻势因而稍受顿挫,而直军二十六师的援兵闻讯也在源源开来,情势又变得对于奉军不利。恰在这时,张作相虎将军自天空降,他带来了卫队旅的四个营,以及第四混成旅的整一团人,在他的后面尤有奉军第三混成旅,不旋踵即将开到,张作相有心以大城为张国镕与吴佩孚东路主力第二十六师的葬身之地。
直军西路告急,吴佩孚在他的指挥总部得着消息,他摇头叹气,说是张国镕明明晓得我寡敌众,就不该贪功恋战,反而遭了敌方的暗算。当时总部人员请示他应该如何解围,吴佩孚说:
“我们东、西、中三路,当面之敌至少一倍于我,哪儿还有部队可以抽调得出来?牵一发,动一身,一着错,满盘输,这事实在很伤脑筋,”然后他略一沉吟,便又自言目语地说道,“罢罢罢,情非得已,我只好再用一次奇兵之计。”
于是,他吩咐左右,喊一名工兵连长来,附耳授以锦囊妙计,叫他如此这般。
张国镕浴血苦战,拼斗不休,从四月二十七日发动拂晓攻击,直到围攻静海,卒告败退,回师大城力抗奉军。二十八号整整一日杀声震天,目不交睫,再打到二十九日午刻,张作相率领大队,并力来攻,他已经五六十个小时不食不眠,实已精疲力竭。张作相后面的奉军第三混成旅又到,轮番冲锋攻击,终使张国镕难于拒敌,迫不得已,他便想向中路直军靠拢,以求支援,于是下令全军西撤任丘,当张作相挥刀跃马,冲入大城,奉军清点战场,直军遗尸共达四百余人。
张国镕往任丘撤退,张作相正待派遣人马,急起直追的同时,他忽然接到进驻静海的李景林电话,李景林告诉他说:方才突见一队直军,正在大城西北一块旷地上挖战壕,看样子仿佛是准备驻守,李景林决意带一支兵去察看究竟,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大城很近,所以他特地打电话来知会一声。
这个电话使张作相迟疑彷徨,举棋不定,如果大城西北发现直军,那么,东路奉军多半已在大城集中,他带这批人马去追张国镕,万一那个腹心地带有事,那他岂不是中了吴佩孚的调虎离山之计?用张国镕作牺牲,引走东路主力,然后批亢捣虚,顺利夺回东路奉军方始拿下的重要据点吗?——就犹移了这么一下,使张国镕险处逢生,顺顺当当地逃到任丘去,二十六师终获保全,直军西路总算不曾一败涂地,全军尽没,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李景林率队往攻挖战壕的直军,少数直军一见奉军大队来临,丢下铁锹铁铲便跑。李景林正待下令追击,紧跟上来的一营骑兵,风驰电掣般来了,李景林高声嚷喊:
“你们骑兵马跑得快,赶紧追上去,可别都杀光了,得给我抓一名活口过来!我还要问他的话咧!”
奉军骑兵一看,直军正在前面不远之处,抱头鼠窜而逃,他们欺直军人少,以为这是唾手可得的功劳。于是由营长发号施令,马队一字儿摊开,一声向前冲呀,便是沙尘滚滚,声势有若卷地狂飙,步兵站在原地艳羡地瞧骑兵八面威风。杀敌致果,讵料马队方到直军方才所挖掘的战壕,蓦地轰隆连响,红光迸射,就地炸开了无数地雷,转眼间天崩地裂,鬼哭神嚎,一营骑兵如风卷落叶,纷纷栽倒。吴佩孚的地雷阵大发虎威,来势凶猛,直炸得一营骑兵人仰马翻,半空中胳臂大腿直飞,奉军三百余骑不曾走了一个,尽数丧生在地雷阵上。一地的尸骸狼藉,血流成渠,看得李景林和大队奉军心摧胆裂,十分凄惨,再望那些直军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在落垡专车上的奉军总司令张作霖,获报一营骑兵误陷地雷阵,全军覆没,损失殆尽,他气得连连跺脚,高声咒骂,骂吴佩孚惯使阴谋诡计,专埋地雷伤人,又骂李景林久经阵仗,见多识广,居然也会上了吴佩孚的大当。骂过人后他命参谋下一道紧急命令,叫奉军全军将士务必牢牢记住:
“往后追击直军,必须半守半追,以免又误中了吴佩孚的地雷。”
吴佩孚用地雷阵作诱兵之计,暂时止住了李景林大军支援张作相,合攻任丘城,使张国镕退入任丘得以喘一口气,协同城内直军紧急加强城防,准备应付明日的大战。这任丘县出城往西,过高阳县便是直军的总部所在保定府,吴佩孚晓得张作霖必将把握时机,并力猛攻,所以他连夜调动人马,把后面的王承斌赶紧拉到任丘来。
王承斌率领他的二十三师和四混成旅衔枚而进,连夜攒赶,当他在二十九日正午渡过永定河时,奉军第二梯队匆匆赶来邀击,二十三师也是久战之师,遭遇任何情况都可以不慌不忙,沉着应战,王承斌留下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四个混成旅,与奉军中路第二梯队隔河大战,这一仗打到下午六点钟,奉军死伤过多,开始退却,直军涉水直追,渡河后便将奉军追到固安西北三十里,张作霖急派骑兵两团,步兵一营来援,于是合兵一处,奋力反攻,又把直军打了回去,鲍德山占领固安,往东南追向永清。驻琉璃河的直军便趁机出动,紧蹑鲍德山之后,来解直军四个混成旅之危,于是四混成旅立定脚跟,整军回身再战,鲍德山腹背受敌,行将大溃,张作霖立遣中路骁将许兰洲的一个师驰往解救,这便是中路的第三梯队。许兰洲带了四门大炮,射程可达八千米远,大炮猛轰,直军有点顶不住了,他们只能匿身战壕,用步枪还击。许兰洲利用炮火掩护亲率大队打冲锋,居然被直军一枪击中,许师长受了轻伤,他一退下,第三梯队便从此不肯向前,张作霖一怒,派吉林第二十八师两营骑兵,猛踹直军阵地,迫使直军后撤,奉军渡过永定河,疾走数里,黑夜中又触发了直军的地雷,炸死了一百多人,垂头丧气退回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