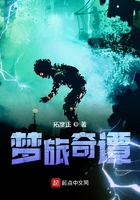场里和政治处分配给曾源的任务一个铸着一个,先是出《跃进报》,采、编全由他一人承担,刻蜡版也是临时拉差;没过几天又有新任务下达,说是上级指示,要编一本“场史”,命曾源先搞个“提纲”出来,提交场党委讨论;“场史”刚刚有点眉目,更大的任务随之而来:场里抽调一名分场场长,一名农业技术员加上曾源共三人,根据上级有关指示,起草一份以加强定额管理为内容的“三仓一奖”实施方案,要求于春播开始前完成。
三项任务,除了油印小报断断续续出过几期外,其他两项都成了“半拉子工程”,因为春节将临,上下都没那份心思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曾源分别向父母和妻子寄了款,自己一个人在农场过春节。同是春节,时空的换位给他带来情感上的强烈反差:上一个春节是在北京过的,虽是异地他乡,然而由于招待所所长夫妇亲人般的关怀,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与仅有的两位住所客人曾源和程继章共度良宵,战友情深,游子欣慰,乐而忘忧;而今又是春节,政治气候变化,人文环境令人窒息,食物短缺到难以果腹,除夕之夜连一顿饺子也没吃上,每人两碗羊杂碎面片,算是见了一点荤;然而在另一个特殊角落有些人却正享受着“手抓羊肉”,除了场里的头头,陪餐者仅为晚宴的操办者和李玉发的几名亲信,连副场长身份的吴远成将军也没有资格被邀人席,其他人更是沾不上边,只能领略随风飘来的阵阵肉香。
春节和元宵节都在寒冷、苍白、郁郁寡欢中度过。
元宵节过后不久,相继有千余名“河南支边青年”和“上海移民”来到农场。他们中不少人是抱着“支援边疆建设”的雄心壮志和“移工就食”的现实需求而来,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持久的饥饿和无尽的风沙……早春天气,春寒料峭,为了实现粮食产量“翻番”,大增产,大丰收,自给有余的目标,全场范围内以积肥、运肥、平田整地、农机检修为中心的备耕工作,比往年提前一周就开始了。然而人们既无激情又无热情,干起活来懒洋洋的,兴味索然。只有那没完没了的风沙不识趣地为拓荒敲击着单调的“战鼓”,更加令人心烦!
好不容易熬过了“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苦寒日子,天气渐暖,白昼渐长,只是饥饿更觉得难耐,肚子里没有油水垫底,一天只有那么一点定量,饿得人坐立不安。日久天长,营养不良,人们的身体渐渐乏困无力,干什么工作也提不起劲,躺着的时间要比干活的时间多。
这天午后曾源躺在床上却无睡意,两只眼盯着天花板,思念留在省城孤孤单单的妻子许如蕙。她的预产期只剩下个把月了,在何处分娩?是回娘家还是去婆家?是留省城还是到农场来?想来想去各有利弊,回娘家路途遥远,去婆家条件太差,省城和农场都没自己的“窝”,许多具体问题无法解决。这事最佳方案应是与妻子当面商定。可是看来很简单的事却变得可望而不可即:自己去省城吧,现在个人的处境不便张口请假,再说什么时候去合适,即便能去,哪里去找坐月子的房子?让她到农场来,就以现在自己住的这间房子做产房,领导上能否恩准?老张那边估计不难通融。这里条件虽然差些,总比没有着落强吧。令他焦急不安的是妻子一个多月没有来信,放寒假后,她是滞留省城还是回上海去了?因为女儿一直在外婆家,祖孙三代血浓于水,岂有妈妈不想女儿……不知是出自某种“磁场感应”还是纯属偶然。这天同室伙伴老张从场邮政代办处给曾源捎来一封上海来信,曾源一看那熟悉的笔迹,长喘了一口气:她终于来信了!
亲爱的源:
一个多月没有给你写信了,算起来跨了两个年头,你一定很着急,也很生气吧?这事的责任当然在我,可也实在是身不由己呀!
我原来打算放了寒假,就到农场来看你,如果条件允许,就在农场分娩,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这次生孩子你能在我身边。
真没想到眼看就要放寒假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校领导宣布:接上级指示,放寒假后,全体教师不准离校,一律去区政府集中参加全区教师集训,我想集训就集训,反正只有一个星期时间。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从食堂打饭出来,没注意被食堂门前的冰溜子滑了一跤,运气还算不错,饭盒子没打开,打来的饭一点没撒,由于穿的是棉衣棉裤,身上没碰疼,所以我也就没在意。下午就同其他老师一道带上行李去区政府报到。到了区里,按分配好的房子住进集体宿舍,又在食堂买了饭票’只觉得肚子一阵一阵地疼,但不太厉害,我还是没当一回事。谁知道半夜一两点,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把熟睡的同伴惊醒了,纷纷披上衣服下床过来关照我,快到凌晨3时,孩子出生了,早产一个多月,是一个小男孩,长得太像你了,只可惜你没见着!
天气那么冷,深更半夜又毫无准备,多亏了训练班的领导和参加集训的老师们:同室的、外室的、认得的、不认得的,大家一齐出动,全力以赴,不大工夫,纷纷送来红糖、糯米、鸡蛋、奶糕等食品,还有奶瓶、布料、小被子等婴儿用品,特别是那些稀罕的食品,大都是上海、北京等条件好的地方的亲人寄给她(他)们的,或者是从孩子的嘴里省出来的,太让我感动了同志们七手八脚用半截床板绑了一副临时担架,互相轮换着把我从三楼上抬下来,连夜送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母子平安无事。困难时候见真情,我被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感动得哭了……孩子不够月份,身体很弱,很快被转送到儿科,送进了保温箱。第二天下午我便挣扎着去我们学校那边的街道办事处去报户口,领了布票和糖票。产后第二天,往返十多里路,虽然是坐公交车,但也确实冒了不小的风险,所幸平安无事。
孩子送进保温箱,进行特殊护理,我想过几天会好起来的,谁会想到过了三天,这只保温箱因有“紧急”任务,搬到“技术革新成果展览会”上去了。孩子的病情急转直下,只活了三天呀!
亲爱的源:我真对不起你,这孩子真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生……
孩子就这么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又匆匆离去。我的身体十分虚弱,学校领导对我很照顾,寒假加上产假给了我三个月的休息时间。来不及同你商量,便乘火车回到上海家中,这里主、副食供应比西北好得多,又有爸爸妈妈精心照料,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
来信直接寄到上海家中。
如葱
196年1月25曰
曾源看完信,心头好像是掀翻五味瓶,酸、甜、苦、辣、涩并来,不知是何滋味。在他的情感世界里半是辛酸,半是忧伤,内疚多于遗憾,哀怜胜似怨尤。作为产妇的丈夫他对妻子临危遇救区训练班的领导和同伴们的殷切关怀和友情付出深为感动,对妻子转危为安和她做出的回沪休养的决定,感到庆幸和赞赏。他一方面觉得愧对妻子,愧对夭折的娇儿,自惭未尽到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感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还是好人多!
妻子的来信,曾源反复看了几遍,当晚在油灯下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尽述欣慰、愧疚和思念之情。
数日后,曾源又接父亲来信,读来令人心酸。
曾源吾儿知悉:
今年过来,家里的曰子多一半靠菜充饥,前半年挖野菜吃,后半年靠咱家园子里种下的白菜、萝卜,从元月一直吃到腊月。街市上粮食一点没卖的,有钱无处花,何况咱们还没钱。公家门市部给居民的供应菜说是每人每天半斤,大多不兑现。我常想走一趟岷县山里找寻些蕨菜,填补一下一家大小的肚子,这几天身子骨乏困,一直没能动身。咱们家月月总要缺六七天粮,到过年跟前至少要断粮十天。现在只有指望你了:你在各位同志跟前求助一下,有他们节余的粮票,哪怕是二斤三斤,凑在一起,迅速寄来’以解燃眉之急。你弟清娃在学校里一月总得十二三元花,还是吃不饱,月月要缺四五天的饭票,困难得很。看来唯有让他休学,暫时干上一点什么工作维持生法7可他硬要继续念书,加上学校里又不让学生离校,真不知如何是好。
想到一家落得如此境地,曾源实在于心不忍,费尽口舌向他人借得5斤粮票,挤出他当月工资的近一半寄往家中,同时修书一封告知父母儿媳早产、婴儿已夭折之事。
十多天后父亲回信说,寄来的3元和5斤粮票皆收到勿念。对信中所言如蕙二月中旬生一男娃不够月份糟踏了,深为惋惜。还说,常言说早生儿不容易活,这也是他命里注定,你劝如蕙要把心放宽,妇人家总是心窄,你要多去信劝说她不要太伤心,给你上海的岳父母去信多说宽慰话、感谢话,多年的打扰,我们抱歉得很。如蕙调养好身子,回来时希望能把晶娃儿带来到咱们家休息数日,全家老小十分想念她和娃娃。我本打算如蕙出月后去省城看看大人和娃娃,不料自正月十六日有病以来不能行动,真是天不随人愿,心有余,力不足。你弟清娃因学校分配学生下乡劳动到水利工程上干活,已去了半个多月还没回来,训人很不放心……这天午后,天空飘动着云块,阴晴无定,曾源正在聚精会神地编报,忽听到有人敲门。
“进来。”随着推门声,一缕阳光入户,室内猛地一亮,进来的两个人使曾源又惊又喜。
“大,红红’这么远的路你们咋吃得消?累坏了吧一一”
进来的两个人:一个是曾源的父亲,另一个是他的妹妹红红。三年不见,又是在这苦寒岁月,在曾源眼里,父亲和妹妹的变化都很大:父亲已经完全苍老了,满头华发,皱纹深深,气喘吁吁,言谈举止都很吃力。这年正是父亲花甲之年,若逢好年盛世,有吃有穿,应当说安度晚年才刚刚开始,不至于衰老到如此地步!妹妹红红长高了一个头,十二三岁的女孩,已及花季年岁,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肢体单薄’只有那弯弯的眉毛下一双秀目闪动着善良和聪慧的目光。
曾源给父亲和妹妹倒了半盆热水,让他俩擦擦脸。唯一能够拿得出来入口下肚之物,只有这白开水,洗尘有余,接风无力。这年头,大家都在挨饿,父亲不远千里而来,无力给儿子带点家乡的土特产,儿子接待父亲和妹妹的也只能是两手空空。
曾源问父亲我妈还好吗?”
父亲回答说身子骨比不上前几年了,不过还是比我强,妇人家耐饿么。麻鞋厂早都关闭了,想做活没活做,成天念叨你们,过完年就催我动身来看你’腊月里你寄来的3元,你妈省吃俭用,留出一半钱给我和红红做盘缠,要不还动不了身哩。”
对于儿子的公务诸事父亲历来不过问,他认为公事不比家事,不能乱插嘴,给儿子为难,自己也不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最关心的是儿子的生活,时下饥饿遍神州,最要紧的是“吃粮”二字。父亲原以为,当兵吃粮,不愁温饱,儿子参军离家后,他先后两次到队伍上探亲,军队食堂里的饭菜,顿顿胜似自家过年;如今儿子到了“军队农场”,沾了“军”、“农”二字还能饿肚子?听了儿子对当年农场职工口粮标准供应情况的介绍,与老家那边城镇居民的标准不差上下,出乎他的意料,后悔不该来给儿子添麻烦。
儿子十分关心家乡的情况和亲朋故旧的现状。
“唉!”父亲长叹一声,又摇摇头说,“都不好过,只不过一家不知道一家。你二舅去世这你知道,没想到去年腊月你小舅连饿带冻也走了他是个伤残人又心直口快,得罪了一些人,这么着粮食局看大门的事人家不让他干了。在家闲蹲了一年多’心里不畅快,加上吃不饱肚子就抗不过来了。曲健老师家也很孽障,那么有学问,有名望的人家,自从打成右派后,连个平常社员也不如,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拿到街上换菜、换洋芋吃了,这世道变得让人不明白了……”
曾源父亲和红红这次来农场,住宿方面不存在问题,因为与曾源同住一室的老张经常回家去住,遇此情景,更是乐意礼让三分,把床铺腾给曾源他们住。这样一来,父亲和红红同住一张床,曾源个人住一张床。同住一室,吃饭、说话都比较方便。问题还是出在一个“吃”宇上,食堂不开早饭,午饭多是芽麦面拌芥籽粒(类似骆驼茨的野草籽)窝窝头,加上一勺清水煮白菜;晚饭千篇一律是菜汤里加了屈指可数的面片。就这样,两顿饭的定量十分有限,吃到肚里别说是充饥,肚子都暖不过来哩!不用说父亲、妹妹此来,将使曾源当月的口粮做出“分外付出”,不到月底就得打好几天的饥荒!在农场呆了两天’曾源父亲感觉到这地方荒凉、寒冷、风沙大,远不如家乡那边,这时候早巳花红柳绿,一片春光了。父亲亲眼看到儿子这边也是饿肚子,媳妇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孤孤零零,也怪可怜的。便不忍心让儿子作难。住了两个晚上,执意踏上归途。此行真可谓抱着希望而来,背着失望而归。
曾源从同室伙伴老张处借了5斤粮票,又找分管财务的副场长恩准预支下月工资3元,同坐一辆去西河堡的拖车,将父亲和妹妹送上火车。
东去的列车颤抖着、吼叫着缓慢地启动,可怜兮兮的两张脸向车后眺望。曾源不住地向亲人招手,直到列车从他的视线里消失。谁会想到,这次惜别是儿子在父亲生則见到的最后一面。
曾源眼眶内溢满了泪水,心里塞满了愧疚、苦涩和无奈。
过了清明,时值青黄不接的季节,饥饿最是难熬。粮票贵如金,半个馒头记恩情。送别父亲半个月后,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以很重的分量讲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父亲说:“有件要紧事,咱们在农场见面时我忘了告诉你。现特意写信说明,我和你妹妹来农场看你,在西河堡下了火车,遇到一位姓裴的同志,是个好人。我去买汽车票,因为来时没开上介绍信,站上不给卖票,幸亏遇到裴同志,亲自为我们买上了车票。那天我和你妹妹离家后一天多时间没吃上一点五谷,饿得厉害,你妹妹忍不住直叫唤。裴同志赶紧把他口袋里装的馒头取出一个给我们吃:我吃了一口,大半个都给红红吃了。你往后再和他见面时,一定还给人家一个馒头,代我好好感谢人家。啥时候咱们都不能忘掉人家的恩情。”
赤诚之心,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跃然纸上,真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饥饿使人们的心灵变得纯粹、直接而又恩怨分明。
信中最后提到父亲回到家中后,病情益重,什么活都不能做了。
曾源心中怅然,有苦难言。无力赡养父母,不能提携弟妹,既惭愧,又愤慨,枉为人子,枉做兄长,人生的道路为何如此艰辛!
此后数月曾源一直没有接到父母和妻子的来信,这使他内心十分焦急,但又害怕突然来信一来信必有事,有事添愁肠,还不如眼不见,心不烦,麻木比清醒好,至于未来将会如何?且莫管它,过一天算一天……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农场在“一大二公”方面使劲发展,一年多时间内,将原先归县上领导的六七个国营农(林)场和一个人民公社并入“红星农场”,地跨三个县,从南到北一百多公里,全民、集体两种所有制并存其间,工、农、商、学、兵熔为一炉,各种先天性的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地一并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