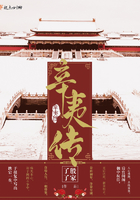正如我所说,危机总在信贷繁荣之后发生。而目前的监管体系无法做到在繁荣时期抑制信贷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进程。那么,如果不能抑制信贷本身,为繁荣之后的萧条时期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将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增量挂钩的办法,有助于敦促银行在繁荣时期增加资本储备。
这种改进方法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制。打个比方说,水坝在洪水(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蓄水,以备干涸期(萧条时期)之用。与这个比喻不同的是,在金融领域“蓄水”应该是个自动的过程,而资本充足率—资产增量挂钩机制能够实现自动调节。
记者:这样的改进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古德哈特:如果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那么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抵押贷款可能从资产价格较高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抵押贷款增量将日益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可能使位于发达国家的相关金融机构以及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分支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
另外,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挂钩的做法,将进一步刺激银行努力将资产转移给准银行机构。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
当然,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国家干预的短期行为
记者:您认为,危机当中和危机过后会不会迎来“金融凯恩斯主义”?目前,所有人都主张加强监管,有一些人进一步主张更强的国家干预,而另一些人则持谨慎态度。
古德哈特:这要分长期和短期。在短期,国家干预或者说“凯恩斯主义”是有效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最有效地解决了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流动性问题,包括国有化也是一样。而改革监管制度需要的时间相对漫长一些,难度也比较大,在当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操作,因此从短期来看,国家干预是解决危机的最好途径。
不过,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人希望被长期国有化和被国家干预。因此,这种国家干预将在危机过后逐渐演变成国家参股,再后来这部分股权也会转移到私人部门,这是中长期的事情。
当然,国家要在这次危机过后起更大作用,要改善现有的监管机制并很好地执行,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所定义的“短期”是多长?
古德哈特:每个人都希望这个短期尽量短。不过,现在金融领域的崩溃与实体经济的衰退已经交织在一起了,这将使金融机构的违约和倒闭进一步加剧。因此,很难说经济衰退到底会持续多久。在日本,这个时期是十年。非常低的增长加上艰难的经济环境,使得这段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我没有说美国和欧洲将会经历类似相同的场景,但是我认为,这轮危机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所有危机持续的时间都要长。
记者:怎样评价人民币停止升值的做法?这是不是中国运用国家干预在危机中保全自己的合理选择?
古德哈特: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比如出口会面临外需下降的难题。目前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起到实效,能有效地扩大内需。我关心这次危机是否会阻碍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进程,因为国家对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干预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特别是在严重的危机下,这是有效的处理方式。西方世界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中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强度。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还是应该继续向市场决定汇率迈进。
必需的欧洲合作
记者:危机是否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
古德哈特:当前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向金融系统注入资本和流动性的操作都只能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做这件事,国际清算银行则根本没有钱,其他机构就更只是纯粹的讨论场所。这样,国际监管者就不可能执行监管的任务。
记者:英国首相布朗、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等人主张“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您对“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提法有何评价?
古德哈特:我认为这纯属政治口号。我不知道布朗首相到底要什么,也许是以此来争取一个讨论加强国际监管问题的议题。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来支撑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二十国集团要讨论这个议题,那是不会产生实质效果的。
记者: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概念?
古德哈特:我认为,有一个事情与此相关,就是欧洲的联合在这次危机中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所有的救市措施都只是在国家层面上独立进行,之前没有任何磋商和协调,欧洲联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部分原因在于我所说的缺乏统一的欧洲财政当局,这是欧洲在危机中最危险的地方。而一个良好的局面应该是欧洲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协调各方利益。也许真正需要做的是加强欧洲合作这件事。
中国的问题与机遇
记者:以您的观察,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将受何影响?
古德哈特: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谈到中国经济“经历着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的出口行业将会因为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萎缩而出现一些麻烦——当然,我认为这也许正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好机会。
长期依赖出口创汇,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的不足。今后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等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必须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国内需求。我想,这应该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一些观察家的共识了。
记者:那么,应该如何刺激内需?
古德哈特:首先要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国内需求不足,部分来源于投资过剩、储蓄率过高。当然,我知道东亚国家都有储蓄的文化传统。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储蓄率过高恐怕还因为国民的不安全感,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很多人担心退休后没有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因此,必须扩展“社会安全网络”,让国民更多地享受社会福利,这样才能够降低储蓄,鼓励消费。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的金融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
古德哈特:怎样评估海外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如何管理巨额外汇储备,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和执行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
我个人认为,美元资产在一两年内还不会成为优质资产,投资美国不是一个上佳选择。不过,鉴于中国手中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怎样处理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其中也许不光有保值方面的考虑,还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
记者:您提到您正专注于经济史的研究。那么,从您的角度,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今后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古德哈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30年间,中国解决了国内的温饱问题,经济经历了几次飞跃,并且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就个人生活而言,我所接触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在30年来有了奇迹般的提高。比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前来进修的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也包括普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显然,他们在伦敦这个昂贵的城市的生活水准并不差。总之,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显而易见。
然而,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深刻的问题。比如,中国一直过于依赖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创造外汇。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但是一些特定的群体可能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长。
我认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需要重新定位(rebalance)——这并不是否认中国走过的道路,而是在新的情况下不能总是走过去的老路。我相信,中国有机会摆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并让她的人民更多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
我了解现在中国正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也有很多人谈到下一个30年怎么办。以我目前从事的经济史研究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持续60年保持平均10%的增长。因此,即使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再持续10年,这个速度也总会降下来。那么,怎样使经济在高速增长结束后适应新情况,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摆在下一个30年的议程中。
再深入一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继续讨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比伦敦更摩登、更像个现代化大都市了。这个很令人振奋。不过,现代化的含义可能是多重的。物质世界的现代化有一个极限,达到这个极限后就不再有现代化的问题;而怎样使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更多的尊重,这可能是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只有实现人的价值,我和我的同事(其中包括我的中国同事)所从事的金融工作才真正有意义。
目前,中国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就符合这一逻辑,需要在现实层面做更多的事来实现“和谐社会”的要求。其中,实现产业升级、保护劳动者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都是这些现实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