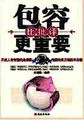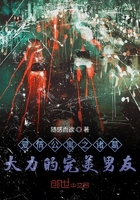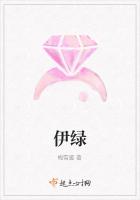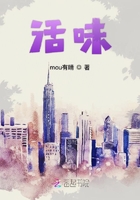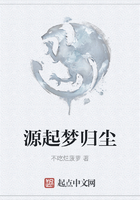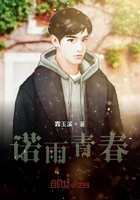说起北魏孝文帝,许多人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位鲜卑族皇帝为了推行汉化,不但改头换面迁都改制,还搞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人之举,比如把自家的姓氏从“拓跋”改成“元”,籍贯从“代北”改成“洛阳”,这在当年可都是离经叛道的事儿。更邪乎的是,后来他把自个儿的太子也给弄死了。
说起他这太子元恂,御用史书上可没多少好字眼儿,什么不好学啦,有谋朝篡位之心啦,等等等等。可仔细看看就能发现,这位太子爷到死也不过15岁,无非是个半大孩子,而且自己差不多是毫无争议的合法皇位继承人(弟弟年幼而且懦弱),不好学算不得大罪过,谋朝篡位更不符合逻辑。他真正提得上台面的罪,就是对汉化的消极怠工。
原来元恂体型保持得不怎么样,体重超标,他待在北魏老家平城(山西大同)倒没什么,跟老爹一起搬到洛阳后便热得浑身痒痒,加上洛阳人说话他听了跟听外语差不多,汉人的衣服他穿了也别扭无比,一时想不开便离家出走,想跑到平城老家避暑度假。结果怎么着?孝???帝派人把他大老远逮回来,亲自打了个半死扔进牢里,没多久就废去太子称号,一年之后索性被毒死了。
有人说,这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当时反对改革的势力太强,人数太多,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跟皇帝对着干,不得不杀鸡给猴看。可问题是,这猴也未免太大了点儿吧?
孝文帝改革的榜样之一,是战国时候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要说赵武灵王改革的时候,碰上的阻力也不小,朝廷里支持他改穿“西装”的不过小猫三两只,反对他的可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叔叔公子成。这位尊亲不但自个儿反对,还串通朝廷大臣一起给武灵王穿小鞋,最后干脆泡病号,弄个留职留薪回家静养,给侄儿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可人家武灵王不但没给处分,还跑去叔叔家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害,最终换取对方的合作。
要说改革阻力,武灵王碰上的不比孝文帝小,基本上都是大半个政府班子加上大多数家庭成员集体反对的格局。要说改革的迫切性,武灵王比孝文帝更急,因为赵国当时面临的是强敌环伺,不改革弄不好就亡国的生死关口,而北魏那会儿已经兵强马壮,国富民强,是整个东亚版图上的第一超级大国,改革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说错误的性质,刨去那些不可靠的虚词,元恂也不会比公子成更严重。没错,元恂杀了个叫高道悦的跟班,可按帝王时代的标准这根本不算什么(汉武帝的太子刘据真的造反,一个看坟头的小官田千秋发表学术论文,认为应该处以打一顿屁股的惩罚,汉武帝居然表示赞同)。他反对改革的具体行为,不过是不穿汉服、不学汉话(这还有些生理和天资问题)和自个儿跑回老家探亲,比起公子成串通朝臣装病对抗,至少不会更严重,而且论血缘怎么也是儿子更近吧。怎么罪过差不多,孝文帝就没武灵王的耐心,而元恂就没公子成的好命呢?
问题就出在那个多半子虚乌有的“谋朝篡位”上了。北魏从第一个皇帝什翼健算起,拓跋
、拓跋焘等几个有作为的皇帝都死于“自己人”之手,这使得历代北魏皇帝对自己的宝座格外杯弓蛇影,比历朝历代都变态,甚至明文规定立谁为太子,就立马把太子的娘给杀了。在这种情况下元恂敢公然跟老爹对着干,那位老爹兼皇帝能作何反应,不是明摆着的吗?没错,元恂这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多半不会真的想造反(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问题是,皇帝宰人与否的关键,从来就不是被宰的人如何想,而是他这个有权宰人的主儿如何想。
公子成固然是武灵王的叔叔,但本人对王位似乎没啥兴趣,就算有兴趣,隔着武灵王的俩成年儿子,他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没了这重最要紧的顾虑,武灵王当然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和谐公子成,而不必弄得血淋淋的,毕竟说到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改革进程的最坚实、最有力保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