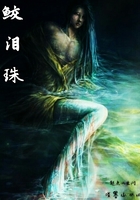对庞婉青来说,那个夜晚是疯狂的,终生难以忘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唤起了她对生活的兴趣和热情,让她觉得活着其实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说也奇怪,庞婉青第二天在镜子里发现鼻子旁边的几颗红疙瘩不见了,皮肤显得光滑滋润,她觉得自己是一朵花,多日没有浇水,就快要桔萎了,“坏蛋”一晚上辛勤的浇灌,使她立即又变得鲜艳娇嫩。
“坏蛋”把手放到嘴里吹了一口气,笑笑说:“你可真狠。”
“我……”庞婉青心里酸了一下,眼睛就发潮了,“对不起啊。”
“没事,呵呵,希望你更狠一些,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坏蛋”朝她眨了一下眼,言词暧昧。
“你……”庞婉青又晃了一下兰花指,但是没有出手,他的眼情和话意,让她感觉到一种调情的情调,贴心而又温存。她望着面前这个比她整整小了十岁的男人,眼光里射出了绵绵的爱意。“……真是坏蛋。”
“这两天忙什么?”“坏蛋”关切地说。
“你说能忙什么?忙着想你。”庞婉青装做漫不经心地说。
“还赌六合彩吗?”
“昨天买了‘一只小号的马’,输了五百块。”
“告诉你别再买了,中奖机率很低,钱都让庄家赚走了。”“坏蛋”轻轻叹了一声,像是慈祥的老爷爷语重心长地说,“你也真是,怎么就迷上这地下六合彩?以后别再买了,难道你还想靠这发财不成?听我的,从明天开始金盆洗手。”
“我买的也不多,只是有时无聊才买一点。”庞婉青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低着头小声地说。
这时,“坏蛋”的手机响了,他拿在耳边听着,嘴里应着:“好,好,知道,知道。”手机里漏出一些话声,让庞婉青听了个大概,那地瓜腔的男声显然是他的老板,让他把市场调查报告尽快送去。“坏蛋”挂了电话,脸上飘起一丝无奈,带着一种愧疚和歉意对庞婉青说:“你看,我刚出差回来,老板就催命鬼一样催要调查报告,我本来还想下午在这里和你好好说些话,晚上共渡良宵。”
庞婉青喝了一大口杨桃汁,好像被呛了一下,呼吸突然变得急促,一手抓住“坏蛋”搁在方几上的手,说:“现在才一点多,你三点再回漳州。”
“坏蛋”显得很善解人意地笑了一下。
几分钟之后,如痴如醉的狂欢便在美仁小区一套布置得很温馨的房间里开始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分别搭坐一辆三轮车,一前一后走上房间。这里是庞婉青租来用于和“坏蛋”约会的。她打开门锁时,手一直在颤动,刚进了门她就不由靠在墙上,长长地呼了口气。楼梯上传来了“坏蛋”的脚步声,她心里砰砰直跳,好像十几年前第一次被男朋友搂在怀里。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过渡,两个人的眼光稍一接触,便有如电闪雷鸣,情欲的烈火立即把他们烧成一团。
等到火慢慢地熄灭,庞婉青感觉自己像是一堆灰烬,徐徐地冒着烟。这是一种激情的燃烧,一种生命的燃烧,庞婉青犹如凤凰浴火重生。
“坏蛋”跳下了床,从地上捡起短裤、袜子,就往脚踝里套。他弯曲的腰身像是一张弓,紧凑有力,总是能让庞婉青看得心跳不已。
庞婉青躺在床上不想动,也似乎动不了了,全身绵软无力,眼光显得迷离闪烁。望着“坏蛋”的侧影,她的心里柔情荡漾。
“我现在得走了,我一忙完就来看你。”“坏蛋”一边提上裤子一边说,他走回到床前,低下头亲吻了一下庞婉青的额头,一根手指头弹了弹她的鼻子。
庞婉青轻轻喘着气,像一个受宠的孩子似地发出幸福的微笑。
“坏蛋”走到门边,摸了一下口袋,自言自语地说:“糟糕,出差回来身上都快没钱了。”
庞婉青连忙用一支手支起身子,对“坏蛋”说:“我包里有二千块,你先拿去用。”
“坏蛋”走了过来,抱住庞婉青的脸,亲吻着她鲜红的嘴唇说:“你是一朵花啊,刚给你浇水施肥,你就变鲜艳起来了。”
“是啊,花儿不能缺水啊。”庞婉青说,“我包里有钱,你都拿去吧。”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
“这有什么?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啊?”庞婉青爬起了身,弯腰从地上捡起她的挎包,拉开拉链,掏出一叠钱就塞到“坏蛋”手里。
“那我不客气了。”“坏蛋”说着,把钱收进了口袋。他走到门边,回头对庞婉青做了个飞吻。
“坏蛋”轻轻带上门走了,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庞婉青又躺了下来,刚才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她需要再休息一会,顺便把刚才的经过在心里回味一遍。
“坏蛋”年轻气盛,孔武有力,更重要的,他懂得女人,懂得一个比他大的女人。
他的动作熟练准确,粗犷而又充满温存,他的许多姿势看似色情淫荡,却又不失一种儿童般的纯真和本色。当庞婉青翻身上来,把他坐在屁股下面,把他压在身体下面,看着他年轻漂亮的面孔沉醉在快感的高潮里,她全身就激荡起骄傲和荣耀,在这时候,在马铺还有哪个女人比她更有成就感吗?她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了不起的女人。
刚刚上初中时,那些嘴唇上面刚刚长出胡须的小男生就开始给庞婉青递纸条,对她挤眉弄眼,在她身后唱歌、吹口哨、怪声尖叫,让她觉得很可笑。上了高中,庞婉青变得更漂亮了,像是一轮初升的明月,皎洁动人。很多男同学都不敢看她,至少不敢公开地正面地看她,她身上那种高贵而冷漠的气质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知道那些男同学特别渴望看她,特别渴望和她说话,但是他们心里在发抖,这些也许才学会自慰的小毛孩没有勇气,更没有自信。
上了邮电中专之后,班级里一个自称最英俊的男同学公开宣布要把她追到手,那天傍晚,她站在宿舍楼前的一棵树下,穿着一条绚丽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出席一场盛大的舞会。那个英俊的男同学鼓起勇气走到了她面前,有些紧张地说,我晚上请你看电影好吗?庞婉青轻启朱唇说,谢谢,我男朋友要来接我去外贸酒店跳舞。这时一辆本田125的摩托车轰鸣而至,庞婉青很熟练地踩着脚架登上车,侧身坐好,把飘起的裙裾往下捋了捋,一手搂住了骑手的腰身。那个男同学看得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他痛苦地冲上宿舍楼后面的小山林,像受伤的狼一样嚎叫了一声,据说他后来成了一个诗人。
那时庞婉青的男朋友是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他父亲是省直机关的一个处长,他很有信心地对庞婉青说,他父亲绝对有能力把她留在省城。一个狂风暴雨的台风之夜,她回不了学校也不想回去,像猫一样偎在他的怀里。那是在他家他的房间里,窗外是风雨交加,床上是心旌摇荡,他一双手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动作力度也越来越大。很快,她全身被脱得精光,她突然很害羞似地直往他怀里钻。那天晚上,庞婉青感觉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这个男人了。可是那年暑假,庞婉青回马铺没有几天就觉得心烦意乱,往他家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他也没有写信来(那时她家还没有电话),她似乎预感到事情起了变化,第二天就跟父母亲撒谎说学校有事,匆匆赶回了省城。她从车站下车就直接打的来到他家,门铃按了半天,他家那个农村来的保姆才打开一道门缝,探出头来发现是她,告诉她说他出国去了,给她留了一封信。她一下知道出事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那封信是他们分别两天后写的,他在信上说他们不大合适,还是尽早分手为好,长痛不如短痛。分别的那个晚上,他一点也没有透露他就要出国的信息,而实际上他都已经办好签证了。庞婉青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欺骗,心如刀割。她把那封信撕碎了,把纸屑和着眼泪揉成了一团,扔进学校那口人工湖里。有好几次,她想闭上眼睛纵身跳进湖里,一切痛苦就全都解脱了。可是想到湖水将把她淹没,水草将缠满她的全身,她就退缩了。在最后的一学年里,庞婉青变得郁郁寡欢,她的同学们很快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女同学一个个幸灾乐祸似地笑逐颜开,男同学看她的眼神则显示出严重的鄙夷。毕业了,她心灰意冷地回到了马铺,在邮电局办公室干了几天,就跟老主任闹了矛盾,不久就转到财会科当了出纳。
庞婉青在邮电中专的伤心往事,马铺人几乎没人知道。那是1987年,她刚刚22岁,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不断有蜜蜂向她嘤嘤嗡嗡地飞来,在周围缠绵地飞舞。她并不驱赶这些别有用心的蜜蜂,但是谁也别想停在她的花心上采蜜。一个晚上,她独自一人在中山路逛街,准备买一件秋衣,但是走过十几间店,没有一件衣服能入她的眼。在经过民主路口时,她看到了老同学陈炳星,小时候她也住在大庙街,他家就在她家的斜对面,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他们一直都是同学,所以她能认得他。陈炳星也看到了庞美女,脸上有一种惊喜的表情。因为比较了解庞美女的情况,陈炳星对她从未有过非份之想,反而显得坦然大方,向她叫了一声,阿青。庞婉青想起小时候陈炳星就是叫她阿青的,有时候还会一起去摘桑叶,上了中学之后则形如路人,需要叫她的时候就叫“哎”。那天晚上,庞婉青听到陈炳星叫她阿青,像是故人重逢,觉得很高兴,就问他现在做什么,要去哪里玩。陈炳星说他第一年没考上,复读两年都没考上,现在又在马铺一中读“高六”。庞婉青哦了一声,看着陈炳星结实的小个子,理着一个短短的狗啃式的发型,觉得他真有些可怜。陈炳星说,我没有你那样好命啊,现在都出来工作赚钱了。庞婉青笑了一笑,“好命”这个词让她感到意味深长。谁知道她的命运也正是从这晚上开始新的变化呢?那天晚上,她跟陈炳星来到解放广场边的一个大排档,见到了几个在等陈炳星的同学,但她这个不速之客更受欢迎。她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唯一不是同学的那个人,后来成为这个人的老婆。
庞婉青沉沉睡了一觉,醒来时房间一片漆黑。她的手在床头的低柜上摸了一阵,才找到台灯的旋钮。把台灯打开,她从包里取出手机一看,时间是8点15分了。她佩服自己真能睡,也许真是太疲惫了,这一觉从阳光高照睡到星星满空。
庞婉青冲了个澡,穿上衣服来到了街上。满街灯光闪亮,自行车在人群中蜿蜒地穿梭往来,不时有摩托车从面前呼啸而过,总是要把她吓得毛骨耸然。马铺这几年的发展,就是摩托车骤然增多,像响尾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庞婉青很不喜欢这种混乱无序的场面。
她肚子饿了,可是到哪里吃饭呢?她一下想起江滨路的七匹马大排档,那条路经过改造,变成了江心公园外围的一条通道,一到夜间两边就摆满了大排档。
七匹马大排档是陈炳星开的,她去过几次,感觉那里的空气很好,老同学的厨艺也不错。
6、陈炳星
天气太热了,有些人不喜欢在饭店就餐,尽管封闭的房间里有空调一直吹着,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在敞开的大排档吃饭,吹吹大自然的凉风。在江滨路的大排档里,陈炳星的“七匹马”算是个历史悠久的名牌。
那块“七匹马大排档”的广告牌靠在平板车的车轮上,这是陈炳星用红漆亲笔写的字,看得出有些书法底子。油烟将牌子熏得很脏了,但那六个字还是很显眼的。每天七点左右,他和老婆和两个雇工刚刚摆好摊位,就会有生意了。陈炳星是主厨,老婆阿春负责点菜,也给他打下手,两个雇工则是端盘子、收拾碗筷和洗盘子全包了。
来了几伙散客,因为没有喝酒,吃完就走了。有一伙四个人的常客在一棵龙眼树旁喝酒,他们点的菜都上齐了,陈炳星走过去向他们每个人敬了一根烟,说了几句话就回到摊前,坐在塑料椅子上抽烟歇口气。
那两个雇工蹲在大水桶前洗着碗筷,她们都是从阿春老家土楼乡来的妹子,手脚很麻利,把洗好的碗盘放到另一只水桶里,过一下清水便捞了起来,又摆到平板车上。陈炳星的眼光向路的两边转着,主要是看有什么人来,不经意间就落在了那两个蹲着洗盘子的雇工身上,她们的五官长得比较土气,但是年轻饱满的身体,曲线突出,还是让他的眼光有些发烫。
街灯都亮了,“七匹马”前面就是穿城而过的越来越狭窄的蓝水江,这些年来蓝水江水流越来越小,马铺人都说像是小孩子撒尿似的。去年,下游建了一座拦河坝,江心公园这一段的水域才积了一些水,虽然水质污浊,但夜幕下也看不清楚,灯光一照,还是有些波光粼粼的意境。隔着蓝水江,对面是马铺县国土大厦,八层楼的楼顶上安装着一块“七匹狼”的大幅广告:与狼共舞,尽显英雄本色。灯光照射着这一行字和一匹正在狂奔的狼,老远就可以看到。
到“七匹马”来的人,有时就会问陈炳星:你这七匹马是不是模仿人家七匹狼呀?陈炳星连忙解释说,我读书的时候,班级里有七个同学经常玩在一起,像个小帮派一样,正好我们都属马,大家就叫我们“七匹马”。陈炳星说,那是1985年呀,那时有“七匹狼”吗?有吗?你听说过有吗?要是当时我有商标意识,注册了“七匹马”,那“七匹狼”肯定就注册不了啦。陈炳星一副很惋惜的表情。他十三岁的儿子陈天成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七匹狼”的广告,有一天就对他说,人家“七匹狼”做得多大,有茄克有皮鞋还有香烟,你那“七匹马”却只是个大排档,你也太没出息了吧?陈炳星愣了一下,真想抽儿子一巴掌,老子要是没出息,还能在这世界上生下你这个鸟儿子吗?
陈炳星接连参加了四年的高考都没考上。1988年的最低录取线公布了,他还差了19分,心里很不死心,但全家人都对他没信心了。父母亲都是城关的农民,以卖菜为生,也赚不了几块钱。父亲对他说,看来你没那个命,捡猪粪就捡猪粪,不要羡慕人家穿皮鞋上班的。那些天是陈炳星人生最苦闷的时期,班级里第一年就考上的同学,有的读的是两年大专或中专,都回马铺工作了,就是读三年大专的也回来了,而他却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在他们的“七匹马”里,两匹第一年考上,两匹复读一年考上,再两匹复读两年也考上了,只有他复读了三年还是名落孙山,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匹劣种马、一匹驽马。好几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在蓝水江边走来走去,心情坏到了极点。有一天晚上,他正看着水面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发呆,突然一块石子打破了水面,激起水花溅到了他的身上,他回头一看,只见罗汉城笑呵呵地走过来。罗汉城是“七匹马”里的老马,第一年就考上了厦门一所大专学校,刚刚毕业分配到马铺统计局工作。他对陈炳星说,我到你家找你啊,你不在,我就想你能到哪里呢?随便往江边走来,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是不是想不开想跳水啊?陈炳星推了罗汉城一把,骂道,干你佬,谁想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