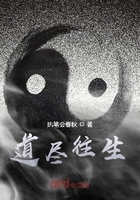黄小琼迈着模特似的步子走过来,说:“催命鬼啊。”她坐进了车里,不满地撇了撇嘴说,“见个副书记,你就激动成这样?省长我都见过了。”
“约好了时间嘛。”黄进步踩了油门,车就跑出去了。他想见丁新昌,到他宿舍好好跟他谈一次,已经筹划很久了。黄进步至少给他打过20次电话,他都说没空,改天再联系。一个副书记兼副县长肯定是很忙的,就像成语说的日理万机那样,而且最主要的,还要看他愿不愿意见你。不过这点黄进步还是有把握的,毕竟他们是同学嘛。
那么多同学中,丁新昌能出人头地混到目前遇大的副处级,令黄进步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同学里,丁新昌是毫不起眼的一个人。那时黄进步父亲是城郊的农民,在城里开了一间废品收购店,有些同学瞧不起他,而他那时对班上几个同学更是瞧不起,其中一个就是丁新昌,他家来自农村,穿着土里土气的,相貌平平,学习成绩也很一般。有几次,忘记了什么事,他扬言要揍丁新昌,有一次还当着许多同学的面,踢了丁新昌一脚。谁知道丁新昌那年高考发挥特别好,考到了412分,刚刚上了师大的本科线。大学毕业那年,他主动要求到贫困县任教,就被分到了马铺隔壁的大坪县的一个乡村中学。那个穷乡很少有大学生分配来,乡书记没几天就把他从乡中学借调到乡里写材料,没多久他的关系就转入了乡政府,算是改行了。三年后他当了副乡长,后来又当了乡长,再后来就调到大坪县农业局当了局长,再后来就当了大坪县副县长,去年初他调到了马铺县,算是衣锦还乡,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县长,明摆着下一届是要当县长的。
丁新昌到马铺上任后,开头住在马铺宾馆的一个套间里,黄进步打听到房间号码,就提了一条中华烟一瓶五粮液和一箱蒙牛牛奶去拜访他。黄进步刚报出姓名,丁新昌就说老同学啊,十多年没见面了。没想到他还记得老同学,这让黄进步惊喜交加。那天丁新昌把烟酒退了,说看在老同学面上,收下牛奶,正好当作睡觉前的点心。后来,黄进步又到宾馆和办公室找了他许多次,每次他都坚决不收黄进步的礼品,每次黄进步都想谈点比较重要的的问题,他都是避重就轻,有意转换话题,净说些哪个同学现在如何,哪个又怎么了,谁胖得走了形,谁还保持当年的身材等等。丁新昌属于开始发福的典型,而黄进步还差不多像二十年前一样瘦。黄进步说他从高一年起就得胃病,几年前把胃切掉了一半,怎么吃也胖不了。丁新昌说还是瘦点好,以后老了少得心血管疾病。几个月前,丁新昌搬进“白宫”的宿舍后,黄进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黄进步的宝来车穿过几条街,驶向马铺县政府大院后面的“白宫”。这是一幢刚刚修建不久的五层楼,外墙刷得非常白,马铺民间称之为“白宫”。这里住的是家不在马铺的副处级干部,也就是说,“白宫”是家在外地的副处级干部的宿舍,所有配备都由政府提供。丁新昌的宿舍就在这里的302室。
“白宫”门卫拦住了黄进步的宝来车。黄进步放下车窗说:“我找302丁副书记,有预约的。”门卫抬手放行,宝来车缓缓驶到楼下停了下来。这里有一大片绿地和水池,像个规模不小的广场,空地上零星停着几部车。
黄进步带着黄小琼走到楼道口的可视对讲机前,按了一下302,恭敬地对着探头说:“丁书记,是我,进步。”
铁门啪地开了。
黄进步带着黄小琼走进丁新昌的宿舍,发现他看黄小琼的眼光有些异样,连忙介绍说:“这是我老婆,也姓黄,黄小琼,叫她小琼就行了。”
“丁书记你好。”黄小琼扭着腰肢,向丁新昌伸出了一只纤细的手。
“好好好。”丁新昌握了一下黄小琼的手,“来来来,请坐。”
丁新昌的宿舍是一个三房二厅138平米的套房,装修豪华,各种家具电器配套齐全,和黄进步家有得一拼。难怪马铺民间说“白宫”是一座腐败楼。对丁新昌来说,一周一般也就在这住二三个晚上。
黄进步在黑皮沙发上坐了下来,对丁新昌说:“丁书记好忙啊,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最近是忙了一点,正好晚上没事。”丁新昌说,“不好意思,你们先坐会儿,我进去把电脑关了。”
趁他走进书房的一会儿,黄进步和黄小琼观赏着客厅的摆设,相互点着头表示赞赏。电视柜上有几只青花陶瓷,看起来很珍贵。等丁新昌一出来,黄进步便忍不住地说:“丁书记,你这几个瓷盘很值钱啊。”
“那不过是赝品,要是值钱的东西怎么摆在宿舍里?要拿回家珍藏了。”丁新昌在茶几前的矮沙发上坐了下来,准备开始泡茶。
“茶让小琼来泡吧。”黄进步说。
“怎么能让客人自己泡茶?”丁新昌说。
“丁书记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是同学,我们都属马,你比我大几天,就是我的大哥,小琼就是你的弟媳,让她泡个茶有什么?”
黄小琼就把身子往前倾,提起电磁炉上的水壶冲洗着茶盘,说:“我来泡嘛,给大哥泡茶也是应该的。”
丁新昌笑了笑,表示同意了。
“以后你这里要拖地板洗衣服什么的,叫她来也行,自己的弟媳嘛。”黄进步说。
“这可使不得。”丁新昌摆摆手说,他坐到高背的沙发上来,仰头靠在高背上,突然发出一声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啊,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黄进步接上话头说:“当年我们都还是傻乎乎的毛头小伙子,现在都四十岁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最杰出的就像丁书记你这样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你真会给我戴高帽。”丁新昌说,“同学面前,都说人话吧,你说我算什么,不过运气好,当了点官,倒是你不容易,靠自己本事,打拼出一番事业,每年为我们马铺缴纳不少税收啊。”
黄进步受到了表扬,心里很受用,脸上笑得肉都不够用了。
“来,丁书记,喝茶。”黄小琼泡了三杯茶,把第一杯端到了丁新昌手里。
“最近你的铁厂效益不错吧?”丁新昌喝了一口茶说。
“还行,去年更好一些。”
“要注意环保,杜绝污染,上头很重视,可能过一段还会下来检查。”
“我知道,我很重视环保的。”黄进步说,身子往丁新昌方向探过去一些,声音同时低了一些,“丁书记,机械厂那块地是不是要卖了?”
“到时会出公告,公开招标,现在都得这样做。”丁新昌说。
黄进步微微一笑,笑得有点神秘,有点无所不知,丁新昌说的固然是目前流行的做法,但这后面照样有文章可做,道上的人谁都明白。所以他将微笑持续了十几秒,说:“丁书记,你要多关照啊。”
丁新昌没有回应他的话。他又喝了一杯茶,换了个话题说:“我们要开同学会了,你知道吗?”
“哦,我听谁说过,二十年了,应该好好纪念一下。”
“准备下个月在紫荆湖开,大家同学一场,也是缘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捐点款吧,5千块。”
“食宿费用全由顾明泉包了,不过你想捐款,我看也很好,可以成立一个同学基金会,同学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可以从基金里拿点钱出来慰问。”
黄进步连连点着头。说到同学,他一下想起那年的歌咏比赛,在一次排练中,他站在安佳佳后面,把她那显现出来的乳罩带子想象成弹弓的橡皮筋,一下一下地拉着,突然刘锦标扫了他一眼,他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突然他想起那次踢了丁新昌一脚,他就是瞧人家不起,看他走过来了,没来由地就抬脚踢去一脚……蓦地,他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不知丁书记还记得那一脚吗?他想自己当时真是太没道理了,凭什么踢人家一脚?也许丁书记不记得了,也许他偶尔还会想起,但是他大人不记小人过……黄进步对自己二十年前的举动十分后悔,要是知道今天,他宁愿让丁新昌踢一百脚。
“丁……”黄进步刚刚说出一个字,丁新昌书房里的电话响了,他做了个打断的手势,就走进书房接电话。
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一脚,黄进步感觉到愧疚、有罪,简直有眼不识泰山、简直罪恶滔天,他心里慌乱不安,觉得自己这支臭脚真是应该烂掉了,恨不得把它立即砍断。
丁新昌接完电话走了出来,说:“不好意思,下面一个镇长要来谈点工作。”
这就是辞客令了。黄进步站起身,伸出双手握住丁新昌的手,声音突然变得有些颤抖地说:“丁书记,对、对不起……”
“怎么这么说?应该是我对不起你们。”丁新昌说,“下次再来坐吧。”
“下次……”黄进步咽了口水,把后面的话也咽了下去。
回到车上,黄小琼不解地瞟了黄进步一眼,说:“你怎么了?”黄进步像发烧似地喘了口气,摇摇头说:“没什么。”他发动了汽车,这才感觉到口袋里有一只红包,忘记送了出去。尽管丁书记从不收他的红包和礼品,他还是准备了一只3800元的红包。
这个晚上,黄进步一直睡不着觉,心里非常后悔二十年前踢了丁新昌一脚,不知怎样才能将功赎罪。
20、庞婉青
庞婉青走进办公室,感觉到一股霉味有点呛人,连忙把窗户全打开。上周五她就没来上班,接着是周末,周日上午她到了厦门,今天中午才回马铺,算起来有四天没来办公室了,门窗紧闭的,空气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她的心情也同样不好。
那是星期六晚上,她从“七匹马大排档”吃了晚饭回家,已经快十点了。她打开电视,看了会儿“超级女声”,心如止水,好像在看一群人耍着猴戏。电话来了,家里的固定电话响起彩铃,一看来电显示,是在厦门的老公打来的。她不想接。老公肯定是有事才会打电话的,她要让他在电话那头焦急。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老公,早已有名无实。开头是她不愿意离,现在是他不想离,两个人就这样耗着熬着。她对他也恩尽义绝了。只是他们有个11岁的儿子,被他送进厦门一家全封闭全寄宿的贵族学校,成为他们之间绝无仅有的最后纽带。那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唱了一遍,歇了一下,又唱了起来。这首歌是她百听不厌的,所以才会选来当作彩铃,再听一遍也无妨。她的手机号码换过了,老公不知道,所以他只能一遍一遍地打家里的电话。那天晚上,她在听了五六遍的彩铃歌曲之后,终于有点听烦了,这才接起电话。
老公说,儿子学校来电话了,傍晚时他把脚脖子扭伤了,儿子一直哭,跟老师请假两天,老师同意了,让家长明天上午来接。老公的表述很简捷,庞婉青听了之后也没有明显的反应,儿子虽然是她生的,但她从小就很少带他,又好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母子间的感情变得很生份。老公说,我明天早上的航班飞深圳,你过来接他回家。她本想说,我没空。但老公把电话挂掉了。
睡觉前她怕睡过了头,调了手机闹钟。6点整,闹钟刚一响起,她就从床上爬起来,把自己收拾一下,再准备一些行李物品,到外面店里吃了早点,就坐三轮车赶往车站,正好赶上开往厦门的早班车。
庞婉青从厦门松柏车站打的来到儿子的学校,办了手续将他接了出来。第一眼看到几个月没见面的儿子,感觉他差不多长到自己的腰带一样高了,她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但是儿子对她很冷淡,只是问,你怎么来了,我老爸呢?
她说,他没空。她想把儿子揽过来一下,然而他的手把她推开了,她的心一下就凉了。
坐的士回家时,儿子不愿和她坐在后排,抢先坐到了前排。老公家在前埔小区的一套楼中楼,从法律上说,这也是她的家,但她对这个家是陌生的,甚至是排斥的,她感觉像一个意外闯入者一样唐突。回到家里,儿子走进自己的卧室,就把门关上了。看他走路的样子,扭伤的脚一点也不严重,她猜想他可能是受不了学校严格的规章制度,找个借口回家玩几天的。他根本不想理她,她也对他无话可说。儿子虽然是儿子,但是情感的隔阂,他们和陌生路人毫无二致。家里有个保姆,是老公家的什么远房亲戚,买菜、做饭、拖地板、洗衣服,全套家务都包了。庞婉青在家里也没事干,就独自出门到南普陀烧了一柱香,又到鼓浪屿走了几条老街,在中山路吃了肯得基才回家。刚离开肯得基时,她想给儿子带条鸡腿或别的什么,但只是想一下就打消了念头。回到家里,保姆在洗衣服,儿子在房间里上网,一听到她回家的声音,就把房门关上了。她也懒得理他,就走进自己的房间。这家里到底有一间属于她的房间,平时没人住,只是她偶尔来,住一二个晚上。她躺在床上,找了一本过期的《读者》看了几篇,就睡了过去。第二天,她想走了,回马铺上班,虽然她在马铺电信局很自由,不高兴的话几天不上班,连局长也不敢管她,但她还是想走了。她听保姆说,老公下午一点多的航班回到厦门,她不愿意和他碰面,更是应该走了。走之前,她还是希望和儿子说几句话,她没想到儿子定定地看她一眼,便扭过头去,从嘴里飘出了一句话:听老爸说,你是个坏女人。这句话石破天惊,不过庞婉青没有晕倒,她努力地挤出笑容,对儿子笑了一下。
庞婉青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朱局长走了进来。这个肥头大脸的朱局长叫作朱高生,被她改作谐音的“猪哥生”。猪哥是马铺话,意谓种猪。几年前朱局长带她到外地开会,晚上赖在她的房间里不走,借着酒兴就来抱她啃她,见硬的不行,还跪下来求她,她就施舍一样让他上了一回床。从此,他就像被她捏住了七寸似的,不仅给她安排了个人办公室,委以重任,对她迟到早退旷工之类的事情一律不敢过问。
“你上午到哪去了,不是睡懒觉吧?”朱局长笑咪咪地说。
庞婉青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不想搭理他。
“我打你电话,没人接,打你手机说是关机,中午到你家门口去敲门,又敲不开,我差点都想报110了。”朱局长走到庞婉青面前,歪着头看了一下她的表情,生怕她不高兴,努力显出和颜悦色地说。
“到厦门,刚回来。”庞婉青懒洋洋地说。
朱局长哦了一声,让庞婉青从单位小金库取二万现金出来,他要用。庞婉青把保险柜的钥匙放在桌上,让他自己取。朱局长把两叠百元钞票塞进提包里,想伸手摸一下庞婉青的脸,见她把脸扭了开来,就讪笑着走了。
庞婉青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打开电脑上了QQ,一下就看到“坏蛋“的头像在晃动。那是他给自己留的言:“亲爱滴狐狸,你在做啥米?我在想你,你也在想我吗?上班忙,老板又要派我去温州。可能不能上网和你聊天,我有空会发短信给你。昨晚我托一只蚊子去找你,让它告诉你我很想你,并请它替我亲亲你,因为现在我无法接近你!它会告诉你我多想你!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大包代表我的心!”
线上还有几个好友,有一个网名叫作“帅得惊动国务院”的,也曾经对她穷追猛打,公开要求一夜情,她认识“坏蛋”之后就不大理他了,现在她甚至提不起聊天的兴趣,随即下了QQ,打开一个音乐网站,点了一首歌《两只蝴蝶》。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跃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跃这红尘永相随,等到秋风尽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