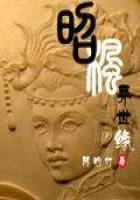晚上的这餐饭属于家庭聚餐,严舸请客,在市里的一家高档酒店。
经过这顿饭,池芸和严舸的关系正式得到金良琴的首肯。
饭后,三人去地下停车场取车。金良琴是自己开车过来的,晚上约了小姐妹喝茶,池芸则坐严舸的车。
严舸睡在外面酒店,金良琴向来对女儿放羊式管理,池芸来去自由,分手之前,金良琴问池芸今晚上回不回家睡。池芸是告假出来的,打算事情一完就回新泽,明天一早回去,下午就要上班,按理和严舸一起住在酒店最方便,但池芸想到,和母亲之间一年来无多少时日相处,于是说今晚上还和昨天一样在家睡。金良琴心满意足地开车走了。
目送金良琴的车离开,这一对才慢悠悠上车。
打开车门正要进去,池芸忽而定住了。
前方走过来几个人,男人女人还有小孩。
男人穿着黑色休闲装,是张陌生脸孔,走在最前面。女人穿一条连衣裙,侧低着头,前额一绺发垂下,半遮住侧脸,手里抓着一个咿呀咿呀蹒跚学步的小男孩,不经意的一抬头,也看见了池芸,当即一愣。
久未谋面的故人,不禁想起年少时种种,要说放下真的很难。
“孔丽丽。”池芸到底还是打了招呼。
孔丽丽也朝她笑了笑,脸上有初为人母的幸福感。池芸注意到她的目光在严舸身上停留了一下,大概听闻小船回来的消息了吧,毕竟是那么轰动的事,过去的朋友同学没有几个不知道的。
不咸不淡地聊了两句,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告别。
孔丽丽的老公站在前面几步远等她,交谈声传过来。
“熟人?”
“嗯,以前的同学。”
“初中还是高中?怎么没听你提过?”
“你问那么详细干嘛……狐狸精有什么好说的……”
声音逐渐远去。
池芸拉开车门,看了眼严舸,“走吧。”
坐在车里,外面明亮的灯光恍的眼疼,眼眶干涩,闭了闭眼,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池蒙的脸来,可怜兮兮地扒住她的胳膊,“姐,你不疼我谁疼我。”
“我不是还有姐姐嘛。”
“姐,以后谁欺负你我就揍谁。”
“姐……”
“姐……”
蒙蒙……
真的很想他。
池芸感到心口泛疼。
严舸开了轻音乐,轻缓柔和的乐声,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抚摸她,情绪一点点趋于平和。
时近八点半,再过半个小时九点。
严舸一手扶着方向盘状似漫不经心看池芸一眼,“先去我那里怎么样?”
池芸愣了一下,“这么晚,去你那里干嘛?”
严舸目光笔直看着路前方,半点没有商量的意思,“十点之前送你回家。”
池芸看向严舸,不吭声。
严舸趁转向时侧头看过来,“不想去我就直接送你回家。”
池芸动了一下,调整坐姿,“那就去吧。”淡淡的,听不出情绪。
刷房卡进门,池芸换掉高跟鞋,穿上更为舒服的拖鞋,看到床头柜上搁着一本书,靠在沙发上看。
严舸靠上来,从后面圈住池芸,下巴搁在她的肩上。池芸顺势往他怀里靠进去,手指翻页,到他标注的地方,看了眼页码,问,“你看到这里吧?”严舸把人抱到腿上,从池芸手里抽出书本放到一边去,“我们抽个时间去看看蒙蒙吧。”
池芸看着他,半晌没有回应。
她被怔住了。
他总是能轻而易举猜中她的心事。
池芸凑上去亲了亲他的唇,“本来我想等过段时间跟你说的。”
她没有勇气说出的话,他替她说了。
“你上回说等庭审结束要我答应你一个要求,是这个吗?”严舸手习惯性地贴在她背上,隔着薄薄的衣料揉着。
“嗯。”池芸抓着他的手,从膝盖上滑下去,坐到对面床上去。
严舸坐在沙发上,保持着坐姿,看着她。
池芸这才静下来,也看着他,“你去的话,他一定会惊讶,但是我希望你去,我希望得到他的祝福。”
严舸没说话。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池芸依旧很平静。
严舸看到女人黑色的瞳孔有光在闪烁,心里一动。
严舸笑了,有些宠溺,又有些无奈,“拿六个喜欢来换?”
“我把你对我的爱都赌上了。”女人眨了眨眼睛,颇有些调皮道,“我知道你会同意的,这是我们的约定。”
很早很早以前她就知道了的。
在她确定喜欢上小船的那一刻,她就决定了——
在徘徊、犹豫之后,要做一个挥舞长剑的勇士。
她向来说话算话。恰好,他也是。
池芸看见男人眼睛微弯,深刻的目光满含柔情。
“你又赢了。”他短促一笑,走过去环住池芸的腰身,将女人柔软的身体揉进怀里,“今天晚上留在这里过夜好不好?”
他看着她,等待答复。
池芸到底没有遂男人的愿,主要是今天真的没心情,严舸也没有强留她的意思,两人聊了一会儿天,安排好第二日的行程,严舸便将她送回家去。
原本计划好的行程,在前一天晚上有了变动。
回新泽之前,池芸和严舸去了一趟槐乡。
在四月某个适宜乔迁的日子里二姨和二姨夫两口子搬去了镇上。
这个他们最初相遇的地方,承载着许许多多共同回忆的地方,以后也难有机会再回来,他们是来告别的。
离开许久的地方,再回来,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
杀猪家的也早搬走了,大门紧闭,门上挂着一幅褪了色的对联,风一吹,摇摇欲坠,石榴树长的老高,火红的石榴花从墙头斜伸出来。
离开,转去山上。
时下正午,烈日当空。
前一天下过一场雨,山路泥泞,湿度很高,加之草木茂密,别有一番凉爽。
因知要来山上,池芸特地穿了运动鞋,饶是这样,走起路来仍有些磕绊。
这条路没有经过开采,羊肠小道,坑洼不齐,有些地方已被杂草掩盖,严舸走在前面开道,时不时停下回头搭一把后面的池芸。
大抵许久没有运动,才走几步池芸便气喘吁吁,倒是并不赶路,索性停下来休息,看看风景聊聊天。
池芸找了一处阴凉,拿严舸那顶鸭舌帽站着扇风。
不远处传来的歌声的变得更加清晰动听。
是茶山上传来的。
小满刚过,正是旱季茶的采摘时令。
从这处抬眼望上去,约莫能看清对面的茶山,绿油油的一片,很多人忙碌着,蚂蚁似的一点点。茶叶是槐乡的特色产业之一,每到三月中旬,茶山上便忙碌起来,所谓的明前茶就是指这个时节采制的茶叶,也就是“惊蛰”这一天开始。在槐乡,采茶制茶是一门手艺,早年前,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着一个火灶,灶上一口大锅,那锅子就是用来炒茶叶的,每当炒茶那便热闹了,小孩子们最开心,抓一把刚炒好的茶叶往嘴里塞,一时之间满口都是暖融的茶香味。这样的景况现在已经不再有了,谁也回不到那个饿到去抓一把茶叶吃的年代了。
池芸以前也跟过二姨上茶山采过茶叶,背着一个小竹篓,走很多路去茶山上,很奇怪的是,那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甚至觉得新奇好玩,学着大人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摘起来,时隔多年,即使早已忘记茶叶怎么摘了,那份快乐却永远留在了心间。
槐乡浓厚淳朴的乡风是池芸喜欢的,也是教她永难忘怀的原因。
山上下来一个砍柴的老人,池芸认出他是住在祠堂口的阿公,和严舸两人叫“阿公好”。
阿公记性很好,还记得池芸,叫她“老夏家那对双胞胎”。老人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快八十岁了。
当年,池芸和小船可谓一段“佳话”,几乎到了村里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最主要原因是两人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古语说“门不当户不对”,很多人都不看好,没想到时过境迁两人仍然在一起,阿公向他们竖大拇指,又说小船叔婶真不是东西,为钱不要命,以前卖猪肉的时候就知道,那肉里一大半是水,背地里对他有意见的人多了去,又问他们吃过饭没有,没吃的话去他们家里吃个便饭。
阿公的好意领了,饭自然是不会真去吃。离开之前,阿公说下山去他们家坐坐,两人忙不迭答应说好。
严舸父母的墓离池芸外婆的很近,她以前倒是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领她去。
池芸想起来,问,“清明节你来槐乡专程来给你爸妈扫墓的吧?”
严舸低头清理墓前新长出来的杂草,“顺便看一下我自己的墓。”
池芸没说话了,蹲在他身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翻涌,虽然已经查出那墓里真正的主人,严舸也请人专门做了碑替换掉了原先那块,在那墓前重重磕了三个头,说了三声对不起,可是……
那隔阂像一条沟裂刻进他的心里了吧,池芸想,无论对严舸亦或是墓里那个顶替了他七年的人,都是一场惨剧。
无论做什么都挽回不了的惨剧,只能尽力弥补。
唯有尽力二字,好像才能让自己的良心舒服一点吧。
他们在父母的墓碑前拜了三拜,严舸说,“爸、妈,这是芸芸,今天我带她来是为了告诉你们——”说到这里,严舸的手抓住池芸放在膝口的手,池芸侧过头,朝他抿了抿唇,极浅的一笑。
“我准备跟她求婚。”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戒指盒,单膝跪地,打开,璀璨的钻戒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望着她的眸光里满是柔情。
他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七年,接下去的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想和你呆在一起,哪怕只是虚度光阴,嫁给我好吗,芸芸?”
这是她全没有料到的,荒草萋萋,树荫繁茂,抬头,阳光正南,在他们最初的相遇的地点,视线模糊,眼前忽然闪现那年,少年抬起头,目光穿过层层叠障的绿,“正午了。”
“咦?你怎么知道的?”
少年回过头。
“看太阳就知道了,正午的太阳在正南方。”
而现在,这个男人单膝跪地在池芸面前,希望她嫁给他。有一种时空交错,恍然如梦境的错觉。
她曾在《眠于半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不是“彼此有多相爱”,而是“彼此早已经习惯了对方”。原来,我爱的样子他都有,我有点样子他都爱,我真希望,他陪我长大,我陪他变老。可是,我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另一半,夭折了。
池芸唇角微微抬高,她似乎比她的主人公顾眠要幸福,顾眠没有实现的那一半愿望,池芸在现实生活中等到了。
她伸出手去,去抓她的梦;她点头,说“我愿意”;她害怕这只是一场梦,就像很多年来一样,梦醒了,什么都留不住。
严舸难掩内心激动,套上女人纤细手指上的戒指微微抖动,但终于还是紧紧套住,连同她整个人都是。
故事到这里,她的愿望全部实现。捎上顾眠的那份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