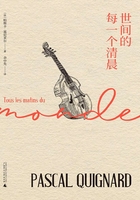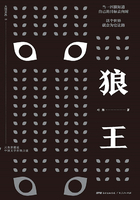项海犹豫了一下,说:“我岂止爱听——我唱了几十年的戏。”
这一聊,便是半年之久,每隔几天都要聊上几句。项海觉得这也是缘份,他叫“杜丽娘”,偏偏就有人叫“柳梦梅”。都说网络乱糟糟的很,没想到居然能遇到一个谈得来的人,真是很难得了。
今天,项海告诉“柳梦梅”:“我喜欢上我家隔壁的一个女人。”说完,心砰砰乱跳,脸都有些红了。“现在,你该晓得了,我是个男人。”
“柳梦梅”停顿了一会儿,问他:“那女人也喜欢听戏吗?”
项海说:“这个我不晓得,但她前夫是京剧演员,耳濡目染,想来她应该也不会讨厌。”
“柳梦梅”道:“那很好啊。你去跟她说。”
项海愣了愣,半晌,才道:“这个,你让我怎么说呢。”
打完这行字,项海便下线了。心兀自跳个不停,盯着电脑屏幕,都有些后悔说这些了。原以为说出来,心里会轻松些。谁晓得反倒更彷徨了。
项忆君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
“你好,我是毛安。”一个男人的声音。
项忆君先是一怔,随即才反应过来。“哦,你好,”想起那天的失态,微微有些局促,“你——找我有事吗?”
“我想跟你学唱戏。”
“什么?”项忆君还当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想跟你学唱戏。”毛安提高音量,又说了一遍。
下班后,两人约在咖啡馆见面。项忆君进去时,毛安已等在那里了。分别点了咖啡。毛安直奔主题:
“我说要向你学戏,可不是开玩笑。我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看着她。
项忆君觉得很好笑。“我自己也是半桶水,哪里会教人啊。我们院子里有许多专业演员,我介绍几个给你认识好不好?”
毛安摇头道:“不用很专业,我又不指望上台表演——我要求不高,只要像那么回事就行了。”项忆君朝他看看,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要学戏?”
毛安拿起咖啡喝了一口,笑笑,说:
“也不为什么,说出来你肯定会笑我的。不过你现在成我师傅了,被你笑两句也没关系——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讲的那个余霏霏吗?嘿,我不用说下去,你也猜出来了,是吧?”他摸摸头,咧嘴一笑,似有些不好意思。
项忆君一愣,随即“哦”了一声,明白了。朝他看了一眼,笑道:
“你这人倒蛮有趣的。”
“不是有趣,是认真,做事认真,”毛安强调道,“我这人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准备工作做足,不打没把握的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争取一击即中。”他越说越兴奋。
项忆君忍不住又笑了。
“你把追女孩当成打仗啊?”她道。她本来是想拒绝他的,现在一下子改了主意,像是马上要投入到一场游戏中去的心情,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有些新奇,又有些跃跃欲试。她眼珠一转,问他:
“那个余霏霏,是不是很漂亮?”
毛安不加犹豫地说:“那当然!”
项忆君下班回到家,看到楼下停着一辆白色的本田雅阁。她认出这是白文礼的车。她上楼,开门进去,果然见到白文礼坐在沙发上,穿一套休闲西装,手拿茶杯,笑吟吟地在和项海聊天。项忆君叫了声:“白叔叔。”
“忆君回来啦?”白文礼笑道,“几个月不见,越长越漂亮了。”
不久前,白文礼筹办了个戏曲学校,生源不错。这次他过来,便是想请项海出山,到学校教戏。
项海推辞了。“这么多年不唱,都生疏了。”
白文礼一笑。
“师兄啊,这话搪塞别人可以,搪塞我可就不行了——说句实话,除了你,我谁都信不过。要是能请到你,我这个学校啊,就有九成把握了。”
项海摇摇头,淡淡地道:“师弟这是抬举我了。我现在不过是个糟老头子,什么也不懂。你让我去教学生,可别砸了你的金字招牌。”
白文礼微微一笑,说:“师兄又何必太谦?你啊,就是亏在退得太早,要不然唱到现在,谁还能强得过你——就当给我个面子,一来是为了我,二来也是为了那些学生,发扬国粹,功在千秋的事,啊?”
项海嘿了一声,不说话了。
项海留白文礼吃晚饭,白文礼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又说要进厨房帮忙,被项海推了出来。白文礼便踱到项忆君房间,见她正在翻一本厚厚的《京剧大戏考》,奇道:“怎么想起看这个了?”
项忆君告诉他:“不是我要看——是有人要向我学戏,我在备课呢。”
白文礼笑了。“倒是蛮巧,我请你爸爸教课,别人又跟你学戏——父女俩都成老师了。”
项忆君摇头笑道:“我算什么老师啊,只不过是闹着玩儿。那个学生动机也不纯,嘿,你晓得他为什么要学戏——”说到这里,忽的想起一事,便问:“白叔叔,向你打听个人——余霏霏你认识吗?”
白文礼愣了愣。“哦,认识的——去年刚分到团里,程派旦角——怎么,你认识她?”
项忆君一笑:“我不认识,不过我的徒弟认识。”
吃完饭,又坐了一会儿,白文礼起身告辞。项海说要送他,白文礼忙道不用。项海便让项忆君代他送到楼下。两人缓缓走下楼梯。项忆君走在前面,白文礼走在后面,停了停,忽的说了句:
“你走路的样子真像你妈。”
项忆君回头一怔。“像吗?”
“像。”白文礼看着她,道,“不光走路的样子像,长相也很像呢。”
项忆君笑笑,道:“我舅舅也这么说,不过他说,我没有妈妈好看。我妈妈是鹅蛋脸,鼻子很挺。我鼻子塌塌的,像个洋葱。”
白文礼也一笑。“你比你妈还要文静些——放在戏台上,她是花旦的路子,你就是青衣。”
项海打开电脑。“柳梦梅”也在网上。
“吃过饭了吗?”“柳梦梅”问。
项海说:“刚吃完——今天,我师弟来了。”
“柳梦梅”说:“是一起学戏的师弟吗?他唱的好,还是你唱的好?”
项海说:“这个不好说。不过,以今时今日的境遇来看,他比我要好的多。我和他是两种人——我只是个戏子。他却是个人物。”
项海打到这里,停了停,又接下去道:“这番话,我从没和别人说过——我没有半点贬他的意思,只是有些感慨。”
“柳梦梅”说:“我明白的。”
项海怔怔地看着屏幕上这四个字,一时间竟不知该再说些什么。心头倒是积得满满的,万感交集的,想不出合适的话,便道:
“‘柳梦梅’,你喜欢现在这个世界吗?”
“柳梦梅”说:“喜欢不喜欢,都要在这个世界过。难道你有时空穿梭机?”
项海想了想,道:“我不用时空穿梭机——窗帘一拉,戏服一穿,眼睛一闭,就变成另一个世界啦。”他说到这里不禁一笑,是笑自己傻的意思。摇了摇头。
“隔壁那个女人,你和她说了没有?”“柳梦梅”忽然问道。
项海一愣,反问:“说什么?”
“柳梦梅”道:“当然是坦露心迹了。”
项海迟疑着,没吭声。半晌才道:“我要去睡了。下次再聊吧。”匆匆下了线。呆呆坐了片刻,便踱到阳台上,抬头望天上的星。头一侧,瞥见隔壁阳台上有个人影,借着月光,一看,竟是罗曼娟。两人目光一接,都是一怔。
“还没睡啊?”项海干咳一声,问道。
罗曼娟“嗯”了一声。一甩手,将刚洗完的羊毛衫挂在衣架上。
“晚上晾衣服,不怕沾了露水吗?”项海又问。
罗曼娟道:“羊毛衫干得慢,放到明天再晾,一整天干不了。”
项海哦了一声。一时找不到话接下去,便依然抬起头,两手撑在栏杆上,看天上的星——其实是在想话题。又怕她晾完衣服便要进去,心里忐忐忑忑,脸上却是带着微笑,悠悠闲闲的。
“项老师今早又唱戏了吧。”罗曼娟忽道。
项海说:“嗯——吵了你睡觉是吧?”
“没有,”罗曼娟道,“我早醒了——就算没醒,在这样好听的声音中醒来,也是件美事呢。”她一边说,一边整理着羊毛衫。
项海心里一动,想再说些什么,罗曼娟已转身进屋了。“再会。”——她是苏州人,这声“再会”甜中带糯,听着说不出的惬意。
“再会。”项海看着她背影,一时间,胸中有东西在涌动,一波一波的,又似被什么撩了一下,浑身轻轻打个激灵,思路都有些跟不上了。
(三)
项忆君把授课地点定在她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周六周日,学校的操场上到处可见打球的学生,教室里却几乎空无一人。项忆君挑了底楼的一间教室。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京剧的起源,”第一堂课,项忆君说,“京剧的前身是徽剧和汉调。清朝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与汉调的艺人合作,又吸收了昆曲、秦腔的曲调和表演方法,渐渐就发展成了京剧——”
毛安道:“老师,能不能不学那些理论知识,直接教我唱戏?”
项忆君问:“你想学哪段?”
毛安嘿了一声,说:“我不懂的,反正只要好听就行,再有就是别太难,你晓得,我一点基础也没有。”
项忆君想了想,说:“那就学《苏三起解》吧。”
毛安说:“这个我会唱。”说着,便抢在前头唱了一遍。唱完,朝项忆君看了一眼,笑笑,“我晓得我唱得不好,你别这么看我,我会自卑的。”
项忆君摇了摇头,道:“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你运气的方法不对,应该用丹田运气,那样唱出来的音才浑厚,你这么唱,就像唱流行歌曲似的,轻飘飘的。”
毛安问:“丹田在哪里?怎么用丹田运气?”
项忆君说:“丹田就是小肚子,你试着深吸一口气,把气从那里升上来,喏,就是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小肚子,深深吸了口气,又吐出来,“感觉到没有?平常你是用肺呼吸,现在是用丹田呼吸。唱戏时一定要用丹田的气。”
毛安学她的样子,呼吸了一遍。
“项老师,”他笑着道,“我记得以前生物课老师说过,人是用肺呼吸的。我实在想不通——小肚子里只有大肠和盲肠,怎么个呼吸法?你倒是说说看。”
项忆君愕然,倒不晓得说什么好了。她想起自己从前跟父亲学戏的情景,是何等的屏息凝神,连喷嚏也不敢打一个。现在这个人,居然嘻皮笑脸,浑然不当回事。项忆君觉得,学戏不该是这个样子。她有些不快,朝他看了一眼。转念又想,反正他也是闹着玩儿的,自己又何必太认真。
“那你还是继续拿肺呼吸吧。”项忆君淡淡地说,“《苏三起解》你已经会唱了,我们再学段别的,嗯,《智取威虎山》好了。”
白文礼专门派车去接项海上课。司机按门铃时,项海刚刚熨完衣服。他原先预备穿中山装,已经拿出来熨好了。谁知穿上后才发现,袖口那里居然有个洞,也不知什么时候破的。只得另拿一套西装。急急地熨了。穿上,随司机走下楼。他站在一旁,等司机开门。谁晓得司机自顾自地上了车。项海一愣,想这人真是不懂规矩,只得自己开门,上了车。
学校大楼新建不久,教室里的玻璃窗和课桌椅都是崭新的。项海走进去,见下面坐了五六成学生。一个个眨巴着眼睛朝自己看。项海暗暗提了口气,竟也有些紧张。“大家好,”他道,“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姓项名海,现在开始上课。”
项海教授《霸王别姬》。他先唱一遍: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恨只恨无道秦把生灵涂炭,只害得众百姓困苦颠连——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适听得众兵丁闲谈议论,口声声露出那离散之心——”
项海许久没在公众场合唱戏了,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他唱完,朝台下看去。见这些学生一个个表情木木的,毫无反应。项海正有些失落,忽听见角落里响起欢快的手机铃声,一个女学生拿着手机,飞也似的奔了出去,一会儿再进来,大喇喇地坐回位子。招呼也不打。项海被她的高跟皮鞋声弄得好一阵发愣。
第一堂课上得索然无味。手机声此起彼伏。听电话的,上厕所的,进出教室旁若无人。后排一个男生边听课边吃口香糖,手插在口袋里,靠着椅背,对着项海叭嗒叭嗒嘴巴灵活地翻转着。前排的一个女生,赫然在项海眼皮底下看一本画报,翻页时毫不避忌,弄出哗啦哗啦的声音。项海对着她发了一会儿呆,还没想好该说什么,女生却抬起头看他,还朝他笑了笑,继而又低头看画报。
项海没说话,心里却有些糊涂——难不成现在学生上课都是这个样子?几十年没进课堂,都变得让人看不懂了。
上完课,项海微一欠身,朝台下道:“今天就到这儿吧。”说着慢慢地收拾东西。他静若处子,学生们却是动若脱兔,只一会功夫,便走个干干净净——只留下项海一人。教室内顿时空空荡荡。
司机告诉项海,车坏了,不能送他回去。“你坐校车吧,到人民广场。喏,就在那边——”司机叼着烟,手朝校门口一指。
项海只得走过去,上了大巴。车上座位已满了。零零星星有几个人站着——坐着的都是些学生,说说笑笑,有些是刚才班上的学生,见到项海,也不理会。项海挑了个位置站着,一手拿包,一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一会儿车开了,起步时不大稳,项海没抓牢,整个人朝后倒去,“啊哟!”幸好后面有人,扶住了他。
“谢谢。”项海重新抓住行李架。这次抓得牢牢的。
“项老师,我帮你拿包吧。”旁边座位上一人道。项海一看,见是刚才上课时吃口香糖的男生。男生一抬臀,再一伸手,将他的包拿了过来。
“这趟校车人最多了,每天都有人站着——项老师你累不累?”男生嘴里嚼着口香糖,问他。
“嗯,还好。”项海听他这么说,还当他会给自己让座,谁知他纹丝不动,并没有让座的意思。便有些后悔,该说“很累”才是。再一想,整车的学生只有他一人提出给自己拿包,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仗义了,不该再奢求什么。
好在路上不堵,不到半小时便到了人民广场。项海从男生手里拿过包,说声“谢谢”,下了车。换乘一辆地铁,很快到了家。
项海走进门洞,被迎面冲下来的一人撞得险些跌倒,他踉踉跄跄看去,那人已冲出十来米之外。“小赤佬,你给我死回来——”与此同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尖叫声,在项海头顶响起。项海抬起头,五楼的女人见到他,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项老师,这个——回来啦?”忙不迭地把头缩回去。
这女人以前唱裘派,是京剧团里唯一的女花脸,一度前途远大,后来跟着老公炒期货,心思全放在赚钱上,把家当输个精光才回头。几年不唱戏,全撂下了。现在拿着一份死工资,日子清苦得很。项海猜想,她儿子刚刚必定又是拿了家里的钱去赌,她才会如此失态。不由得叹了口气,慢慢地走上楼。
“项老师。”忽听见一个轻轻柔柔的声音。
项海抬头,见罗曼娟站在面前,手里端着一碗馄饨,正望着自己。“自己包的馄饨,虾仁馅的,拿一碗给您尝尝。”
项海“哟”的一声,连忙放下包,双手接过。“这怎么好意思——多谢多谢。”他正要开门,才发现自己端着馄饨,竟腾不出手拿钥匙。罗曼娟微微一笑,又从他手里拿过馄饨,“您先开门吧。”
项海也笑了笑,掩饰脸上的窘态。打开门,“进来坐会儿,”他对罗曼娟道,“我昨天刚买了些上好的普洱,请进来尝尝。”
罗曼娟推辞道:“不了。家里的衣服还没收,小囡马上就放学了,还要烧饭。”
项海“哦”了一声,兀自不死心,道:“只是喝杯茶,耽误不了多少功夫的。”说完朝她看。又觉得自己死缠烂打,有些过头了。正踌躇间,听见罗曼娟道:
“这个——好吧。”
项海泡了杯酽酽的普洱茶,端过来。罗曼娟坐着,在看旁边镜框里的照片。有项海父女的合照,还有早年项海在舞台上的戏照。
“项老师这几年都没怎么变呢,保养得真好,”罗曼娟道。
“哪里,”项海笑笑,“老了,脸上的褶子拿熨斗也熨不平了——来,请喝茶。”
罗曼娟接过,放在一边。朝项海看了一眼,停了停,忽道:“项老师,我们家小伟昨天在学校里闯祸了。”说完眼圈一红,几乎要落下泪来。
项海见她这副模样,先是一惊,随即问道:“怎么了?”
罗曼娟说:“他和同学打架,把同学的头打开了,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校长对我说,要给小伟记一次大过。我晓得记三次大过就要退学。项老师你说,这可怎么得了——”急得又要哭。
项海劝慰她道:“小孩子打架,也是难免的事——男孩子嘛,自然调皮些。再大几岁就好了,你不用担心。”
罗曼娟摇头,道:“项老师你不知道,这个小囡啊,我当妈的心里最清楚,要是不好好管教,将来就跟五楼上那个宝贝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