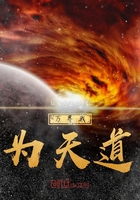让大爷我死个痛快,一箭射死我,倒是清净,门外一小厮怒喊道。
胤禛听了走出客栈,外面火把将黑夜照的通亮,官兵齐齐下跪,异口同声道,给王爷十阿哥请安。
那小厮嘴角微扬,冷笑道:“临死了还能见到狗皇帝的儿子,倒也痛快,爷不怕死,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另外三人则都弓着背,一言不发。生是怕受了连累。
胤禛伸出手,对身旁的官差冷声道:“弓箭拿来。
那官差将弓箭递给了胤禛,又后退几步。
心想原本是县太爷吩咐,里面倘若人稍作反抗,乱剑射死,这下情况却天翻地覆,完全调换了局势,那县太爷更是弓着身子随在后面,大气都没敢喘一下。
胤禛拉着弓,眼里的寒气更重。
那本王就成全你,说着箭一出弓,直射到那小厮,一箭毙命。
只看那小厮头顶顷刻被穿透,嘴巴大张,死相极其难看。
锦绣跑过来,扶着脸色吓的惨白的淮七,淮七则紧紧的抓住锦绣的手,锦绣轻声安慰道:“二小姐别怕,奴婢在这儿呢,也别往那边看,回头生噩梦。”
张赫德之后一直跪在客栈,胤禛摆了摆手,你回去吧。
张赫德如获大赦一般,谢王爷哥,十阿哥不杀恩。
你又没错,为何杀你,胤禛淡漠道。
张赫德走后,客栈也恢复了平静,大堂里不出一声,屏息凝视着这一行皇室贵胄,不敢直视,只是偷望。
到了房里,胤禛差人送来了干净的衣裳,刚才溅了一身的血,胤禛又极其爱干净,回房即刻换下了衣服。
和淮七也没有交谈,独自洗过澡,带着一身的湿气走了出来。
淮七坐在床上,胤禛想要去抱她,却看她冷不防的避开。别过身子。
在和本王生气?胤禛问道。
淮七不语。
两人僵持了半天,房里陷入了一片死寂,胤禛终于忍不住沉默,再次开口问淮七说,到底是怎么了?
淮七仍不回话。
这下惹急了胤禛他捏着淮七的下巴,力道却没用几分,本王在和你说话,你这是什么态度。
淮七漠然道,大不了王爷也把我杀了?
胤禛听后松开了淮七,拿起案子上的空烛台,烛台上的铜尖直逼着她的脖子。
淮七这下真是怕了,看着胤禛的举动心里没了底气,哀莫大于心死,心想难道自己来到这儿,
就是为了让胤禛杀死?自己年纪轻轻的小命,倒死在了雍正的手上。是该庆幸这光荣的死法?还是悲凄这可怜的身世。
刚才的话是气话,她可没成心找死,但那胤禛好像全当真的听,自己倒是不争气的哭了出来。
胤禛扔掉了手上的空烛台,怕了?
怕死就别说死,况且本王怎么舍得杀你,未免把本王看的太寡情了。
胤禛叹声道:“本王怎么做你才能不怕?”
淮七摇了摇头,哀叹道,不知道,可能会一直怕下去,这样也好,省得犯什么大错。
胤禛将淮七圈在怀里,低下头吻住淮七,见淮七不去回应,硬是撬开了淮七的朱唇,两人的舌头纠缠在一起。之后顺势吻着她的耳垂,这样敏感的地方让她失了方寸,浑身开始战栗发麻,胤禛将手探入淮七的衣服里,揉搓着淮七早已经坚挺的浑圆,淮七知道胤禛已经有了欲望,底下的昂藏也在坚硬的搏动。
淮七将胤禛要伸入她下面的手拦了下来,王爷,妾身身子不方便。
胤禛这才想起淮七来了月事。
沙哑道:“本王忍不住了怎么办?”
妾身真的不方便,淮七保持着仅有的理智说。
胤禛将淮七的手放在了自己的昂藏上,虽然隔着裤子,也能感到那东西的火热。
那就想办法帮本王泻火,胤禛附在淮七耳边暧昧的说。
淮七对这种事儿还是害羞,她呆呆的望着胤禛,始终没有动作。
胤禛也不强求,将淮七的扣子一颗颗的扣好。
背过身子,独自睡去。
淮七看着胤禛,佩服他的自制力真不是一般的好,这种情况,还能把持的住,简直少有,都已经烧了身,如果换作别人,定会和野狼一样,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来了月事,这家伙竟然能安稳的睡去。
到了苏州,苏州知府元盛前几日听闻自己独子被雍亲王手刃的噩耗,病了好一阵才能下床,而今却还要毕恭毕敬的去迎接雍亲王和那十阿哥,一想到这儿元盛就欲哭无泪,心里恨不得剐了他们,面上还要笑脸相迎,简直是羞辱难当。
自己四十岁才有了这个香火,几代单传,平日里更是任凭他胡作非为,也舍不得呵斥,现在谁料确成了孤魂野鬼。
自己夫人到也是走不出丧子之痛,天天还要哭上个几回,哀叫着元贺死的不值。
想到这些,
觉得这样的杀子之愁,不能报也罢,还要继续当着奴才才是残忍。
卑职参见王爷,十阿哥,元盛强撑着笑脸说。
胤禛和十阿哥做到了太师椅上,胤禛抖了抖袍子上的灰,然后问元盛要来了水灾的地形图。
十阿哥看了一眼也不明白,装懂的说,这灾情不是很严重。
元盛看这十阿哥暗想,不愧外面传十阿哥愚笨,今儿还真证实了这件事儿,他遂罢也顺着说,是不太严重。
胤禛仔细斟酌了一番水患图,每一处都是细细观察。他放下了,图纸,皱着眉头训斥道,如果这叫不严重,那好像世间没有严重这一说了。
元盛和十阿哥互相对视一番,没有答话。
自打胤禛进来他就打量着这雍亲王好久,气度不凡暂且不论,就是他那浑身那种冷死人的架势,也觉得自己儿子是命不好,偏偏得罪了这主。
元夫人听闻杀自己儿子的仇人来到苏州府,一下子又激发了怒气,想要和他们去理论。
身旁的丫鬟拉着元夫人,劝到,夫人,来的可是皇子,如果您出去和他们理论,怕到时没准连累了老爷。
那我总该为贺儿出气,不能让他枉死,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元夫人正在气头上,此时也根本听不了一句劝。
这边后院闹的厉害,前院也是极度紧张。生怕答错一句话。
现在苏州府有多少个苦力,胤禛问道。
回王爷,二百余人。
疏通河岸,在征一千人,灾民情况怎么样?
元盛面露难色,王爷,灾民与日俱增,这才是首要之急,有的村子全村也都害了疫病。
胤禛听了眉头紧锁,村子大概有多少户人家?
三百余户,临河而居。
染了病的有多少?能不能别问上一句你答一句,自己该说什么就说,胤禛没了耐心,看着吞吞吐吐的苏州知府,脸色难看的要命。
元盛这回接话倒快,胤禛这一脸的不悦,愣是催着他甚至加快了说话的语速。
二百余户,早前派了几个郎中去,也都不济于事,那几个郎中倒也染上了疫病,卑职已经派人将那里隔开,只怕那村子的人家撑不了多久,拒属下说,村子周围已是臭气熏天,有的一家几口都没了命,尸首也就无人善后,也在没有敢进村的人,所以散发出阵阵臭气。
贴告示找能医此病的郎中,如果过些日子仍是没有起色,我像皇阿玛请旨放火烧了村子,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万不可以出此下策,能治活一个,就给本王治活一个,街上流窜的灾民,统一安置,在几处要道,开餐救济,城门给我守好了,别让灾民出了苏州城,胤禛吩咐道。
十阿哥感觉自己多余,插不上一句嘴,更是对灾情没有一点应对之策,连着喝了好几杯茶,在屋里来来回回的转着圈。
胤禛问十阿哥说,十弟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十阿哥挠了挠头,四哥已经吩咐的滴水不漏,十弟也觉得的说的有理,一切遵照四哥的意思去办。
紫禁城连着下了几天的雨,整个天也是灰沉沉的不见一点阳光,到处充满了潮气。
八阿哥和十四一边下着棋,一边说着这几日的天气,十四喝了一口茶,望着窗外的狂风暴雨,雨拍打在窗子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八哥,这雨下了有几日,也不见小。
十四弟,春雨虽然下的大了些,但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所谓春雨如油,来年的收成也定是很好。
这几年我大清旱灾涝灾严重,皇阿玛为此费劲了心思,这几日看他鬓上的白发添了很多。
八阿哥原本要下落的棋子停在半空中,等了一会,才落下棋子。
十四弟何时进的宫?
前几日皇阿玛宣我进宫下棋,输了他不下五盘,皇阿玛临走时还说我棋艺不精,让我回去多加练习,过几日在宣我对弈。
八阿哥表情骤变,问道,皇阿玛和你下棋时还说了什么?
十四完全没发觉八阿哥脸上的阴郁,仍是没有心机的说,无非是问我最近闲暇时读了什么书,对朝中一些事的看法,还赐了为弟几个书名,让我回去拜读,昨儿就差府里的下人,去买了回来。
八阿哥听了心头更是一紧,待十四因府里有事冒雨走后,八福晋和身边的丫鬟进来,丫鬟将杯中的凉茶端走,换了一杯热茶。
八福晋看八阿哥的心思不在那盘只剩一人的残局中,什么都没说,也随丫鬟退了出去。
八阿哥将手中的黑子落定,发现十四虽已人走,但确给自己留下盘死棋,无论自己怎么走,只有一个输字。
八阿哥面上带笑,将棋子一个个收入棋蒌之中
雍王府里,那拉氏算胤禛走了足有小半个月,好在府里最近也是相安无事,只不过年氏每日给自己请安的时辰越来越晚,总是有意无意的数落两句,却不敢深说,年氏在雍王府算的上是最受宠的一个,那拉氏虽是嫡福晋,对年氏仍是有所顾忌,这次胤禛去江南带上个平日不起眼的妾室,给年氏无疑是个打击,曾经胤禛连续三日在年氏房里过夜,让府里的女眷都瞋目结舌,年氏从那以后连走路都是傲慢做作,让李氏几人都红着眼,暗里骂她狐媚子,眼里透着股嫉妒。
年氏收拾好了行李,找到那拉氏,姐姐,妹妹要去江南。
那拉氏听了脸色一沉,年妹妹,你这不是为难姐姐,王爷临走时交待过,让我照顾好府里,你这一走,回头怕王爷回来责怪我疏忽,路上在出点什么意外,王爷一直心疼妹妹,姐姐真是担当不起。
姐姐大可放心,是王爷想妾身了,派人传话来,让妾身过去。
那拉氏一听知道年氏在扯谎,胤禛的性子她也摸的几分,根本不会做出此事,眼下年氏扯了这么大的谎,她要拦着,怕她回头在府里说自己阻止她去见王爷,到时候自己倒成了罪人,年氏在府里的确也是恃宠而骄,实在不招人喜欢,索性由了她去,一句妹妹路途遥远,好生照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