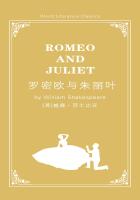孩子终于像一只出巢的鸟儿,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艰难地翱翔。
我和妻子相视而坐,开始忆起孩子的童年,整理那些早已忘却的玩具。布娃娃,小狗、机器人、四驱车以及各种儿童兵器……足足两大纸箱子。
我说,把这些东西送给人吧。
妻说留着吧,留着用过的东西就留着一种视觉的记忆。
我说,记忆这东西是一种滋味,就像糖果一样只有吃过它的人才保存着一种甜美,而不是保存了糖果就保留了记忆的味道。我小候虽没有这些洋玩意儿,有的只是弹弓、陀螺、铁环这些土玩具,而这些东西早已荡然无存,但留在心中的记忆永远愉悦着我的人生,尤其是在那些刮风下雨的日子里,取出一份记忆就像取来了一份阳光。
山里孩子的童年拙嫩,童年的玩具却拙朴美妙,有天然的,有自制的,有小不拉叽的,有大得几人高的。一个小土块就可以当作投掷的工具,看谁抛得最远;一棵大柳树就可以成为攀登架,看谁爬得又快又高;一块小石片掠过水面,谁的石子划过水面的次数多,谁就溅起的水漂多;一个掉在地上的竹棍就可以当作绕床弄青梅的竹马;一团泥巴就可以捏出所见所想的东西,还可以进行“摔响盆”比赛。摔响盆就是先将泥团捏成盆状,然后端在手上慢慢举过头顶,再用力摔到地上让盆口着地,里边的空气就会冲破盆底,发出“呯”抑或“叭”的爆炸声,谁的声音豁亮谁就是赢家。摔响盆是一个技术活,包含着泥的质量、盆的制作以及举起的高度、摔盆的力度等,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即便你掌握了这些要领,也未必就能摔出清脆的声响,就像阿Q与王胡赛虱子一样,虽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却怎么也不及王胡的响。因为,这里边有一种你无法言传身教的潜意识的东西,也许就是我们说的“习惯成自然”的那种感觉。习惯是一种滴水穿石的功效,是一种难以表述的势能,人一旦习惯了某种动作,就会有一种势能定性成你的行为,就像有人用左手捉筷子吃饭,一旦形成定势,就很难矫正过来。因此,有什么样的习惯元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构成成分。
天然的玩具很多,比比皆是,唯有蜗牛让我们爱不释手。蜗牛多裸露在河滩、沟渠,有时藏在山地里。儿时,我们一边干活,诸如拔猪草、铲柴,一边找蜗牛。等到找到一小攥把时,就坐在一起开始挤牛比赛。挤牛就是用一只蜗牛壳的顶端挤压另一只,挤着挤着一只脆弱的蜗牛壳就会被另一只钻破,如此反复,所有的蜗牛壳都被挤破,谁拥有最后一颗久挤不破的蜗牛,谁就是牛王。经过几次比赛,我们对哪种蜗牛牛劲大,哪种不行,就有了辨认的经验,于是就专找那种顶端凸起、油光青亮的。现在想起来,这种牛劲大的是刚死去不久的,而一挤就破的属于死掉时间长的,岁月早已风化了它的外壳。说实话,那时我们挤牛都挤的是已经死去的蜗牛,真正活着的我们很少见到过。
记得我的第一个自制玩具就是陀螺,不过我们叫它牛儿。截一个三寸见长的木棍,把一端削尖,用破布带拴一个鞭子,将鞭子缠绕在木牛腰部,尖端放在平坦的地面上,一拉鞭把,牛儿就会顺势在地上旋转,然后用鞭子不停地驱赶它,这就叫赶牛。如果能在尖端上放一个小滚珠,在顶端上用红蓝颜色画几道圈,不但旋转时间长,而且旋转时上面的彩圈飞舞,十分好看。赶牛最好的地方是冬天河里的冰面上,虽然捉鞭子的手冻得发红,时不时让我们放在嘴边呵呵气,但赶牛的劲头十足。虽然冰上行走脚下很滑,时不时就听到同伴一声哎哟,便知谁又摔了一跤,但大家笑声不断,兴致十足。坦率地说,我小时候在冰上赶牛比我的孩子在街道旁比赛四驱车的那种情趣要质朴得多,由此陶冶出来的性情更经得起岁月的摔打与磨砺。
我的第二个自制玩具要算风车,不过至今我还是叫它风转儿。风转是在一个掏空瓤子的核桃壳上横穿一根竹棍,里边再套一个小竹竿,竹棍的顶端插上几根鸡翎,风带动鸡翎,核桃就跟着旋转,并发出一种动听的声音。我的父亲心灵手巧,做出的玩具常常比他人的精妙得多,我也因之在同伴中的地位显高,说话的底气也很足,有时也摆几个谱,让他们一个个围着我转,那种得意十足的派头现在想起来,倒觉得好笑。人就是这样,总有一种潜在的占有欲,一旦欲望得到满足,就会自然流露出一种矜持感。“见蜜就甜”是一种欲望,“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另一种欲望,欲望不同生活的情趣就不同。容易满足的人总生活得有滋有味,欲望强烈的人常常活得很累。知足常乐是一种生存之道,知不足常乐也是一种人生哲理。同一个“足”字,却意思有别,就看你如何看待“乐”的境界。这种乐似乎深藏玄机,只有儿时的乐才是最纯粹的不染尘埃的乐。
上学后,看着大孩子们滚铁环,我开始想拥有这种玩具。放学回家后,我将家中的一个坏了桶梁的木桶拆掉,取下那个箍桶的铁圈,翻箱倒柜找出了半截洋丝扭了个弯钩,镶在向日葵秆上,一个滚动的手柄就做好了。我拿着自己亲手做的铁环在大场里滚动时,很快吸引了不少孩子。于是,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同伴差不多人人都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铁环。记得社会子做铁环时,找不到铁圈就将家里吊水用的好木桶拆了,不但他自己遭到了父亲的痛打,就连我也稍带挨了骂:尽是这林林子的坏点子,要不是他,社会子能平白无故害人吗?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有错,有好一段时间总躲着社会他爸,现在想起来我一点没错,要错就错在那时我们太穷了,穷得挖地三尺也找不出来半截细钢筋,即便是细一点的洋丝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了。
后来,我又对自己的铁环做了改造,在大环中又套了4个小环,待铁环滚动时,顺着大环旋转的小环发出仓朗仓朗的声音,美妙极了。上学路上,我们滚着铁环走,铁环仓朗仓朗地响着,声势浩大,乐趣无穷。滚铁环还能滚出许多花样来,技术好的,单手拿铁钩将铁环往前一送,铁环就乖乖转动起来。滚在路上也能“停车”,即铁环斜靠在车把上,再滚时弯钩轻轻启动就行。累了,用弯钩钩住铁环,往肩上一扛,那姿势极为潇洒。用钢圈做成的铁环有着滚好长一段路而不倒的优势,凸凹的路面和水坑也不在话下,这让我在同伴面前出足了风头,自豪极了。
弹弓,我们又叫它雀叉,那是专门用来打麻雀的。它做起来比较简单,找一个叉形的树枝,在它的两端各拴一个橡胶带,再用一块皮子将橡胶带的两头固定,雀叉就算做成了。只是那年月胶皮不好找,因此有雀叉的孩子并不多。我十二三岁时才有了一个雀叉,不过我的雀叉不是“Y”形的木叉,而是用洋丝制作的“U”形带柄的铁弓,不光看起来美观,用起来也准心较好。当我们比赛瞄靶时,我的弹弓往往命中率较高。那时,我们玩弹弓,用土块、石子作子弹,用麻雀作靶子,只是吓唬吓唬它们,很少有人真正用弹弓将麻雀打死。虽然儿时我们并没有在课本里学过保护鸟类方面的常识,但山里人终年与鸟为伴,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让我们对喜鹊、普鸽、麻雀、黄鹂等这些山野的精灵护爱有加。即便是消灭“四害”的那阵子,一个麻雀腿腿可以在商店里卖一分钱,我也很少去赚这种钱。那时,钱对我们来说金贵无比,但我们对自己朝夕相处的生灵说什么也下不了生杀的手。
此外,毛蛋(旧棉花做芯,上面缠上毛丝线)、纸船、纸飞机、高粱秆眼镜等这些自制的简易玩物为我的童年增添了无尽的乐趣,也把我们单纯的梦带出了大山深处。尤其是三月的柳笛、六月的瓦坞(陶埙)、九月的篦篦道(口弦)、十月的泥哨、腊月的树皮桶二胡,这些土色土韵的乡村特有的儿童乐器,吹奏出童年的五色音符,让童谣穿梭在四季的风雨中,圆熟了我们稚嫩的音色,最终烧制出乡村后生老成、持重的做人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