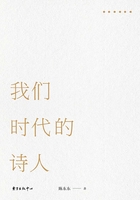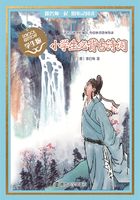山里的野花是山里的金盏,点亮节令的灯芯,照着小草生长的路。
山里的野花是山里的图画,描出阳光的金边,装点风儿到不了的空间。
山里的野花是山里孩子朴素的笑脸,一张张,一簇簇,纯真自然的面孔丰富了山村的表情;一阵阵,一片片,银铃般的笑声从田头地埂漫过,草长莺飞,抒情的节拍让田野五彩缤纷。
山里的野花从春天一直开到深秋时分。红、黄、白、蓝、紫,各种颜色让人眼花缭乱;兰、菊、苋、旋花、石竹,各个科属使人应接不暇;喇叭、鸡冠、狗尾、玉盘、猫耳,千姿百态,撩人心弦;田埂、山坡、沟壑、路旁、河滩,星罗棋布,引人入胜……
山里的野花是开给山里孩子看的。
春天来了,一丛丛狼毒花开在山坡上。从村子里远远望去,粉嘟嘟、雾腾腾一片,着实好看。于是,叫几个小伙伴,跑到山上,我们采摘狼毒花。狼毒花,故乡人叫它狗苣子花,它的茎,直立,丛生,不分枝,浑身锁着椭圆形的细叶,头顶上举着球状花序,有的开白花,大多数是淡红色的,火柴头般大小的花骨朵,娇美无比。尤其是细瘦的花筒里藏着针尖那么小的一种小虫,我们称它狗娃。找狗娃是最有趣的事儿,每人手里拿一股,找一块干净的路面,只要把手中的花束在地上用力摔打,受了惊吓的狗娃,就会从花心中跑出来,密密麻麻一片,这时我们就会静静地观察它们,直到它们一个个钻进草堆里,便开始坐在山坡上编花环。正因为狼毒花的枝干柔软细长,叶片窄小,用它编出的花环戴在头上,花朵排列有序,漂亮极了。
进入四月,整个山村清新明媚,晨露洗涤了夜间栖息在叶片上的尘埃,阳光给所有的枝条涂上一层亮漆。对面的屲上,一片片刚刚送走花期的杏树林青翠欲滴;身后的坪上,一坨坨绿油油的庄稼向早起的人们点头致意;田埂地头,青青的冰草在祥和的气氛中努力向上生长;房前屋后,榆树挂满了串串铜钱,着实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路旁沟渠,柳树抽出毛茸茸的花穗,惹得蜂蝶飞上飞下……满山遍野碧草如茵,天蓝,风柔,鸟雀啁啾,村庄处处弥漫着草青花香的气息。
这时,所有野花都从叶丛中钻出,露出婴儿般娇嫩迷人的脸庞。在这些自由开放的鲜花中,最为灿烂的,也最让我们激动不已的要数打碗花。打碗花盛开在崖畔、田头、路边,细长的枝蔓袅袅婷婷,一路向上,劲头十足,纯白色、粉红色的花朵在微风中轻颤,像民间的唢呐吹出悠扬清新的小曲。别看它弱不禁风,一旦开起花来总是泼泼辣辣、热热闹闹。
故乡有很多禁忌,打碗花带回家将会打破家中的碗,就是其中的一种。打碗花带回家就真那么灵验吗?“硬叫耳听着,不要叫眼见了”,母亲的规劝让我每此打消了第一个想吃螃蟹的念头。是的,有一种事情只要你一直怀有神秘感,不要固执地去捅破那个纸糊的窗户,内心深处也就一直存着一种甜美的梦,这种美好就是一种向往,而保留这种向往就是一种慈心善念。
地雀花是山里最香的一种花,它匍匐在地的蔓儿向四周不停地拓展生存的领域,它层出不穷的花朵不断延长了生命的花期,从春至秋,以它独有的香气一直在山里使劲地展示着自我的价值。每次上山我总要摘些地雀花,放在窗台上晒干,用油炒了拨一点放在碗里,一股特有的野香直沁心肺,原本一碗普通的饭因有了地雀花便显得美味可口。
秋天是野菊花的天堂,那轰轰烈烈开放的野菊花,张扬着季节的情绪,是秋天最优美的诗句。白的如雪,黄的似金,红的热烈,蓝的清爽,它们目送着南飞的大雁,欢呼着成熟的庄稼,在寒风中抱成一团,竞相开放,面对渐渐逼近的霜期,它们相互勉励,共同平分山里的秋色。
我曾不止一次用山菊花自喻。山坡上、地头边有我童年的影子,不嫌山大沟深,不怨土地贫瘠,与伙伴一道守护着山里的风俗;深秋里、寒风中有我少年的志趣,不怪天干地旱,不叹出身寒微,与鸟雀一起歌唱乡村的宁静。即使走出山里,走到城市的上空,也是盆栽在阳台上的一束山菊,用山里特有的憨厚纯真的情感,向城市的阳光、向来往的白云开出朴素的花朵,不失山野宽容的本色。
山里的野花,有人欣赏没人欣赏,它们都开着;无论向阳还是背阴的地方,它们照样打起精神;不管春夏秋冬,它们从不错过开花的时令。山里的野花,它们独自开放的天性,不畏酷暑严寒的品性,自由生长、蓬勃向上的个性,以及几分不受羁绊的野性,让我想到今天的教育,应该让孩子像山里的野花,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性情,有自己的花色品种,甚至允许孩子有点有悖常理的做法,这样校园里便一定是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