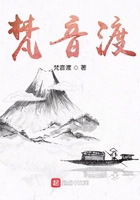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他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今河北邯郸)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太后跟先帝刘知远很久,经历了很多天下大事。陛下您正年富力强,有事情应该先向太后禀告而后推行。宫中朝中,要亲近忠诚正直的大臣,放逐谗佞邪恶的小人;善恶之间,要有明智的审核。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时期的老臣,能够为国尽忠,期待陛下能够推心置腹信任并任命他们,这样,可以让国家社稷不至于有败亡之危……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乱世中的"圣贤"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有个茶酒使,照顾隐帝吃喝的中官郭允明,因为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经常跟他说些淫词、丑词。太后为此劝谏他,他也不听。隐帝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
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放纵"人欲",不懂自我约束,就是"悖礼"。传统之"礼"的本质可以用两个主题词来概括:当位、节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负责任就是当位;每一个人不得放纵人皆有之的欲望就是节制。人欲,不可没有,也不可放纵。对帝王而言,节制"人欲",尤其重要。但不懂节制、放纵"人欲",实是历来帝王之惯态,也是历来社稷遭遇颠覆的逻辑源头--因为国家元首放纵,所以朝野群下效仿,从此导致政治昏昧,致使小人奸党弄权,终于民生凋敝,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于是,血雨腥风中,江山易主。
帝制社会中,圣贤人物至为担心的大事在此。圣贤人物考量此类风景也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元首的"人欲"之放纵,其原因在:不读圣贤书。于是,宫禁之中有一常设的制度性规定:经筵--聘请德高望重的儒家人物充任帝王之师,为他讲述圣贤经典,以此建构国家元首的圣贤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简单表述为:王道理想。传统帝制之政治制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制衡。君子是讲述并恪守圣贤价值观的,小人恰好相反。因此,庙堂之上,大臣劝谏帝王"亲君子、远小人"的风景屡见不鲜。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规劝模式"。
五代时期尽管是乱世,尽管多由不懂圣贤价值观的帝王执掌天下权柄,但大臣之中总还是有一些未曾泯灭圣贤价值观的人物,冒着被黜落的风险劝谏帝王--他们期待这个乱世尽可能地好一点,哪怕好那么一点点。
张宪死不拥新主
劝谏隐帝刘承祐的人物,除了郭威之外,是大臣张昭远。此人比赵匡胤大三十多岁,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通晓儒学,读过当时流行的九部儒学经典,能明了圣贤大义。他还是一个藏书家,家藏图书数万卷,据说他甚至藏有武则天的亲笔诏书九十多篇。
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个儒将张宪。张宪在后唐时得到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信任,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张宪做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最后被任命镇守河东,在太原做了节度使,也是一方藩镇。史称张宪年少之时就喜爱儒学,精通《左传》。他家有藏书五千多卷,公事之余,常常一部部书为之校勘。这样认真的读书人,五代罕见,作为一员武官,更是难得。
张昭远决计结识这位儒将,于是带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史称《三代兴亡论》,去见张宪。张宪一见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下就给他官做,后来成为河东藩所的推官,也即河东战区的司法主任。
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赵匡胤出生的前一年,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藩帅,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发动兵变。张宪的亲属很多在魏州,但得到了赵在礼的"善待",原来,赵在礼以此为手段,写信劝降张宪。张宪将魏州来使处死,根本都不打开来信,原封不动地派人送到京师洛阳,以此表明忠君大义。但不久庄宗李存勖被叛兵乱箭射杀,李嗣源入京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往太原。显然,李存霸知道皇兄李存勖最信任的人物就是张宪,所以在万难之际来依附河东。但唐末以来"权反在下",将士们大多贪图富贵,张宪的左右带着一股乱世流行的势利眼,也不愿意与李嗣源对峙,就鼓动将士将李存霸拘押起来,之所以没有杀掉李存霸,也是在观察形势--如果李嗣源坐稳江山,就杀掉李存霸;如果坐不稳,再做处理。
在利益的角逐中,张宪这位藩帅,与此前此后的藩帅一样,已经受制于"权反在下"的将士。张昭远看到了形势的险恶,出于对张宪的关爱,他劝谏张宪赶紧奉表拥戴李嗣源,否则将要引来杀身之祸--不知道左右部下们会做出什么来!张宪也看到了这一危局,但圣贤价值观就在此际开始起作用,他对张昭远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籍籍无名的布衣,到今天做到一方大员,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情!我岂可因此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让我背叛先帝,我做不到啊!"张昭远立即明白了这位节度使的忠诚价值。他知道唐末以来,这类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更知道张宪如果不能拥戴新主可能的后果,于是边哭边说:"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志向啊!你能这样实行,可谓死而不朽啦!
史书留下了两人这一段对话,整个五代时期,这是"忠义"价值最重要的一次叙事。《宋史·张昭远传》评论说:"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当时的清议(社会舆论)很看重张昭远这番话,认为能够成就张宪的气节。
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区别于《旧五代史》的重要义理就是"春秋笔法",也即对历来君臣士庶做道义评判。五代之际,忠义难得,所以欧阳修专门做了两篇传记记录忠义之人,一为《死节传》,一为《死事传》,所谓"死节",也即自觉地死于忠义;所谓"死事",也即不自觉地死于忠义。前者记录三人,后者记录十五人,但是无论"死节"还是"死事",都没有列入张宪。我认为这是《新五代史》的一个疏漏,张宪就是欧阳修表彰的那种"全节之士",因此完全有资格进入《死节传》。
后汉隐帝时代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宪和张昭远二人所料:乱兵杀死李存霸,张宪也同时遇害,河东宣布效忠李嗣源,到新主之前求富贵去了。
《宋史》认为张宪同时遇害,《资治通鉴》认为张宪"闻变,出奔忻州",听说有兵变,逃跑到忻州(今属山西)去了。
张昭远没有"死节"也没有"死事"。但他应该能够从张宪的"死节"中看到乱世的渊源和祸患的逻辑。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有可能,就劝谏君主行正道不要走邪路。
李嗣源时,他做了史馆修撰,专门修《唐史》和《实录》,他得到一次机会,给李嗣源上书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臣看到先朝(李存勖)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伶人戏子,进门就给姬妾捯饬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的仆人骏马。有如此习尚,怎么可能有希望成为圣贤?现在,应该为陛下的诸位皇子精心选择好的老师,令皇子们躬身拜他们为师,要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培养一点敬畏之心,请老师们为他们讲习礼义和圣贤经典,论述国家安危之道。
古代人君一旦即位,就册立太子,这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以此塞住祸乱的根源。张昭远这一番话可谓"一言兴邦"之至理。帝制时代,权力交接自有合法程序,预先立储,正是让他人免去觊觎皇位的野心。
宫廷不乱,天下不乱,士庶平安。五代乱世,张昭远有此见识,已经迥异于一般朝臣。史称"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后唐明宗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不能接纳他的意见实施。而李嗣源死后的乱局,也恰恰因为没有做好权力交接所致。
到了后汉隐帝时,张昭远正做着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虽然这位隐帝望之不似人君,出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张昭远还是上书,要隐帝亲近儒家读书人,学习儒学经典和圣贤教训,不要亲近佞臣小人。
但刘承祐对此类建议毫无兴趣。历史经验:帝国管理中,国家元首对儒学没有兴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价值观,剩下的就是权谋意识、丛林意识,或无以名之的那种疯狂的放纵、享受意识。
后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帝王不学无术是一方面,执政们也流于五代陋习,动辄蔑视帝王。如此一来,君臣关系紧张,就是逻辑中演绎的风景。
儒学屡屡倡导"君君臣臣",其大义就在于: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何像个君?如何像个臣?历代帝王自太子时代就有师傅教授,做了皇帝也有御前讲习。这些帝王之师都在按照儒学理念中的"礼制"设计教育太子或帝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多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等等相关。这是一些多年累积之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价值观,综合来看,这些东西可以概言为"公道"与"仁德"两大互相关联的板块。
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君臣言行各有礼数。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因此,礼,不仅是上行仪式,更是下行仪式。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那就是邦国政治的失序。而政治的失序则造成帝国机器运转的"非正常化"--帝国一旦进入"非正常",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后汉隐帝时代,就在"非正常化"运作中,发生了悲剧。这个悲剧,是由后汉隐帝和执政们共同酿就的。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欲知后汉之悲剧,先要知道一个叫苏逢吉的人物。刘知远时,苏逢吉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他在性情刚严的刘知远面前表现甚为乖巧伶俐,以至于有些奏章,大臣们不敢奏对,苏逢吉就选了一些,揣摩着刘知远心情不错的时候,适时递上,往往也就获得了批准。刘知远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玩弄,这样就在众官之中形成了"苏逢吉上头有人"的感觉,于是人人都来巴结苏逢吉。
当时后汉制度草创,很多"典章"直接出自苏逢吉之手,但此人不学无术,只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临时提出意见,所以史称"汉世尤无法度"。
在五代中,后汉尤其没有制度建设。他更不施德政,综观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令人鄙夷的故实却一桩桩一件件。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是索贿。他的索贿,礼、义、廉、耻全不顾。
后汉初建,地方大员纷纷前来京师汴梁朝见新主刘知远。内中有一个来自凤翔的官员李永吉,苏逢吉认为此人是原来后唐的皇室,一定有皇族"奇货",就派人暗示他,索要后唐皇上用过的玉带,说只要给我玉带,可以推荐他做一个州官。但李永吉告知他:没有这个玉带。于是苏逢吉让人到市场去购买一条玉带,价值数千贯,让李永吉代偿这笔钱。
又有一位客省使(负责外交、礼仪事宜的官员)名王筠,在后汉之前的后晋时,就到南方的楚国(当时占有湖南全境和广西部分,属于"十国"之一)公干,现在后汉建立,就回来向刘知远汇报南行结果。苏逢吉认为他肯定得到了楚国的重贿,于是派人去找他直接要东西。王筠有了"怏怏"之色,但没有办法,将带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但李永吉、王筠,都没有得到州郡的官职。这事等于用了人家的钱财连事都不办。
索贿到这等境界,史上罕见。对待下级官吏不尊重,无礼;受人贿赂不去报答,无义;做官不清不白,无廉;公开指使下人讹诈,无耻。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去考察,如此邪痞的赃吏也是罕见的。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