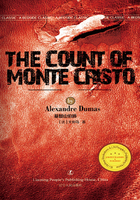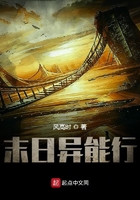五天以后小班摇着船去了鹤顶,还是没有把老班接回来。老班说,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他们俩人必须全力以赴把图纸定下来,图纸搞好了就可以分头做了。小班看到他们争论得很激烈,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简直是一寸一寸地商讨即将设计出来的枷锁。偶尔老哈烦了,老班不让他烦,即使老哈烦了他也不放弃和他一起揣摩。小班吃了顿午饭就回花街了。
又过了五天,小班总算把父亲接回了家。接回家的不仅有父亲,还有几大捆木料和竹子,堆了整整一船。一路上老班都在围着木料和竹子转,用手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小班说什么他都嗯,过往船上熟悉的人远远地对他打招呼,祝贺他出来了,他也嗯,有时候连头都不抬。过去不是这样的,老班人好,谁都和得来。
到了家里依然如此,只顾着把木料和竹子翻来覆去地弄,一会儿截,一会儿拼,谁都不理。街坊邻居听说他回来了,都过来看他,他就叼着烟斗嗯嗯地敷衍,对方说什么他根本就没听见。这让小班娘很不好意思,只好尽力把家里能吃的小东西都拿出来招待邻居,免得人家见怪。事实上邻居们还是见怪了,都觉得老班坐牢还是坐出问题了,头脑显然没有过去好使了。要么就是坐傻了。他们接着又同情老班,每到小班娘见到老班不理人要生气时,他们就劝,说先随他去,在那里头蹲了两年了,连个太阳都见不着,也挺不容易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别跟他计较。说得小班娘哭笑不得,她知道孩子的爹没毛病,但他的入迷到这种程度,也是她没有想到的。
老班关起门来,闭上耳朵干活,外面的事一概不关心,邻居吵架他也不去看看热闹。最近花街上的灵通人士都在传闻,南边打起来了,说是一帮人和官府打起来了,一直在向这边来。这个消息让花街人激动了好长时间,他们把原来议论的中心老班给放下了,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想像那伙人长什么模样,竟然跟官府对着干,还要把皇帝从龙椅上赶下来。消息更灵通的人说,早就打起来,一年前都打起来,不过是离花街太远,杀人的声音我们听不到而已。老班不管这些,手艺人嘛,没有比把手里的活儿干好更重要的事。
他还是见识了外面的动荡。那天他从鹤顶回来,在运河上遇到了两只大官船,船上站满了武装齐备的兵士。所有的小船都被勒令靠边停下,让官船先走。本来他从老哈那里回来,心情就不好。他在制作新枷锁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个小地方没法完全按照图纸来实践,他就去和老哈商量。谁知道老哈手头的东西几乎没有进展,他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越做越觉得没有意思,失去了耐心。老哈说,你说我们做这东西有什么意义?做好了也没人给我们钱,又不是衙门里下达的任务,实在是没事跟自己过不去,他老婆也不赞同继续做下去,做个凳子还能挣点打灯油的钱呢。老班听了很难过,觉得老哈在背叛他们共同的事业,差点和他吵了起来,最后总算勉强说动了老哈,还是继续做,但是他看出来,老哈的兴致事实上已经大踏步撤退了。回来他又装了一船鹤顶的木料和竹子。他有气无力地摇着船,一路悲伤,又撞上了这群耀武扬威的兵士,心情更糟,他不知道装着两大船的人在河上跑来跑去干什么。真是莫名其妙。
但是,进了家门把木料和竹子摊开,老班又精神抖擞,他几乎已经能看见即将做好的枷锁了,那么完美,无懈可击,套上了你就逃不掉,而且越想逃越折腾,枷锁就越紧,把你套得越牢。他要让衙门里当官的看看,他老班能做出最好的枷锁,让鬼见了都没办法,何况那些一天吃三顿饭的囚犯。
他的行为又遭到了大班的否定。大班自从接父亲那天和小班分手,一个多月了,终于回到了家。他看到父亲还在做这东西,很不满意。
“爹,”大班说,“你怎么还做这个?苦头还没吃够啊?”
“这叫什么话,干这行不做这个做什么?”
“马上都改朝换代了,这东西以后谁还用?”
老班愣了一下,抬起眼皮看看儿子,“你说什么?”
“革命了,朝廷要完了。”
老班赶紧站起来,手慌乱地挥动,“你瞎说什么。你住嘴。”
“我说的是事实。早晚的事。你看到处都要打起来了。”
“瞎说。你真是瞎说啊,”老班嘴都哆嗦了,让小班去把院门关上。
“南边早打了。衙门里都怕了,不然他们为什么在运河上来来回回跑?”
他们的确是在运河上来来回回地跑。他们跑什么呢。看来真乱了。可是外面乱糟糟的,大班为什么也到处乱跑?大班说,他回来就是跟他们说一声,他要跟朋友去南边做生意,要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兵荒马乱的,你做什么生意?”母亲问。
“瞎做,什么挣钱干什么。我就是帮个忙,本钱都是朋友的。”
“听说外面整天在杀人,你就别到处跑了。”
“娘,没事的,我又不是去打仗,是去做生意。”大班说,为了转移话题,他又对老班说,“爹,你做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衙门里抓坏人,不让他们逃掉,”老班说,又蹲下来捣弄截好的木料和竹子。“一套一个准。”
“抓的也不一定就是坏人。”
“不是坏人衙门里还抓他干什么?”
大班不再跟父亲争辩,进屋收拾自己的行李,晚上就要坐船离开花街。母亲很难过,一个刚从监狱里回来,一个就要长途跋涉出远门。
“不能在家待几天再走?”
大班说:“朋友在等着。做生意得赶时间,一天一个价呢。”
大班在家吃了晚饭,饭桌上他又和父亲说起做枷锁的事。他觉得父亲是在帮助官府欺压百姓,帮衙门做刑具,简直就是为虎作伥。当然他没这么说。老班说,他不是父母官,管不了那么多,他就是一个做刑具的,就像卖烧饼的一样,哪能管得了别人吃了烧饼去不去杀人。再说,不是坏人衙门费那么大劲抓他干什么。大班就不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