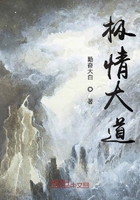很多年前的一天,木匠老班的两个儿子,大班和小班,要到城里把父亲从监狱里接出来。为了不让老班在监狱门口久等,天没亮就出发,兄弟俩轮换着划桨。从花街到城里,水路得走二十多里。他们不敢划得太快,运河上起了大雾,船头看不见船尾。为了防止与对面突然出现的船只相撞,小班在两支桨上各拴了一个大铜铃,每划一下桨,铃当都哗哗响个不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大意,雾气太重,把铃当打湿了,声音听起来也潮湿沉闷,完全没有平时的清脆,传之不远。好在一路平安,没什么大事。他们仔细辨别周围的声音,看不见船,只能往来的船只上的人声,都像用棉花捂着嘴说话。
开始是大班摇船。大班后半夜才从外面回家,出发时兴奋劲还没消,一点睡意都没有。小班就不行了,他从床上被大班拉起来,迷迷糊糊跟着往外走,拴完了铜铃又迷糊了,打着哈欠坐在船舱口看大班划。大班划了一会儿,跟他说话,发现弟弟坐在那里已经睡着了,身子东摇西荡。大班就让弟弟到船舱里睡,外面雾水重,要生病的。小班听了,往后一倒就躺进了船舱,又睡着了。等他醒来,伸出脑袋看外面,雾还很大,船走得好像慢了,他看到哥哥的头歪在一边,两只胳膊生了锈似的,越划越慢。大班也扛不住了,到底一夜没睡。
小班从船舱里爬出来,说:“哥,你睡一会儿,我来。”
大班清醒了一点,笑笑,“三天没睡了,到底不行。”
“三天没睡?你都干什么了?娘在家整天担心。”
“没事,和朋友在一起,想做点生意。”
他没推辞就把桨给了弟弟,他知道小班比他对这东西更在行。这两年一年到头在外面跑,家里的事基本上都是母亲和弟弟操持,他有点惭愧。还没等惭愧深入下去,他就睡着了,两只脚还露在船舱外。醒来船已经靠岸,大班听见喧嚣的人声,天也亮堂多了,雾还没消散,但太阳总算能看见一个圆润瓷白的轮廓了。
兄弟俩泊好船,上岸去监狱门口接父亲。门口空空荡荡,站着四个持刀的士兵,一只麻雀都没有。没有老班。小班胆怯地看看大班,大班咳嗽一声,上前去问把门的士兵。
胖士兵说:“什么老班?不知道。我只管看门。”
另一个脸上长黑毛的士兵说:“哪来的老班小班。就出来两个疯老头,一人拎一个包袱,咕咕哝哝地走了。”
“是一个长山羊胡一个长络腮胡子么?”
“我是你们家老妈子呀?”胖士兵烦了。“滚一边去。”
大班一声不吭地盯着他,让他一愣,伸手去抓腰下的佩刀。小班赶紧去拉哥哥,让他快走,说只出来两个老头,那一定是了,另一个是老哈。大班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就和小班往码头走,到那里去打听。他问了码头上卖早饭的小摊贩,又问了蹲在船头吃烟袋的船夫,他们说,是有两个老头,一直在争执个什么东西,大清早租了船回家了,说是去河下游的鹤顶。这就对了,大班也松了口气。另一个老头应该是哈图,老班叫他老哈,沿花街再往下游走,家在鹤顶。他们俩一起干活,一起被官府抓起来,一起蹲的牢房,现在又一起放出来了。
小班说:“爹真是,说好了我们接的。”
大班说:“出来了就好。雾大,路上也没看见。你先回去吧。”
“那你呢?”
“我还有点事。你跟爹说,过两天我就回家看他。”
摇了半天船,父亲却提前走了,小班一下子泄劲了。好在回去顺流,雾也开始散开,小班慢腾腾地划,两眼瞅着运河两岸的景,顺便看了看来往船上穿花衣服的小姑娘。中午时分,小班到了花街前的石码头,他拴好船,回家告诉母亲,爹已经回来了,跟老哈去了鹤顶,让娘不要担心,他填饱肚子就去鹤顶把爹接回来。母亲听了才放心,一放心又哭了,老班在里面蹲了两年,她总担心老头子会死在监狱里,因为老班的罪和别人不一样,他做的枷锁出了问题,官府捉拿的罪犯逃脱了。老班是个做枷锁和刑具的。
午饭之后小班继续摇船,鹤顶离花街近,十里的水路。他找到了老哈的家,在一座小码头后面,他和老班去过几次。鹤顶盛产竹子,毛竹、斑竹都有,丛丛簇簇到处都是,老班常去鹤顶,目的之一就是去寻上好的竹子,刑具上有用。另一个目的就是和老哈商讨做刑具的事。老哈和他一样,早些年是木匠,活儿做的好,城里当官的知道了,就让他们做刑具、枷锁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世道乱,官府要抓的人太多,库存的刑具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衙门里规定,手艺优良的木匠都要改行。他们俩做木匠时就是不错的朋友,改了行还是同道,关系更好了。被罪犯摆脱的那个枷锁就是他们俩共同制作出来的。按理说那东西应该是衙门里最好的枷锁,但是罪犯就是挣脱了,然后就逃掉了。当官的很来火,那罪犯是上面点名要的,现在竟然逃掉了,做枷锁的也逃不了责任,他们俩就被关起来了。刚进去时,两个老头心里都不服气,认为那枷锁堪称完美,罪犯脱掉了不是枷锁的错。关了一年半之后,他们才逐渐琢磨出来,那种枷锁其实还是有不小的漏洞的,这个发现让他们平和多了,在监狱里不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愁苦得要死要活的。
小班推开老哈家的院门,看到两个老头正蹲在院子里,脑袋凑在一起,一人手里一根筷子在沙地上划,旁边是一块脏兮兮的布,一看就知道是迫不及待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上画着怪模怪样的图案。他们脚边放着饭碗,好几只鸡在碗里争食吃。两个老头和一群鸡对小班的到来都没有反应,各忙各的。
“爹,”小班说。老哈先抬头,两只眼瘦得都变大了。小班又说:“哈叔叔。”
老哈说:“是小班。”他用胳膊肘捣捣老班,“你儿子来了。”
老班说:“别动,这地方还是有问题。”继续在沙地上划。
“爹,回家了,”小班放大了声音。
老班抬起头,他的眼更大,头发和胡子凌乱不堪,一片花白。“哦,”老班说,“小班来了。”低头接着划。从小班的角度看,他爹的脖子好像突然拉长了,皮肤松弛,细脖子上挂着个尖瘦的小脑袋。
“你看,老哈,”老班画了几下,在某个地方重点捣了捣。“这地方问题最大,如果不解决,做出来不比上次的好多少。”
老哈嗯着,点头,招呼小班到屋檐下的竹椅上坐,又冲着堂屋里的小女儿喊,让她倒茶。
小班说:“你们在干吗?还要做?”
“做。”
“他们不是都把你们关过了么?”
老班头都没抬,“关过了,更要做。要做出更好的。”
“衙门里让做的?”
“不是,”老哈说,“我们自己做,要做出最好的。”
小班觉得莫名其妙,原来父亲没任务一般是不愿动手的。“爹,娘让你回家。”
“跟你娘说,弄好了就回去。”
他们在商讨一种新设计的枷锁的方案,彻底杜绝两年前那种存在的隐患,让所有带上这种枷锁的囚犯一个都逃不掉。在监狱里就开始了争执和商讨,现在还在讨论,从图案和他们争论的口气看,这个新东西离最后的完善和结束还很远。
“爹,回家吧。”
“这个弄不明白怎么走?不是让你先回去了嘛?”
小班没办法,最后只好一个人回去了。到了家把情况告诉了娘,娘说,你看你爹头脑没出问题吧?
“没有,”小班说。“好着呢,说起事来头头是道。”
娘感叹一声,说:“你爹痴了。随他吧,好在出来了,人没毛病就谢天谢地了。过几天你再去把他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