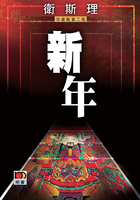船继续漂,我或者在前,或者在后。都无所谓。基本上没有时间概念。我睡累了就通过窗口和布帘子往石老板的舱里看。她知道我在看,我猜她甚至希望我看。上午一个男人上她的船,嘴里说买酒,进去了却半天才出来。他下船时,石老板对我勾了勾右手的食指,眉毛挑啊挑。她的表情让我脸红,但不让人讨厌。我当然没去,没那个胆量。午饭时她扔过来一块腊肉,脸上直掉冰渣子,说:
“别装模作样了,我可不想欠谁的!”
“我没让你欠什么。”
“那最好。别整天跟着我,烦不烦啊。”
这女人。我把腊肉扔到她船上,抓起橹要摇到她前面去,又想,偏在你后头跟着,我在运河里漂漂还不行么,水又不是你家的。真是奇了怪了。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我都在想这事。也没别的更好玩的事。半夜水声漫上了船,她的声音都比我的大,既然不把我当成个好鸟,索性不要脸一回,我就不信不敢进你的舱。我钻出船舱,她的船在前面,黑灯瞎火的,有鱼跃出水面,吓我一跳。鱼落入水里,水面上突然炸开的那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我紧了紧裤带,算了,明天再收拾你。还是心虚。我对着大腿狠狠地掐了一把。
第二天我一直告诉自己没醒,其实眼都睁开了。赖着不起,耳朵却竖得直直的,我希望钻出船舱的时候再也看不见石老板的船。对我来说,要“不要脸一回”至少现在还有点难度。可是她的声音沙哑响亮,我听见她高声喊:
“酱油?有!”
一直到午饭时分,不能再不出来洗脸了。一出舱门就看见她蹲在船尾淘米,“还以为你睡死过去了呢,”她说,“女人坐月子也懒不成你这样。”
“吃完饭我就去找你!”我脱口而出,把自己都听愣了。
“好啊,我沏好茶等着。”
没办法了。草草吃了饭,提提裤子我就跳上她的船,和其他嫖客一样,我把小船拴在她的船帮上,然后一声不吭进了她的屋。
“啊?还真来了,”石老板说,眉毛直上直下地抖。说真话,她那两根画出来的眉毛我怎么看都不顺眼,真想一把将它们给薅了。“这就沏茶。”
我转身关上门,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推到床上。我必须一下子解决问题,拖不起的不是她,是我。我就积攒了这么点勇气。相对于这么一艘船,她的床实在是太隆重太奢侈了,大得让人顿生大有可为之心。
“你干什么?”
“要债。”
她推开我,突然笑了,“真的假的?就你?”
这话让我相当不高兴,又来了点勇气,一把又将她推倒在床上,上来就往她腰上摸。先得解裤带,这我懂。我的手在哆嗦。没出息的东西。于是我把力气都用到手上,我能感到自己的狠。
“你真来?”石老板的笑僵在脸上,死死地捂住我的手。“你他妈的真来?”
我直直地盯着她,觉得头和脸一起胀大,应该像个又红又圆的大皮球。我不能让自己停下来。她猛地推我一下,一脚踹到我左腿上。
“你他妈的死一边去!”她的头脸也像个红皮球。
“是你要还债的!”
“今天不行!”她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剔骨尖刀,指着我,“你再动一下我杀了你信不信!”
我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了,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我忽然觉得不要脸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想要脸要不到,就像现在,我跟条鱼似的被晾在岸滩上了。我在她的刀前本能地举起手往后退,绊了一下凳子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她把门打开,刀还在手里,说:
“除了今天,什么时候都行。”
我狼狈极了,出门的时候觉得两条腿长短不一,跳上自己的船才发现缆绳还没解,又回去解缆绳。石老板一直拿着刀。
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待在船舱里,喝酒,睡觉,也不好意思驾船离开。那等于此地无银,明摆着捞不到就走。但这事我有点不明白,不是她犯病就是我犯病。第二天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石老板推开了我的舱门。“还挺尸呢,”她站在我脚前,双手掐腰。从我的角度看,这个高大的女人胸部雄伟,我甚至看见了它们在动。我的手一直在眼前遮光,以掩饰腰部以下在被子里急剧发生的变化。她以为我看不清是谁,就在我身边蹲下来,我的眼前立刻悬着两只大眼睛和一张浓妆之后的脸。
“是我,老娘!”
我的粗鲁吓得她叫起来,我一把抓住她,翻了个身就把她压到身底下。胳膊上的伤没事了,速度慢不下来。“你,你,”她说,“干什么?”明知故问,我的手已经伸到她的衣服里。她打了一个喷嚏,抓住我的手,“不行,你这窝又小又臭,我可不委屈自己。”我爬起来,顺从地跟她上了大船。她已经提前把船拴在一起了,看来早有准备。
开始时我还缩手缩脚,后来总算有点男人的样子了。不错,石老板很厉害,相当厉害,那张床应该那么大。
风平浪静后,她冷着脸催我穿衣服,说:“你帮我杀了人,咱俩是一根绳上的,你也别想着害我。我的债还完了,你可以走了。”
已经很明白了。我还装傻,“以后我还能过来吗?”
“当然可以,那就得带钱了。”
“哦,”我说。出门的时候忍不住又问,“昨天为什么不行?”
“昨天是我男人生日。跟你没关系。”
明白了。她男人。我出了她的门,旁边有条船经过,一个黑脸的瘦子对我暧昧地笑,说床大不大?我没理他,对水里吐了一口痰就去解缆绳。
躺到舱里就是漫无边际的时间和水。我要回的花街如同飘荡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三年了,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他们人是不是还在。我躺着,想起来就咪一口酒,瓶子就见底了。我起来去石老板船上买酒,顺便多带了点钱。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什么方法能遏制无边无际的飘荡感觉。
石老板只认钱,装进口袋就往床上一躺。每次我只买一两酒,所以不得不一次次跳上她的船。那几天我几乎是她唯一的顾客,我是说在床上。她的表情一次比一次松动,对我的兴趣也越来越大。有个晚上我在她那里待了很久,还陪她喝了点酒。二两酒下了肚,我们俩的话都开始多。我问她男人在哪,为什么让她一个人在水上漂?她说她不知道,很多年没见他了,他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了。那时候他没事就喜欢爬到槐树上玩,就是一个呆木头。我一惊,脸急着往一边躲,灯火烧着了我的胡子,弄灭的时候一半胡子已经烧没了。
“怎么回事?这么不小心。”
“没事,”我站起来要走。
她拉住我,找到一把剪刀,非要帮我把另外一半胡子也剪掉。她剪得很认真,那种坏里透着的仔细,我盯着她眉毛看,原来刮掉的眉毛是弯的,像两个倒扣的月牙。我还在她左耳朵上发现一个痣。胡子剪完了,她端着我的脸,左看右看,拍一拍,满脸的疑惑,说奇怪,有点怪。我又要走,她按住我的脑袋。
“别动,”她说。“顺便把头发也剪了吧。”
我知道她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索性低下头让她摆弄。她问我要不要剪个光头,我说随便,她就扳起我脑袋看,一只手按在我左眉骨处,她把我吊起来的伤疤往下拉,然后突然松了手,直直地看我,我努力让自己平静,她又去拉那块伤疤,接着后退两步,说:
“你,是呆木头?”
她认出了我。我知道我猜的没错,她是茴香。她的眉毛,她的痣,她的这个人。我们竟以这种方式见了面,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嫖客。在花街的时候,她逼着我叫她姐。我拉开门就往外面跑,她大喊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立在船尾不知所措,看着她一点点靠近我。她一脚把我踹到了水里。半夜的运河水直往骨头里钻,冷得我直哆嗦。
“上来!”她跺着脚喊,“你给我上来!”
我不上去,上去了可能还得挨一脚。她干得出来。见我迟迟不上来,她的火气一下子没了,跪在船边向我伸出手。“你上来呀呆木头,你上来,”她哭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三年,我把一条运河都跑遍了。你上来呀!”
立刻有水一样苍茫浩荡的悲伤和感激充满我心里,我伸手抓住了茴香。
“你跑哪去了?”茴香在舱外拧我的湿衣服。我在舱里,裹着被子,一蹦一跳地出汗。“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我的确觉得莫名其妙。
茴香晾好衣服进船舱,我打算跟她说点什么,但她根本就没兴趣,进了门就掐我一把,疼得我晕头转向,被子没抓牢,掉在了地上。我赶紧捡起来包住自己,我不能空荡荡地面对茴香。她也背过身,接着又转过来,掐了第二把。
“臭呆木头!狗屎呆木头!你都学会了嫖女人!”
我委屈地说:“不是你要还债的嘛。”
“还嘴硬!你就是嫖了!”说完她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头,低头翻着白眼,“我是为你才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