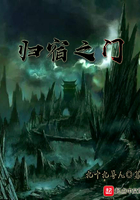一
太阳金光四射地照着念头岭。
念头岭背阴的一处凹地里,采石匠哼唷哼唷地喊着号子在撬一块大石。这是胡菰蒲家的采石场。为首喊号子的是徐二思的二叔徐石匠。徐二思上辈的徐家这二兄弟,一个做了铁匠,一个做了石匠。到了下一辈,徐铁匠却生了个和绣花针打交道的徐二思;徐石匠呢,他的老婆从嫁过来就病恹恹十几年不死不活,没给徐石匠生下个一儿半女。徐家两兄弟这手艺看来是要失传了。
“一块上好的青石。”徐石匠拍拍手,估算着这块青石在地下埋藏的年份。“兄弟们,起了!”他抽了一袋烟,招呼几条汉子重新把绳子撬棍等家伙操在手里。
又两轮号子声过去,青石从土里缓缓地升起来,被抬到平整一点的地方。青石在太阳底下发出近似透明的青光,让徐石匠爱惜不已。他重新点起一袋烟,坐在青石一角上,用手摩挲着它凉浸浸的还带着地下潮气的表面。按照他的经验,这样上好的青石应该是以岩层分布的。他目测着刚才挖出青石的深坑周围的地势,把烟袋锅在地上磕磕,站起来走到深坑旁边。
阳光穿过旁边大树的叶隙,像一根金色的胡须戳进深坑,照亮了什么东西,闪出乌色的光。“拿铁锹来。”徐石匠蹲下细看了两眼。
“给,石爷,铁锹。”一把铁锹递到徐石匠手里。他跳进深坑,小心地用铁锹扒拉开周围的泥土。一些树木的乳白色的根须,使那东西显得越发得乌黑。铛!铁锹和那东西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击打声。
“一柄剑!”给徐石匠递铁锹的伙计伸长脖子,惊呼道。
的确是一柄剑。徐石匠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生怕它骤然接触空气而化成粉末。他擎着它,用另外一只手的手指弹一弹那乌黑的剑刃。“结实。”他说。“你,去找我大哥来;你,去报告老爷,就说挖出古剑了。”
徐石匠重又在青石板上坐下,点起这片刻工夫的第三锅烟。早上他出门的时候感到右眼皮直跳,所以干活的时候就加倍小心,提防伙计们有个跌打损伤的什么闪失。现在看来,可能是应验在这柄古剑上了。
烟抽完,徐石匠跳进深坑,用铁锹继续往下挖。胡菰蒲和徐铁匠赶到的时候,他们被深坑外面堆着的那数量不少的铁器给惊呆了。徐铁匠蹲在那些铁器旁边仔细检视。“老爷,剑六口;戈两支;箭簇一百八十七支;古币二匝。”
“这是什么?”胡菰蒲拿起一个椭圆形的勺子一样的东西。
“老爷,要是我分析得没错的话,这应该是刁斗。”
“刁斗?”胡菰蒲拿着那铁勺子的柄,翻转来看看底部,又用手动动勺边上的一个铁环。铁环居然没跟勺子锈到一起,被胡菰蒲一动,灵巧地在勺子边上的圆孔中跳跃几下,发出好听的声音。
“好铁。”胡菰蒲赞叹。
“是的,老爷。淬火手艺不错。”
“刁斗。”胡菰蒲擎近来,欣赏手柄尾端的雕刻工艺。“透雕”。他说。“这么精美的器具,是干什么用的?”
“古代军中的一种炊具,容量一斗,所以叫刁斗;白天用来煮饭,晚上可以敲击代替更鼓。”
胡菰蒲笑了。“这么说,这些兵器是古代作战遗留下来的?”
“极有可能,老爷。”
“唔。”胡菰蒲又拿起一匝古币。“想必这就是刀形古币了。看来像是多枚古币;因用麻绳捆扎而多枚融为一体。如此说来,确已年代久远。铁匠,以你看,这些铁器大概是什么年头的?”
“这我也说不准。老爷可以问问曲先生。曲先生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地理,应该能知道。”
胡菰蒲也像徐石匠那样,坐在青石上。“好青石。”他摸摸石头,“可以做我的碑。”
“您说什么呢,老爷。”徐石匠从伙计手里拿过扇子,给胡菰蒲扇着一阵阵从岭上滚过来的热风。“日头挺烈的。”
胡菰蒲仰头看了看天空。他坐着的青石旁边有棵树,树叶像捉迷藏一样把日头从叶子中间甩来甩去。那堆斑驳的铁器躺在没有遮挡的太阳下,从胡菰蒲的方向看过去,升腾着若有若无的水汽。他想象着古代这里居然曾经打过仗,身上冷了一下。
“把它们运回胡宅。老黄,回去把后院那间凉房收拾一下。”
二
作为三进四合院,胡宅和其它这种院落的结构大体相同——后院坐落着一排用来当杂间和库房的后罩房。不过,胡宅的后院和其他人家的后院略有不同:胡菰蒲把它修成一个天井,紧邻厅堂的那面墙边还修了一条小游廊。有的时候,他厌倦整天坐在厅堂里面对那规规矩矩的院落和落日街。太太初秋懂得胡菰蒲的想法,便花了不少心思整理后院:游廊每年都是要刷一遍漆的,天井里养着许多花花草草。
老黄穿过东厢房旁边的狭窄过道,来到后院。他拿钥匙打开那间名叫凉房的闲置的空房,吩咐跟在后面的几个伙计赶紧洒扫。因为铺了一种念头岭上凿出来的特殊的青石条,这间房比其它房都要凉爽,尤其是夏天,一进屋就让人消汗。胡菰蒲给它取名叫凉房。在老黄头顶的门框上方,一只蜘蛛爬在网上,紧张地瞅着一把在空里挥来挥去的笤帚。它还没做好逃跑的准备,那只笤帚横空扫过来,破坏了它的网。蜘蛛落到地上,蒙头蒙脑的,马上就被一只脚踩中了。
一个时辰以后,胡菰蒲站在房中,嗅着墙壁和窗棂上粘附的清水珠散发出的气味。他很满意房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这么清洁。那些带着念头岭地下潮气又被太阳热烈抚摸过的铁,一件件被搬进来,摆在青石条铺成的地面上。六口剑、两支戈、一百八十七支箭簇、二匝十二枚刀形古币、一只刁斗。
“老爷,曲先生来了。”老黄躬身把须发纯白的曲先生让进房间。
除了老罗,曲先生是风波镇上从年龄来说排名第二的人。但他显得比老罗要老,可能正是因为那白得不杂一丝黑的头发、眉毛和胡须。他很乐于让这些白花花的毛发把自己体现得这么仙风道骨,所以,胡须和眉毛是不怎么舍得剪的:眉毛像凉棚一样搭在眼皮上;胡须飘飘然垂到胸前。只是有点脏。
“曲先生。”胡菰蒲微微向他颔首。在风波镇,让胡菰蒲敬重的人,除了老罗,也就是曲先生了。他儿子胡谦、他收留的胡逊、黄杏儿,三个孩子都师从曲先生。“您来看看这些铁器。”
曲先生习惯性地摸摸垂胸的胡须,然后握住它们的尾端,沉思半天。“兵器。”他说。这是多余的废话。
“您看,这是什么年代的兵器?”胡菰蒲问。
“依我看,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曲先生不疾不徐地说。
“怎么说?”
“这得从齐灭莱子国说起。莱子国,指的就是咱们胶东半岛这块地方。”曲先生环视众人,以确定大家都在认真倾听。“武王平定了天下,建立了周朝。他封姜尚到齐国上任。途中,旅店店家告诉姜尚,莱子国的人也正在赶往他的封地,企图西略。这两拨人马在营丘相遇并展开激战。莱子国的人战败,没能得到营丘,只好退回莱国。姜尚勤勉治国,在公元前567年,联合鲁国大举进攻莱子国。莱子国的人当时在这块气候湿润、适宜种植的地方冶炼铜铁、采金采矿,国力已是十分强盛,但仍是奋力抵抗未果,终于被灭。”
“以先生之意,这些挖掘出来的兵器,就是当年莱子国与齐鲁大军奋力交战中遗留下的?”胡菰蒲说。
“以老朽所见,应该是。”
“锻造这些兵器的人也算是能工巧匠了。”胡菰蒲对相跟而来的徐铁匠说,“铁匠,你看呢?”
“老爷说的对。我家世代都是做铁匠的,我爹说,古代铁匠的手艺比现在强一万倍,特别是淬火这道重要工序。所以他们造出了许多精良的兵器,在地下不管埋多少年也不会腐烂。有些拿出来打磨一下,还能锋利如新呢。”
“那是。要不怎么会有干将莫邪这些传说呢。” 胡菰蒲吩咐老黄把房门锁好,然后转向曲先生。“先生,请到厅堂喝茶一叙。”
当年曲先生就是在东厢房里教授三个孩子读书识字的。按照胡菰蒲的要求,那几张桌凳仍摆在房里。还有曲先生用过的戒尺。胡菰蒲曾打算将来让孙子也到东厢房识文断字,哪想到世道变了。
“唉。”胡菰蒲叹了一口长气。
三
下午,落日街上有人喊:“来了!变鱼的人来了!”
布店小掌柜胡逊手里拿着一个鸡毛掸子,正在拍货架上的灰尘。天热起来了,秦腊八嫌热,把窗户全都打开了,灰尘就格外地多。在落日街上叫嚷的人,正是秦腊八的爹秦六指。上次,这个嗜酒的人因为在鸟窝村喝酒,而错过了那场被风波镇人盛传的把戏;这次,他激动地成为向人们宣告把戏将要开始的人。
秦六指是在风波桥上遇到耍把戏的汉子的。他这次仍是在鸟窝村喝了点酒,不过不算很多。在风波桥头上他停下来,朝桥下面撒了泡尿。他掖好肥大的裤腰,就看到耍把戏的已经走到身边了。“我认识你!”他兴奋地说,“前几天,你告诉我布店有条奇鱼。好家伙,原来是你变的。这次要变什么新鲜玩意儿?”
“到时再说。”黑瘦汉子看看天空,“太阳可真猛。”
秦六指的义务宣传,使布店前面霎时围上一圈人。因为上次那条鲤鱼的缘故,徐二思和秦腊八也都跑了出去。胡逊见状,只好留下来守店。他站在店门口朝圈子张望。不一会儿,就听到人群发出叫好声,想必是刚表演完“仙人摘豆”等垫场的小把戏。无非就是手快呗,胡逊想。
但上次那条鲤鱼,到底是怎么从荷花缸跑到碗里去的?任凭黑瘦汉子多么手快,也不可能隔空捉鱼吧?胡逊倚在门框上望着人群琢磨这个问题。他想,可能是这汉子有同伙。
胡逊正琢磨着鲤鱼的事呢,人群忽然裂开一条缝,正冲着布店门口。黑瘦汉子大踏步朝他走过来。“小掌柜,上次那鱼活得还好?”
“承蒙惦记,活蹦乱跳的。”胡逊说。
卖艺的黑瘦汉子顺胡逊的目光朝那只搪瓷瓮看过去。“活蹦乱跳的。”他同意胡逊的话。“可否请小掌柜的再将这条鱼借给在下?”
“敢问这回你要把它变到哪里去?”胡逊警惕地看看搪瓷瓮。红鲤鱼移居到布店以后长势不错。
“该回哪儿就回哪儿。”黑瘦汉子显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不就是有同伙嘛,胡逊想,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红鲤鱼该回哪就回哪。
“掌柜的,借给他变变看嘛!”秦六指仗着他是秦腊八的爹,很优越地挤到店里来,占领最佳视角。
“爹,你出去。”秦腊八也跑回店里。她一脸不耐烦,冲她爹掉脸子。自从上次秦六指扬言给她在鸟窝村找了户人家要把她嫁出去,她就一直和秦六指闹冷战。
“好吧,借你。”胡逊说。“但我有言在先,如果这个把戏没耍好,你以后就别来风波镇了。”
“那是自然。耍把戏的吃的就是手艺饭;手艺不行,活该饿死。”黑瘦汉子环视门外的风波镇街坊,“众位街坊高邻,请让条道儿。”
“我来搬。”胡逊亲自搬起那只搪瓷瓮,跨过门槛,把它放到落日街上。他冷眼看黑瘦汉子煞有介事地闭着眼喃喃自语,然后运气发功,在街面上闪跳腾挪。接着他绕那只搪瓷瓮开始转圈,速度由慢变快,人们只看到他青色的对襟布衫像被谁在挥舞一样。
“转这么快干什么,看不见了!”秦六指嚷道。
玄机就在这里,胡逊想。他往四周看了看,没发现有像是汉子同伙迹象的陌生人。等他扫视一圈再回过神来,汉子已经慢下来,只剩下青色布衫的衣角还在微微飘动。
秦六指第一个跳到搪瓷瓮跟前。“鱼呢?”他低了低身子,把头探进瓮里去。“鱼呢?”秦六指站起来往黑瘦汉子衣袋里掏。“一定让你藏起来了。”他掏完左边掏右边。“你不说把鱼变到哪去了,就证明这把戏是骗人的。一条小鱼,那还不好藏啊?”秦六指叫嚷道。
“小掌柜的知道这把戏没骗人。”黑瘦汉子含笑看着胡逊。
胡逊沉默地盯视着黑瘦汉子。他已经相信,那条红鲤鱼此刻大概已经回到荷花缸里去了。风波镇上的人开始围攻胡逊,问他鲤鱼到底去哪了。“回它该回的地方去了。”胡逊说。风波镇上的人集体哗然。他们觉得胡逊变得也像个耍把戏的了。
黑瘦汉子回身把搪瓷瓮拎起来,两手捧着,端到胡逊跟前。当一声,一件什么东西落到瓮里,发出有点沉闷又有点清脆的撞击声。耍把戏的黑瘦汉子一翻手把搪瓷瓮扣过来,底朝上。那件东西扑一声掉到地上。
风波镇上的人们都围过来看,以为是那条鱼,却没想到是块黑不溜秋的小铁片。胡逊也看到了,那是一枚扁叶形箭簇,在太阳底下发着乌亮的光。
四
“把他请来。”胡菰蒲对胡逊说。
胡菰蒲站在荷花缸旁边。缸里的鲤鱼每一条他都很熟悉,像熟悉家里的每一个人。在布店寄居了一些日子的那条最活泼的红鲤鱼,因回到伙伴们中间而亢奋不已
胡菰蒲手里拿着那支扁叶形箭簇——刚才他已到后院清点过了,一百八十七支箭簇缺了一支,剩下一百八十六支。他手里的这支当然就是不翼而飞的那一支。
汉子随胡逊走进来,站到胡菰蒲跟前。他们两人隔着荷花缸四目相对。胡菰蒲试图从他脸上身上找到能证明他们过去曾经见过的特征。这世上任何蹊跷事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请到厅堂用茶。”胡菰蒲对汉子说。“请问贵客尊姓?你我可曾见过?”
“胡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汉子端起茶杯来喝一口。“二十年前,县城大戏院门口,有一个魔术班曾在那里演过几场。”
“唔!”胡菰蒲发出一个意思不详的词,像说了一个语气词,又像仅仅是嘘了一口气。他仔细看看汉子那只搁在桌子上的手。它是他的左手,和其他人的左手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它的五根手指似乎不甘寂寞正在抖动。它们轻轻地磕击着桌面上红色的木纹。“就是这些手指,玩了那些把鱼和箭簇变来变去的魔术。”胡菰蒲想。
胡菰蒲慢慢地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个魔术班。他那时候还年轻,有周游世界的野心和想法——胡菰蒲忽然发觉,他儿子胡谦如今不愿意在风波镇呆着,不正像年轻时的他吗。他们胡家总是世代单传,这让年轻时候的胡菰蒲很不满意。他总是想,如果他有个哥哥或者弟弟,他就不必一边向往外面的世界、一边还得时刻惦记着回来接手祖上的产业。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他爹健康长寿,一直精神矍铄,压根儿用不着他。可惜事情不是那样。他爹好好的竟然暴毙,这谁能想到呢。
回想起来,他爹暴毙之前的那几年,正是胡菰蒲过得最无法无天的几年。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死守着祖上的那点产业——到广州去,到上海滩去;创业,干番大的,不更好吗?最不济,在县城也可以啊!胡菰蒲到过他目标中的广州和上海滩,倒也听说过几个福佬的创业故事,可惜他没遇着合适的机会。他给他爹捎信,说打算从头干起,比方在皮鞋店当学徒什么的。最后,胡菰蒲还是游历一番后回到虹上县城。他结识了几个和他差不多品行的人,整天泡在茶馆和戏院里,干些捧角之类的事。
胡菰蒲笑了。二十年前,那个被人把胳膊腿当机械零件一样拆来拆去的少年,长成眼前这个黑脸的高个汉子了。他仔细看看黑瘦汉子的胳膊,记得当年,这两条可怜的胳膊,每天都要被魔术班的班主从肩膀那里卸下来,再拎着转上三百六十度;充分凌迟以后,才被重新装回到肩膀上。嘎嘣!围观的人们似乎就喜欢听脱臼和归臼时骨头摩擦骨头的声响。那孩子遭受的凌迟,这只是其中一种。胡菰蒲记得他还躺在地上,向上支楞着被一层皮包裹着的排骨架,拼命撑住加在它上面的一块铁板、及铁板上站立着的魔术班班主。
“我没想到你还活着。”胡菰蒲说。这是真话。他每天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第二天在戏院门口就看不到那孩子了。虽然那孩子每天都让人发现还活着。
“我命大,”黑瘦汉子说。
“是很命大。”胡菰蒲附和道。他很由衷。“要不是你们班主被杀……我看你迟早要死在他手里。早晚有一天,你那两条胳膊卸下来就再也按不上去了;或者,让铁板把你那排骨架一样的肋骨一根根压断。”
胡菰蒲现在还能想起魔术班主横尸戏院门口的场景。说起来,他最终决定离开县城回到风波镇来,正是因为目睹魔术班主像条死狗一样躺在戏院门前的下水道口。子弹从那家伙额头穿过,钻进脑子里。前面没流多少血,只是弹孔像被挖掉眼珠的眼眶那么吓人;但人们把那家伙翻个个儿,却见他后脑勺的洞有拳头那么大,脑浆和鲜血红红白白地摊了一地。人们在下水道口积满污垢的一个凹槽里,发现滚在那里的弹壳。有人说,是“掌心雷”……
实际上,这么些年,关于魔术班主之死这件事,胡菰蒲从来就没忘记过。因为就在那天,有人说“掌心雷”的时候,他一摸衣兜,发现自己那把小巧精致的被很多人称为“掌心雷”的勃朗宁手枪不见了。
这件事一直折磨着胡菰蒲;他用二十年时间没想明白的一件事,此刻在见到这个黑瘦汉子的时候,一下子想明白了。“当年是你偷了我的手枪。”他说。
黑瘦汉子把那只一直磕击桌面的手抬起来,伸进长衫里。然后,胡菰蒲看到那只他曾经花二十美元辗转托人买到的比利时FN公司生产的勃朗宁——虽然时隔二十年,胡菰蒲还是一眼就把它认了出来。
他颤抖着拿起那支握把上端刻着“FN”两个大写花体字母的M1906勃朗宁:它的套筒左侧刻有两行外文——上面一行是赫斯塔尔国家兵工厂的法文全称,下面一行是英文“Browing’s Patent Depose”。这支只有114mm长、25mm宽的袖珍手枪,当年可是胡菰蒲的至爱,每时每刻都藏在他的衣袋里。如今,历时二十年的它,除了套筒前端略微有点磨损,其它地方保护得还不错。黑色的、美丽的铁。
胡菰蒲眼里落下泪来。就算是那些他在游历途中遇到的女人,也不像这块黑铁这样,让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这么动情。
“一把好枪。”黑瘦汉子说,“6.35mm口径,200ms初速,没想到能把人的脑壳穿出那么大的洞。我看到那个洞的时候也有点害怕。”
“我记得你那时候不到十岁吧?”
“刚好十岁。”
“那可能是因为瘦弱,看起来就显得很小。”
“混江湖的年龄却不小了。我三岁开始,就被他虐待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胡菰蒲擎了擎勃朗宁。“我是说,怎么把它偷到手的?”
“我知道,你白天夜里都把它藏在贴身衣袋里。但我有办法。”
“这么说,你从小就是当魔术师的料喽?但是,被人卸胳膊,那不算魔术吧?”胡菰蒲不无讽刺地说。
“我后来遇到一个真正的魔术大师;姓白,在行里名叫小天白。我跟了他几年。”
“哦。”胡菰蒲看看院里的荷花缸。“你把我的鲤鱼从荷花缸偷到徐二思吃饭的空碗里,把箭簇从后院偷到搪瓷瓮里——这技术是拜小天白师傅所授。看来小天白比那被你一枪穿透脑壳的师傅高明。”胡菰蒲说。
“我自从无意中看到你这把枪,就日思夜想要用它打死他。”
胡菰蒲仔细抚摸这把无意中成为凶器的勃朗宁。“真没想到,我当年只是买了这把枪做防身之用,却被你拿来杀了人。”
“一把枪,是无法决定它肚子里的子弹要射向谁的。拿枪的人才是有决定权的人。”黑瘦汉子慢悠悠地说。
胡菰蒲把目光从勃朗宁上收回来,很认真地看了一眼黑瘦汉子。他这句话不得不让胡菰蒲对他刮目相看。“敢问尊姓大名?”他问。
“在下姓白,单名一个芦苇的芦字。师傅给取的。”
“白芦。”胡菰蒲说,“好名字。我们风波湖边上就生有芦苇。秋天,那里一片白茫茫的枯衰景象;但到了春天,地里又会冒出尖尖的芦尖来。是种不易折服的植物。你师傅看来定是空怀绝学却不得不在这乱世之中随风而荡之人啊。”
“是啊。飘零之物,随风而荡,终化尘土。不及那经过烈火淬炼的铁器,埋藏地下千年却不朽。”
“看来白老板今天是为那些铁器而来,非为这条鲤鱼;也非为一支箭簇。”胡菰蒲微微一笑。
“在下耳闻老爷宝地挖出铁器,故慕名而来。”
“白老板如今在何处高就?”
“在下不才,在县城北边的白龙寺后面开有一家砖瓦厂。”
“那白老板未免来得也太快了。鄙人上午刚挖出铁器,先生下午就从县城赶到这区区之地;或是,白老板早已掐算出今天是铁器出土之日?”
“哪里。在下愚钝,无法洞见未来之事。只是在下恰好上午在鸟窝村有点事情。”
“看来白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
“哪里,小本生意。”
“鄙人不知,我念头岭上挖出的铁器,与白老板的砖瓦厂有何联系?”
“当然有联系。”白芦指指胡菰蒲,“老爷,您瞧瞧自己:脚下踩着青砖地,手里拿着勃朗宁。”
“哈哈!”胡菰蒲由衷地大笑两声。他觉得多日来压在心中的阴霾之气,被眼前这个白老板莫名其妙地缓解了。
“今天出土的这些铁器,埋在地下有千年之久,看来是专奔老爷而来的。如今乱世,看来它们也想有一番作为。”
“白老板有话但说无妨。”胡菰蒲看看西边的院墙。黄昏金色的的光芒从高大的院墙外照进来,把他们俩变成剪影。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着。
“好茶。来日有缘定能再见。”他们又说了好一会儿的话。白芦最后喝了一口茶,抱拳向胡菰蒲告辞。“好枪完璧归赵,望老爷用它杀该杀之人。”
“什么人该杀?什么人又不该杀?”
“老爷清楚。”白芦站起身,白衫挡住斜射而进的夕照。
五
白芦站起身正要告辞的时候,老黄匆匆走进来,附耳对胡菰蒲说:“老爷,角声回来了,就在二道门外。”
“让他进来吧。”胡菰蒲说。
“在下告辞。”白芦缓步走过青砖甬道。他在二道门那里跟韩角声碰着了:他正要跨出二道门,韩角声正要跨进二道门。“如果在下没认错的话,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大刀会北堂主韩角声吧?”
白芦一口气把韩角声的身世道出来。“阁下是谁?”韩角声大感惊讶,他上下打量着这个脸庞的汉子。
“在下不才,县城一家砖瓦厂的小老板。”
胡菰蒲算准了他们二人要在二道门那里擦肩而过,却没想到他们认识。这个武术很了得的韩角声的来历,不是不让胡菰蒲好奇的;但他多年来恪守江湖之道。他重用韩角声,却对他的来历闭口不谈。
“既然二位也是旧识,就请进来,一同坐下把酒叙谈吧!”胡菰蒲扬起声音说。“老黄,吩咐厨房准备酒菜。”
这一晚胡宅大门紧闭,下人只留下一个哑巴厨子。老黄父女俩给厨子打下手。
“爹,声哥真是大刀会堂主?”黄杏儿坐在灶前烧火。
“那还有假?当年他全身都是刀伤,翻山越岭爬到念头岭上。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有来头的。老爷肯定也是这么想。这年月,到处都不太平。韩角声在风波镇呆下就不走了,忠心耿耿地料理老爷的拳房,这一呆就是十年。也算是隐姓埋名啊!”老黄拿一块抹布仔细擦拭端菜的盘子。“大刀会盛行那时候,你还小。那可真是轰动一时啊。可惜没成气候就灭了。”
“那变魔术的到底是谁啊?神神秘秘的。声哥不认识他吗?”黄杏儿坐着一把小马扎,窝着腰。柴禾枯黄的叶子噼里啪啦地发着光,映着杏儿若有所思的脸。从金牛顶下来后,杏儿就常常这样若有所思。但她又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事情。好像什么都想,又好像什么都不想。脑壳里装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想。
“爹也不知道他是谁。连韩角声都不认识他。三岁混江湖;十岁偷了老爷的勃朗宁手枪,把自己师傅给杀了。十岁就敢开枪杀人,也算是个人物。”老黄把盘子擦好了,在一个铜盆子里洗抹布。“他今天是来还老爷那把枪的。算起来时间也过去二十多年了,他还记得老爷,并能找到老爷;那把枪还光亮着呢——我看到了——真是让人称奇啊。”
“这不就是个整天出怪事的年月吗。”黄杏儿想起自己被掳上金牛顶的遭遇。她往灶里又填了一把柴禾,拿一根烧火棍朝里捅一捅,然后拄着烧火棍,出神地望着红红的灶口。“爹,声哥找到少爷了没?”
老黄担忧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跟她说实话。刚才老黄一直在厅堂那里伺候酒饭,把该听的都听个差不多了。包括少爷的事。“找到了。”
“那……早川千春现在和少爷在一起?”
“……是吧。”
“哎呀爹!他们见面后到底是什么情形啊?”杏儿急了。他爹吞吞吐吐的。
“爹也不知道啊!早川千春那么喜欢少爷,肯定是见面以后十分高兴呗!”老黄没敢对杏儿再多说什么。“杏儿啊,咱配不上少爷,以后就别想这事了,啊。再说了,虹城如今到处都是日本人,说不定没几天就打过来了,咱们能不能保住命都很难说呢。”
“日本人占领了虹城,那少爷在虹城……不会有事吧?”
“听韩角声说没事。”老黄又看了一眼杏儿。他考虑要不要告诉杏儿实话。胡谦到虹城起初是投靠太太的一个远房表姐。太太初秋的这个表姐家里开有一间烧肉铺。这表姐却不杀生,一直吃斋念佛,每周日下午都要到白龙寺上香。有个周日的下午,胡谦陪他表姨到白龙寺上香,碰到一小股游击队和一伙日本人,在砖瓦厂北边的乱坟地里打起来了。当时胡谦并不知道到底是谁跟谁在打。黄昏时分,几个身穿中国人衣服的日本人跑到白龙寺,被胡谦稀里糊涂地藏在寺庙一个废弃的灶房里,给救了。没几天,人们就看到胡谦变成一个翻译官,戴着日本人的黄军帽。听说他救的是个刚来到县城的叫荒井原的日本军官。
老实说,就连老黄都不敢相信,胡谦少爷成了中国人嘴里的“汉奸”。但白芦白老板却证实了韩角声打听到的消息。“荒井原刚从日本来,那天也是带着女人到白龙寺上香。那女人不想让白龙寺的和尚看出自己是日本人,所以,荒井原他们就换上了中国人的衣服,还专门从后面的乱坟地绕道去白龙寺。没想到,在乱坟地被一支游击队伏击了。”
胡菰蒲听到这些之后,沉默良久。老黄觉得老爷好像一瞬间老了。“人各有命。”老爷叹了一口气。“我们继续喝酒。”
“人各有命”是什么意思呢。老黄不太明白。
“爹,日本人能打过来吗?”黄杏儿觉得她爹正在走神。她不知道,她爹想的是:胡谦少爷如今正巧做了那个什么荒井原的翻译官,跟早川千春在一起不是更名正言顺了吗?“爹,问您呢,日本人能打过来吗?”杏儿见她爹还在走神,就拿烧火棍捅了一下他的腿。
“谁知道呢。我看能。听韩角声说,他进城的时候,让日本人盘问了半天。日本人穿着厚厚的靴子,端着闪亮的刺刀,咔嚓咔嚓地踩着街道。人们老远听到了,就都躲起来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跑啊?”
“傻丫头,往哪跑啊?该在工厂商铺里做工的还得做工。要不然,拿什么吃饭养家?再说了,他们又不像咱们,可以往金牛顶跑。”老黄思忖着。“金牛顶虽说是土匪的地盘……让土匪杀了总比让日本人杀了好。”
老黄把一壶刚烧好的老黄酒放在托盘上,端了出去。他看到老爷和韩角声、白芦三人围着桌子坐着,正在说着什么。好像还是关于日本人的话题。“老爷,日本人能打到风波镇来吗?”老黄问。
“差不多。日本人正在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逐步扩张;而风波镇和麦县毗邻,是他们进军麦县的必经之地。”白芦说。“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风波镇在虹城和麦县之间;所以,风波镇是军事要地。”
“白老板分析得没错。”胡菰蒲跟另外二人碰了一下杯。老黄酒在舌尖上散发出淡淡的谷物的苦香。“今天,念头岭上挖出兵器,这足以说明咱们风波镇历史上就是战争之地。”
“老爷,您的意思是,咱们风波镇要打仗了?”老黄吓得差点把手里的托盘掉到地上。“谁和谁打?”他补充道。
“老黄,我欠过耳风二十杆枪。”韩角声揉着他脸上的一道刀疤。“我答应他,两个月之内想办法弄给他。这就是杏儿现在能在灶房里烧着火和你说话的条件。”
“我知道,你有办法把杏儿带下山来。”老黄恭维韩角声。“不过,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韩角声笑道。
六
晚上十点多钟光景,胡菰蒲和韩角声送白芦出门。白芦谢绝胡菰蒲的挽留,坚持连夜赶回虹上县城。“天亮差不多就到了,正好赶上开城门。这年月不太平,鄙人实在是放心不下那小本经营的砖瓦厂啊。不光是日本人,就连伪军也隔三差五就去骚扰一番。”
胡菰蒲抬起胳膊,要对白芦拱手告辞;两只拳头刚抱在一起,还没说话,疯女人从暗影里忽然现身,两手拇指食指组成倒八字的形状,嘴里模拟开枪扫射的声音。“哒哒哒!”
“鬼一样。”胡菰蒲说。
“老爷,胡逊说这几天她经常这样。莫不是又在预言什么事情。”老黄说。
“疯话而已,当不得真。”胡菰蒲说,“老黄,把她送回家睡觉去。深更半夜满街乱跑,不安全。”胡菰蒲看着老黄和疯女人的背影,转回头对白芦说,“她就听老黄的话。要不是疯疯癫癫的,我看她跟老黄倒是般配。”
白芦凝视着疯女人的背影。“胡老爷,您还记得当年在戏院唱戏的一个外乡戏班子吗?”
“那时候外乡来卖艺的太多了。”胡菰蒲说。
“有个艺名叫小花梨的,老爷想起没?脸上长着一些很可爱的小雀斑?”
“忘了,”胡菰蒲说,“我们那时候听的戏、看的角儿太多了。”
“我觉得刚才那疯女人跟当年的小花梨有些神似。老爷觉得呢?”
“是吗?我没觉出来。”
“夜深了,老爷请回吧。在下以后少不得还会来叨扰老爷。虹城一旦无法落脚,还指望老爷赏口饭吃呢。”
“风波镇随时欢迎白老板。”胡菰蒲再次把两只拳头抱在一起,跟白芦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