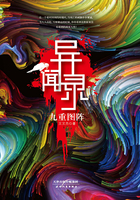一
七月念头岭上的风,吹过大大小小的树木,发出阵阵呜鸣。黄杏儿在黄昏时分醒来,她对自己说:黄杏儿,时候到了。这场睡眠好得让她不忍醒来。没有梦,没有杂音。让她误以为自己死了,到了阴间。她拧了一把脸腮。
太阳的光线从落日街照射进来,穿过南墙上的小窗户。黄杏儿慢吞吞地坐起来,喝了一口水。然后她迈出门,回身把门轻轻带上。走上八步,她停下,朝二道门里看了看。荷花缸里盛开着荷花。她朝东屏门里看了看,听了听。厨房里静悄悄的。以往这个时候,下人们该在里面干活了;说笑,打闹。胡家用一片不可思议的沉默,送走了二十岁的黄杏儿。
太太初秋在厅堂的窗户前站着,她看到黄杏儿瘦小的身影在二道门口轻飘飘地闪过。“她走了。”初秋回头对坐在太师椅上的胡菰蒲说。
“走吧。人要走什么路,老天爷早给定好了。”胡菰蒲喝了一口茶,听到自己女人饮泣了两声。“老黄呢?”他问。
“在自己房里呆着。”初秋叹了一口气说,“我去吩咐下人准备晚饭吧。”
“多准备点,有客人要来。”胡菰蒲看看墙上的一只钟。
“谁要来?”初秋回头问。
“马一传。”胡菰蒲微微一笑。
他一定是猜到马一传要来。初秋将信将疑。这一天下来,她觉得所有人都不正常了。初秋走出厅堂,穿过青砖院子,走出二道门。她站在照壁前犹豫了一下,考虑是不是走到落日街上,看看黄杏儿走远了没有。但她轻轻叹口气,转身走进东屏门。哑巴厨子正在闷头干活。没有黄杏儿和老黄在眼前晃来晃去,哑巴也干得挺没劲。其他几个一到做饭时间就跑来玩闹的下人也都不知跑哪去了,厨房显得格外冷清。鸽子从瓦片上飞下来,在院子里觅食。哑巴扔出一把玉米粒。
初秋今天也没心情过问别的,她认为这是极不平常的一天,大家都还在恐慌中。厨子掀开锅盖,露出一锅白胖胖的包子。“再添几个菜吧,一会儿有客人来。”初秋说。她坐在灶前,对厨子说:“没事,你忙你的,我就是坐一会儿。”她记得经常看到黄杏儿坐在灶前,勾着头,用一根烧火棍在灶膛里拨拉柴火。把灶膛拨得红红的。
大门吱呀一声,有人进来了。初秋走出厨房,看到一个伙计从外面走进来。“太太,”伙计看到初秋,赶忙停下脚步。“马镇长来了。”
初秋想,老爷还真是神机妙算呢。“我去告诉老爷,你在这候着。”
“哼,我就知道他要来。”胡菰蒲鼻子哼了一声。他站起身,拄起阴沉木手杖。“跟我一起到大门口去迎接。”他说。
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胡菰蒲和马一传互相拱手施礼,热情万丈。“镇长来得正好,刚听内人说,厨子包了新鲜的菜豆包子。我家厨子别看不会说话,厨艺可是一流。”胡菰蒲亲热地把马一传让进门。
“胡宅就是胡宅,家大业大心胸也大。今天的风波镇,恐怕得有多数人家是冷锅冷灶,食不甘味啊。你胡兄家,却仍然在气定神闲地吃包子。有胆有识,佩服,佩服!”马一传话藏机锋,猛拍胡菰蒲的马屁。“我家也是冷锅冷灶,没人做饭。我那婆娘正哭哭啼啼,收拾她那几件破衣烂衫,准备跑呢。我这肚子饿得空落落的,就想到胡兄你这里,看看有没有饭可蹭。嘿,还真是让我赶上了。”
“哦。嫂夫人也真是,收拾什么行李。天塌下来,有你马镇长顶着呢。有你在,谁敢来犯!”胡菰蒲请马一传在太师椅上坐下。“你我哥俩先喝杯茶,厨子马上就摆饭上来了。”
“有你胡老爷在风波镇坐镇,我马一传还怕什么呢。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开伙。这么下去怎么得了!人不能不吃饭哪。您说是不是?”马一传坐下喝了一口茶。“好茶。您说,这好日子还能过几天?”
“过几天,还不是您镇长说了算?”胡菰蒲笑笑。“这整个镇子都是你马镇长的。”
“哪里,我只是一介不称职的父母官。是你胡兄不接这苦差事,才把我无才无德的马某推到这个位置上。唉,整天是操碎了心。大家要是都像胡兄这样安分守己,我也就不用操什么心了。”
“呵呵,马兄是在批评我胡菰蒲给镇上添乱呢,我听得出来。不过,马兄可是有头脑的人,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旁人那些小道消息左右不了你。”胡菰蒲稳稳当当地喝了一口茶,很享受地吞下去。“今天早上,鬼子听信秦六指的话,跑到我胡家后院来搜什么武器。我胡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他们的武器藏在自家后院里呀!你说是不是?”
“那是。胡兄就是要藏,也有别的地方可藏,还用藏在后院吗?”马一传也学胡菰蒲,真话当成笑话说。“再说了,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家伙是祸患?老实说,胡兄,今天早上我可真是为你捏了两把汗哪!你说,要是那些家伙真出现在你家,咱们全镇人性命不保是小事,胡兄你能担得起那千古骂名吗?我马某相信,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干那样的傻事。”
“马兄说笑了,千古骂名也不是那么好赚的。”胡菰蒲指着马一传,仰头一笑。
哑巴把菜和包子端上来。马一传捏起一只包子,赞不绝口。“我家厨子要是有您家厨子一半的手艺,我马某人就哪儿的饭也不吃了。你胡兄的饭我也不吃。”
“马镇长真是见外。你要是喜欢这厨子,胡某跟他说说,让他去给您家当厨子。咱哥俩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你这句话,马某就很知足了。好,今天我是厚着脸皮上门讨吃的,就不客气了。何况,吃了今晚,还不知明天这张嘴巴是不是还好好地呆在脑袋上。”马一传咬了一口包子。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明天你的嘴巴不在脑袋上呆着,还能跑到屁股上不成?”胡菰蒲说。
“骂人!骂人是吧?”马一传腾出一根手指,指着胡菰蒲。“明天要是我的嘴巴跑到屁股上了,我可是要找你胡兄算账的。”马一传见胡菰蒲总是不按照套路来,就索性把话挑明了。“你们家黄杏儿呢?怎么不见她来端茶倒水?”
胡菰蒲也拿起一只包子。“马镇长当我是外人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去她该去的地方了。今天可是伺候不了咱老哥俩吃饭啦。”他停下话头,咬了一口包子。“嗯,味道不错,咸淡适中。马兄觉得呢?对不对口味?”
“这还用问?”马一传咽下一口饭,喉咙里鼓突起一个结。
二
马一传有口无心地吃了几口饭。告辞出门的时候,刚迈出二道门,就让一个影子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他定定神一看,是韩角声。“哎哟声爷,把我的胆都快吓破了。”
韩角声拱手让路。“镇长胆子这么小?”他调侃道。
“让日本人给吓得呗。”马一传摇摇头,一脸苦笑。“刀枪棍棒,我马某人还真没见过今天这阵势。马某人不像声爷你见多识广,自然就胆子小喽。”
“马镇长太谦虚了,我们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受你的庇佑呢。”
“这个,我马某人可不敢当啊。何况镇子这么大,人心隔肚皮。若是有人不顾全镇人的性命,一味斗狠逞强,我马某也无可奈何啊。你说是不是。”马一传皱巴着脸。“好了,我也该回去了。这日子,过一天是一天喽。”
两个保安队员先是把脑袋探出大门,左右转着看了看。然后,几个人把马一传团团围在中间,戒备森严地走上落日街,穿过小胡同,拐到落霞街上去了。韩角声在后头看那几个人虚张声势的样子,忍不住一个劲想笑。“十秒钟我就能把那几人撂倒。”他对老黄说。老黄刚从自己屋里出来。他胸闷得慌,身上没力气,刚从一个噩梦里醒过来。
“角声,我梦见杏儿她娘在生杏儿。两个都没活。树下一摊血。”
韩角声看看老黄。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早上若是照他的想法,当时就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但老爷制止了他。在风波镇上,韩角声谁的话都可以不听,老爷的话却从来没有不听过。当然,韩角声并不盲从。和老爷在一块十年,两人在多数事情上彼此心意相通;韩角声知道老爷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有一定的道理。“杏儿呢?”他问。
“走了。”老黄说。“去就去吧。多少妇女让日本人当街强奸。杏儿比她们强多了。”老黄抬眼看看韩角声。
“你这么想就对了,”韩角声说,“老黄,你放心,我一定会为杏儿讨回公道。但这事得从长计议。鲁莽行事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会给风波镇惹来杀身大祸。行了,老黄,打起精神,赶紧去给老爷说一声,厂里来人了。”
老黄一整天都在屋里呆着。直到傍晚时分,杏儿关上门走了以后,他才流下几行窝囊的泪水。身上那根绷了一天的弦终于断开,人立马蔫巴了,一头倒在炕上,直奔那个噩梦去了。醒来以后,天色已是大黑,老黄有些愧悔。老爷和太太一天都没喊自己。听到厂里来人,老黄马上回到正常角色中。他掠过月影摇曳的青砖院子。厅堂里还亮着灯,老爷在太师椅上坐着。“是老黄吗?”老爷问。
片刻之后,胡菰蒲和白芦站在后院的凉房里。韩角声和老黄绕着凉房,前前后后地巡查。胡菰蒲拿着一盏昏暗的灯。他和白老板进入凉房后不久,这点昏暗的亮光就消失了。
“角声,这房里一定有什么暗道机关!”老黄恍然大悟。
“你才猜到啊老黄?”韩角声讥笑道。“真是迟钝。”
“这么多年了,老爷一直都不待见这间房,有东西也不往里放,都成蜘蛛窝了。我只当这是一间闲房,没想到居然暗藏机关啊!老爷瞒得可真严实。”老黄小声说。
“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老爷就是老爷!服了吧?”韩角声说,“这世上不是人人都能当老爷的。”
两人转到凉房后窗外的废园子里。这个园子在后罩房的后面,是整个胡宅最偏僻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来。几棵白杨树和野花野草,在园子里胡乱生长。“秦六指就是翻过这道院墙溜进来的,”老黄看了看院墙。“这么高,他也能翻进来。咱们是不是该再把墙加加高了?要不,栽上玻璃片或者铁蒺藜。”
“老黄,这些办法都没用。也就只能防防秦六指这号的。像过耳风那样飞檐走壁的高人,能怕你的什么玻璃片、铁蒺藜?”
胡菰蒲和白老板正在废园子下面大概四米深的密室里站着。胡菰蒲把手里的灯抬高,照亮了一溜排放的几口大大小小的木箱子。“都在这里了,”胡菰蒲说。
“咱们现在正需要这些铁家伙。”白老板掀开一口箱子。“这里安全吗?”
“目前为止很安全。秦六指偷偷翻过院墙,从后窗看到过这些箱子。不过他没看到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及时地掉了包。”胡菰蒲说。
“荒井原是不会这么就算了的,一定要多加提防。”
“对。荒井原看上了老黄的闺女黄杏儿,让她落日前到炮楼去。杏儿傍晚时分离开了胡宅。傍晚时分,我把下人都打发出去了,为的就是让杏儿自己离开。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留在风波镇,只怕凶多吉少。她多半不会去炮楼,我了解她。她不去,荒井原会更快地卷土重来。组织上对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你猜对了。据可靠消息,黄杏儿没去炮楼。”白老板说。“组织上要求你们做好战斗准备。虽然截获了这些武器,但还远远不够。所以要发动群众力量,利用地理优势,尽最大力量保住风波镇,阻止日本人南侵。”
在耳房旁边的过道里,胡菰蒲对白老板提出一个请求:如果杏儿去了砖瓦厂,请白老板代为照顾。“那是自然,”白老板说,“杏儿跟我去过一次砖瓦厂,那里也算是她的另一个家;何况,她和白鸥千春都处得不错。您觉得她会去砖瓦厂吗?”
胡菰蒲低头沉吟片刻。“除了砖瓦厂,我想不到她会去别的什么地方。”
三
傍晚时分,风波湖里的芦苇染上西天的红霞,倒映在逐渐暗灰的湖面上。没有风,船纹丝不动。胡逊撑起船桨,把船划到芦苇荡边。他把脑袋钻出芦苇荡,再一次朝岸边张望。近处的小木屋、稍远处的风波镇,在这个黄昏都陷入出奇的沉默。早上日本人来那一趟所制造的恐慌,把全镇人都陷入闭门不出的境况。只有不谙世事的狗,偶尔发出几声疑惑的闷叫。
年轻的布店小掌柜胡逊,整个人像拉满弓的弦,随时准备把船朝浩淼的风波湖射出去。他越过芦苇丛,凝望风波镇的天空。用不了多久,那天空就不属于他了。
这傻里傻气的年轻人,一直在芦苇荡里飘了一下午。直到暮色像张黑布徐徐朝湖面落下,他才疑窦重重地把船划回岸边。这年轻人惶里惶恐地离开水面,站到结实的地面上。他看到疯女人坐在敞开的小木屋里,朝他张望。
胡逊走到小木屋里。疯女人打着手势,让他回镇上去。疯女人的意思胡逊看明白了:我早就知道你走不成。
在风波镇上,除了老黄,胡逊跟疯女人最亲。其实,胡菰蒲对胡逊也很不错,但不知怎么回事,胡逊跟他就是亲不起来。夜色落下来了,胡逊离开小木屋回镇上去。
胡逊走到落日街上。在布店门口,他看到秦腊八坐在里面,朝着大街发呆。“胡逊!”秦腊八噌地站起来。“你一个下午跑哪去了?”秦腊八的嗓音哭唧唧的。
“看到杏儿了没?”胡逊顾不得别的。
“杏儿杏儿,你就知道杏儿。”秦腊八气呼呼的。“没看见。她都跟我说过了,她不可能和你好。”
“什么时候说的?”胡逊本来想脚底抹油溜走,一听这话,就迈腿进去了。
“不告诉你。”秦腊八看了看胡逊。“你陪我喝杯酒,我就告诉你。”她转身神奇地从椅子后面拎起一瓶酒。“我偷我爹的。你把门关上,别让他找着我。”
为了探听杏儿的下落,胡逊顾不得自己没酒量,急三火四地关了门,扬起脖子喝下一杯老白干。然后又喝下一杯。他眼前的东西开始晃动,两条腿站不住,扑通坐到地上。“你快说,杏儿都跟你说什么了?”胡逊感到自己的舌头也不好用了。
秦腊八也坐到地上,拿着酒瓶子,往嘴里灌。“她说,她不喜欢你,不能和你好。她说,让我和你好。”
“你胡说,”胡逊软塌塌的,舌头木呆呆地在口腔里躺着,像要睡过去。“杏儿答应和我一起离开风波镇。我等她一下午了,这就去找她。”他站了一下,没站起来。“扶我一把。”他说。
“嘿。”秦腊八也有些醉了,手指着胡逊傻笑。“她骗你,你就当真了。她把你支开,自己一个人跑啦。”
“跑哪了?她真去炮楼了?”
“她宁愿跟日本人好,也不跟你好。告诉你吧胡逊,只有我对你好。”
胡逊不信,但他站不起来,眼皮子也下沉得厉害。我得去找杏儿,他想。他又试了试,还是站不起来。“腊八,我站不起来了,你扶我一把。”他说。
胡逊记不清楚从那以后发生的事了。天还没大亮,布店的门发出响动,门上的铁环呱嗒拍打了几下门板。胡逊睁开眼,发现一大块粉色绸缎缠在身上。他解开那块绸子,又发现更要命的事情:秦腊八也在绸子下面。“秦腊八!”他叫了一声,嗓子抖颤起来。“你把我怎么了?”
秦腊八缓缓地睁开眼,看看他又看看自己。“什么叫我把你怎么了?我还想问你把我怎么了呢!”她扯过另一块布盖着自己,呜呜地哭起来。
“让我想想。”胡逊捶打着发胀的头。“咱俩都喝醉了。酒后乱性。完了。我不是处男了!”
“我还不是处女了呢!”秦腊八哭得又伤心又幸福。“你到底能不能喝酒啊?没酒量还偏要喝!逞什么能。”
胡逊快手快脚地找衣服往身上套。“我得去找杏儿,天都快亮了。”
“你去,你去!”秦腊八恨恨地撕扯着一块布。“杏儿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还能理你啊?”
“嘘!”胡逊停下来,听听门外的动静。“你听到声音没?”他觉得门外好像有人。
“天快亮了,落日街又不是你家的,谁不能在上面走路啊?”秦腊八没好气地说。
胡逊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轻轻打开一条缝,把脑袋伸出去朝外看。他感到像是徐二思一闪身拐到旁边的屋角后面了。胡逊走出去,掩好门,往胡宅走。一颗小石子落在他脚旁,弹跳一下,趴在落日街上不动了。胡逊抬起头,看到韩角声坐在拳房西厢房的瓦片上,朝东看。身边站着两只哑巴养的灰鸽子。
“上来吧,”韩角声说。他看到胡逊举棋不定,就补充道:“她不在胡宅。”
胡逊推开拳房的门,走到院子里。天仍未大亮,竹梯子上蒙着一层露汽。胡逊踩着梯子爬上房顶,坐在韩角声旁边。瓦片上也有露水,湿乎乎的。胡逊看着黎明快要到来的风波镇,又扭头去看鸟窝村那像一截粗壮的烟囱似的炮楼。
“她也不在那里。”韩角声说。
“声哥,你能说句痛快点的吗?她不在胡宅,不在炮楼,那在哪?”胡逊揪掉一根从瓦楞里长出的狗尾巴草。
“在那。”韩角声仍旧看着东方。远处的金牛顶上空现出一缕亮光,慢慢地朝更多的地方洇开。
“声哥,你逗我呢?到底是哪啊?”胡逊着急了。
“金牛顶啊!真笨。”韩角声扭头看看胡逊,“怪不得杏儿不喜欢你。”
“金牛顶?不会吧?你怎么知道?”胡逊根本不相信。
“猜的。”韩角声淡淡一笑。“要不咱俩打赌。你要是输了,给我做身衣裳;我要是输了,教你练几招。”
“不打。每次打赌都是我输。”胡逊眺望着金牛顶,狐疑得要命。“你为什么这么猜?我觉得你猜得不对。”
四
七月的杏树只剩下叶子。黄杏儿抬头仰望那棵叶子浓密的杏树,恍惚觉得自己回到了和胡逊一起摘杏儿的那天下午。风从岭上刮下来,带着热烘烘的夏天的味道。杏儿觉得有点困,还有点倦,有点乏。她背靠树干坐在地上,竟然打起盹来。
杏儿在短暂的打盹中做了一个梦:一个半人半兽的东西,从岭上呼啸着掠下,一把抓住她湖蓝色的小褂。她像风一样飞到空中,飘飘悠悠地飞到念头岭上。她看到风波湖闹起大水,水像一张白色的被单,盖住风波镇的房屋和街道。接着那抓住她的半人半兽的东西,忽然松开爪子,撒手不管她,把她像扔一块石头似的扔回尘世。
杏儿啊地大叫一声,掉到杏树底下。她睁开眼,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刚才是做了个噩梦。她搞不懂那半人半兽的东西是何寓意,是要拯救她还是毁灭她。不管怎么说,风波镇她是回不去了。这个梦,意味着她和风波镇彼此的背叛和决裂。
黄杏儿离开杏树,朝念头岭攀登。她看到风波镇上空浮起一层炊烟。炊烟潦草,带着一股茫然无措的愁绪。她还看到了鸟窝村的炮楼,那粗壮的东西。
夜色落下来的时候,杏儿蹚过了金牛河。今年夏天雨水少,金牛河的水势不是很旺。她踩着一根倒伏在水面上的树干,到达对岸,像走独木桥一样。站在对岸,杏儿回身看看念头岭。那道岭已经把风波镇挡住了。她转过身,朝金牛顶走去。
杏儿一闭上眼,就能看到自己当初被扛着上山的往事。她觉得,刚才过河的那根独木,和上次是同一根。但不知出了什么鬼,还没走两步,杏儿就拿不准该怎么走了。她觉得,也许是时辰不对:夜色遮盖了她的记忆。
不管怎么说,杏儿不愿回头了。她想,反正只管朝山上走就是了。只要大体的方位对,就没问题。她记得上次是先从西坡往上爬,然后拐到南坡上。只是夜越来越浓密,夜风越来越响地刮过树梢。杏儿有点后悔选了这么个时候闯入金牛顶:午后就动身,说不定现在已经爬上去了。
杏儿只爬了一刻钟,就意识到面临的凶险:山势陡峭,大石耸立;厚厚的落叶底下,藏着深深的沟坑。快到十五了,或许已经是十五了,还好,有不算明亮的月光。
野兽发出高高低低的嗥叫。主要是狼。她放轻声音,以免惊动那些夜里还不睡觉的畜生。即便如此,仍有一只黄鼠狼拖着尾巴,从杏儿腿边窜过。杏儿让这东西吓得一屁股坐到坡上,朝下出溜了很远才停住。那东西亮着两只闪闪的小眼睛,蹲在坡上看着她。镇上老人都管黄鼠狼叫黄皮子,杏儿没少听说过黄皮子的故事。她身上生起鸡皮疙瘩。黄皮子不离开,也不近前,只是蹲在那里,眨巴着小眼看着她。
“你走开。”她对黄皮子说。黄皮子眨一下眼,还真听话,掉头朝坡上跑。跑了两步,又停住了,扭回身,继续像刚才那样看着杏儿。“莫非你是在等我?”杏儿说。
有了黄皮子在前面带路,杏儿避开了很多深坑。半夜时分,黄皮子把杏儿带到一个小山洞里。小山洞隐在两株柞树后面。柞树矮壮繁盛, 枝条扑啦啦地长满叶子,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洞口。黄皮子拱开一个小洞先钻进去。杏儿蹲下身,借着月光,拨开枝条。洞口赫然敞亮了。杏儿想,半夜了,干脆进去睡上一觉。她钻进洞口。枝条在身后无声地闭合了。
“这是你的家?”杏儿站在洞里惊讶地四处打量。山洞不大也不小,有她在胡宅那间房的一半大。而且,黄皮子太神了,洞里归置得很像样子:吃饭是在一块桌子形状的石头上,上面扔着一只野兔;睡觉是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铺着一张兽皮。黄皮子蹲在一块正对着洞口的石头上,仿佛山大王。
杏儿在兽皮上坐下。她两条腿肿胀不堪。要紧的还有肚子,一阵一阵向她传递着饥饿的信号。“我姓黄,你也姓黄,咱俩是一家人。我就叫你黄大哥了。我要吃你的兔子。”杏儿从身上摸出一盒火柴。她没带干粮,倒是带了一盒火柴。
洞里有一处石壁,从缝里潺潺地渗着山泉水。“你这里真是个好地方。”杏儿一边就着泉水剥兔子皮,一边对黄皮子说。她钻出去拣了一些树枝进来,生起火烤兔子。金牛顶上高高低低地响着野狼的叫声。
五
第二天,接近晌午,黄杏儿遇到了土匪。她逐一打量着那几个露出胳膊和脚脖子的小土匪,依稀认出其中一人。“我认识你。两个多月前,你看押过我。带我去见过耳风。”她说。
“我们得把你绑了。”小土匪说。
“绑吧。”杏儿满不在乎地站在那里。一根绳子从她脖颈上绕过,和两只手绑在一起。“你叫什么?”她问。
“小运气。”小土匪说。他端量一下杏儿。“我们风爷上次不是放了你吗,怎么又上山来了?
“金牛顶又不是你们家风爷的,谁不能上啊?”杏儿白了一眼小运气。“两个多月不见,你长高了。多大了?”
“十八了。”小运气挺挺胸脯。
旁边一个小土匪打趣道:“肋骨快挺断了。”
杏儿忍不住笑出声来。她抬头看看天空,觉得金牛顶上的天格外地清澈。
差不多一个时辰过去后,杏儿被小运气几人带到金牛顶的匪窝。黄杏儿很认真地看看这些上次她没及细看的房屋。“关我那间房在哪?”她问小运气。
“那间。”小运气指给她看。“不过现在,你得跟我们去见风爷。身上有没有家伙?咱兄弟是爷们儿,不好搜你的身。要是有的话,趁早自己交出来。”
“我一个女孩家,有什么家伙?再说了,你们风爷本事那么厉害,还怕我带家伙?”杏儿感到小运气十分有趣,禁不住想逗弄他一番。“你过来。”她示意小运气把耳朵凑过来。“告诉你,我是来刺杀你们家风爷的。有人出了大价钱,买你们家风爷的人头。我可是有绝世武功的。上次只不过是来踩踩点。”
小运气将信将疑地打量着杏儿。“是不是真的啊?什么功夫?比我们风爷还厉害?我得给你把绳子绑绑紧。”
小运气把杏儿身上的绳子又绑了绑。杏儿扭头四处打量,小运气也警惕地四处看。“你找什么?”他问。
“我黄大哥。”杏儿说。
小运气哗啦啦摆弄枪栓。“还有同伙啊?”他说。
“你真可爱,”杏儿说。“快走吧,逗你呢。”
小运气两人把杏儿带到一栋大房子跟前。杏儿比较了一下,发现这是金牛顶上最阔大的一栋房子,门口毫无规则地摞着几条石板当台阶,台阶上面是大敞着的宽宽的门洞,似乎就是为了让人看清院子里的一把大铡刀,还有厅堂里的几把椅子。杏儿看看里面,扭头问小运气:“正对着大门口的那把椅子,是你们风大当家坐的吧?这一大早,他不坐在上面早朝,跑哪去了?”
“练功夫去了。我们风大当家的行事潇洒,不是每天都上朝。”
“没规矩。一群散兵游勇。”黄杏儿撇撇嘴,看看厅堂上面那块黑漆剥落的牌匾。“还聚义厅呢。你们以为自己是梁山好汉啊?我看叫聚匪厅还差不多。”
小运气和另外一个小土匪商量如何处置黄杏儿。最后决定把她绑在院子里。“这棵树是咱们专门用来绑人的。”小运气边把杏儿往树上绑,边给她介绍山上的规矩。“一般捉来探子或是流氓强盗,我们就把他绑在这棵大树上,风大当家的和另外几位当家的都坐在聚义厅里。等把那家伙解到厅里审问一番,再出来,八成就是要冲着这把大铡刀来了。看到这把大铡刀了吧,不知道多少人的脑袋让这家伙剁下来了。上面还有血呢,看到没?”
杏儿看到铡刀上果然有血迹。她胃里一阵恶心,差点吐出来。但她把那口恶心咽了回去。“我是有武功的!就这破绳子能绑得了我?攒口小气就绷断了!老老实实让你绑,是给你面子,哼!我要见的是你们风大当家的。不拿到他的人头,我是不会离开金牛顶的。快去找他,就说我黄杏儿又回来了。”
小运气将信将疑地上下打量黄杏儿,不敢轻敌,就跑出门去,喊来另外两个小土匪。“你们三人好好看着她,拿枪指着。你,指着她的头;你,负责胸口;你,负责腿。我去找风大当家。”
三支枪马上各就各位,牢牢咬住黄杏儿身上致命的部位。黄杏儿感到奇怪,跑到匪窝里来,她反倒心情变好了。小运气把她面朝西绑在大树上,她朝西看了看,看不到风波镇。一道墙挡住了她的视线。她抬头看了看天,天上静静地悬浮着几朵云彩。她不知道风波镇的上空此刻是什么样子。
过了一碗茶的工夫,小运气回来了。过耳风走在小运气后面;在他后面,跟着另外几个当家的。黄杏儿一眼认出当初扛她上山的刀疤脸。过耳风手里提着一杆枪,新锃锃的。“你们风波镇的枪真好使,”他说。
“大当家说得没错。”小运气抬起胳膊,把一只野鸡提给黄杏儿看。“对眼穿。”他补充道。
“不就是对眼穿吗。整天炫耀。”黄杏儿说。
“那你打个对眼穿给咱爷们儿瞧瞧?”刀疤脸说。
“报告风大当家的,”小运气两条腿往中间一并。“她说她会绝世武功,是来要您的人头的。有人花钱让她干的。”
“呵呵,是吗?”过耳风摸摸自己的头,绕着大树转了一圈,返回到黄杏儿跟前。“我这颗头值多少大洋?”
“不告诉你。”黄杏儿白他一眼。她发现他好像和上次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又说不上来。
过耳风提起手里的枪,掉转过来,把枪柄送给黄杏儿。“知道怎么使吧?给你五分钟时间。五分钟过后,这颗项上人头,恕我风爷就不奉送了。”过耳风转向小运气,说:“给她松绑。”
“风大当家的,她还有同伙,姓黄。”小运气不无担心地说。
“啰嗦。”过耳风瞪一眼小运气。小运气扔下手里的野鸡,过来给黄杏儿松绑。野鸡还没死利索,翅膀扑扇了一下。
六
一九三八年,黄杏儿神奇地打中了一只雕。
她拿着那杆崭新的三八大盖,对准过耳风的胸口。金牛顶上出奇地安静,只等着黄杏儿的旷世一枪。“老二,我要是死了,金牛顶就交给你了。”过耳风对刀疤脸说。
杏儿觉得金牛顶上的时间过得也跟风波镇不同。五分钟在金牛顶显得过于漫长。她根本不会开枪。山风在金牛顶上徐徐地吹着,黄杏儿身上却渗出汗粒。她横下心,两眼一闭,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出去了,她觉得自己手腕子一阵发麻。手一松,枪没了。再睁开眼,发现枪在过耳风手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额头。
杏儿第二次被可恶的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额头。她想起上次在金牛顶的最后一夜,枪口对准额头后,把她带入那种不可名状的黑暗维度之中。看样子这次要死了。她想,死在金牛顶,总好过死在风波镇。或是鸟窝村的炮楼里。至少金牛顶空气新鲜一点。
“风大当家的,她打中了一只花雕!”
小运气的叫声打破了金牛顶上的寂静。过耳风的枪口离开了她的额头。大家都跟着过耳风去看花雕。
那可怜的小家伙躺在地上,已经死绝了,露着黄灰色的胸腹。蓝灰色的太阳穴流出一道细细的血线。
“对眼穿,大当家的!”又是小运气的叫声。
“还真是对眼穿。”过耳风拎起花雕看了看,又把它扔到地上。他把枪丢给小运气,两只手拍了拍。花雕的一片羽毛轻飘飘地落下,在风里飞舞。“看来真是身负绝世武功,枪法这么准。”过耳风踱过来,上下打量黄杏儿。
“不就是对眼穿吗,谁不会呀。”黄杏儿撇撇嘴。她觉得特别好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她根本不会开枪。
“说吧,到我们金牛顶来,目的是什么?”过耳风问。
“你们金牛顶?谁说金牛顶是你们的?那是我们风波镇的!既然是我们风波镇的,我就自然有权利来。我就是来玩的。打打猎。怎么了,不许啊?”
“你这小丫头,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谁敢这么跟风爷说话?”刀疤脸插话说。
过耳风朝刀疤脸摆摆手。“山上没女人,也怪冷清的。小运气,把她带到上回住过的房子里去。”
“几个岗哨?”小运气问。
“不用。”过耳风说。“老二老三老四,咱们继续打猎去。”
黄杏儿觉得自己掉入一个梦里了。太神奇了。她坐在那铺灰扑扑的炕上,端详着自己的右手。她想把食指勾起来,复习一下是怎么扣动扳机的,却没找到一点感觉。“小运气,我真打中了那只花雕?”
“当然了,我亲眼看见的。你真有武功啊?真看不出来。”小运气也凑过来端详她的手。
“小运气,你过来。”黄杏儿让小运气把耳朵凑过来。“告诉你啊,其实我不会开枪。刚才我就是乱开了一下。”
“乱开都能打那么准?有如神助啊。不过,你也太大胆了。万一打中我们风大当家的,你就等着死无全尸吧。”小运气直起腰来,拍拍胸口,说:“我们风大当家的比你还胆大,他就不怕你真把他打死啊?”
“其实我根本没朝他打。我是朝天打的。你们风大当家的知道我不会朝他打。”
“为什么呀?”小运气好奇极了。
“不为什么。”黄杏儿用左手揉着右手腕。“有剪刀没?我要把这被子拆开洗洗,太脏了。”
“你打算住下来不走了?”小运气更好奇了。
“当然了。不欢迎啊?”
“那你的黄大哥呢?”
“你过来。”杏儿又朝小运气勾勾手。“告诉你吧,黄大哥是一只黄皮子。是它给我带路,我才没摔死的。我跟你说的这些,都不许跟你们风当家的说。”
“那,你到底是不是来杀我们风当家的?”
“我杀他干吗。他又没惹我。”杏儿说。她把小运气搞得一愣一愣,摸不着头脑。小运气找来剪子,她三下两下拆开被子,皱着鼻头,把黑油油的被面被里都泡到那只藏污纳垢的黄铜脸盆里。“小运气,陪我去摘点野花好不好?屋里太冷清了。”
小运气摸摸头皮。杏儿说:“你们风当家的说了,不安排岗哨。这就是把我当客人待呢,你怕什么。再说了,你不是扛着枪吗。”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黄杏儿再一次站在金牛顶的九丈崖上。她看到崖下云蒸霞蔚,一道彩虹凌空飞跨;尘世间的纷纷扰扰,一下子从她脑海里剔除掉了。黄杏儿站在离天很近的崖顶之上,远眺风波镇。风波镇变得很小很小。她痛快地呜呜哭了一场,然后睡过去了。
醒来之后,黄杏儿看到过耳风坐在旁边,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一棵草。
“你是怎么爬上金牛顶的?”过耳风问。
“小瞧我是个女人?”杏儿坐起来,拣掉身上的草叶子。“我运气好,就该来到金牛顶。我来了就不打算走了。”
“想给我过耳风当压寨夫人?”
“美得你。”黄杏儿说。“我来金牛顶你怕不怕?日本人要是知道了,没准就拿大炮把金牛顶给轰了。”
“知道。昨天夜里你本该是在鸟窝村的炮楼里。风波镇恐怕要有麻烦了,也不知道你们家胡爷和韩爷能不能顶得住。”
“横竖不就是个死吗。”杏儿也扯下一棵草来,放在嘴里嚼。“风波镇再也跟我没关系了。”
过耳风研究着杏儿。“当真?”
“当真。”杏儿恨恨地说。
“那我就收留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杏儿脸涨得通红。她站起来跨到崖边。“你要是逼我,我就从这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