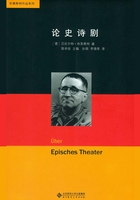鸟们在清晨尚未到达的时候醒来,它们的出现就是音乐再一次降临,仙女湾重又成为庞大的演艺厅。棕头鸥、赤麻鸭、贼鸥(鱼鸥有偷吃其他鸟类的蛋和幼仔的不良行为)、草原鹰、鸬鹚、黑颈鹤、斑头雁……它们从水汽迷蒙的湿地起飞,或者掠过清辉荡漾的湖面,在湿地上空的灰白晨光中打开它们的歌喉。怎样谛听,我都无法分清节奏、曲调、和声、速度、调式、旋律,也辨别不出高低、疏密、强弱、刚柔、起伏、断连,我所熟悉或者陌生的蓝调、灵歌、重金属、嘻哈……它们一齐出现,多么繁复。这些旋转在水面上的灰色河流,现在没有一双做作或粉饰的手,去为它们指挥和引领,也没有一条路可以引领我到达前面的湿地。闪烁清凉露珠的茂盛草丛高过脚踝,裤脚迅速湿透,寒意从小腿向上递送。分开草丛,踩下去,脚底依然是柔软多汁的嫩绿草茎,充满年轻肌肤的弹性。草叶掩映处,大丛粉红明黄淡紫的小花朵吐露出来,薄绸的花瓣,精巧对称的古典图案,黑色小虫子爬过来,晕头转向,像参加一场热烈的盛会。水汽依旧浓重,仿佛每一棵草茎和叶脉都在无止境地向外输送看不见的露珠。停驻,望过去,丢失掉边际的水泽地正耀射出成片光芒,无数个小太阳嬉戏其上,浮光跃金,而大丛生长的草棵子丰茂静谧。远处湖水荡漾,天域辽阔。不需要走,所有的光与影,所有的祥和与宁静,所渴望的,终极的,现在它一一呈现。
我依然要想起许多年前青海湖泛出晶莹光芒,仙女奏琴吹箫,仙鹤翩然飞舞,仓央嘉措踏浪人海,归于天堂的事情,尽管我知道这只是关于“仙女湾”这个名字来历的一个传说。但对于仓央嘉措,我并不愿接受他在此处羽化成仙的传说,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理论根据。“遁去”、“营救”、“放行”、“病逝”、“失踪”、“自杀”、“谋害”,关于一个人消失的可能性,后人用尽了所有的想象和推测,在这种种之间,我只选择“遁去”一说,因为只有这一说极大可能地保障了我对这位具有争议、神秘和个性的人的空茫祝愿。是,我在读到所谓仓央嘉措诗歌的时候,总是持着怀疑,我不知道那流传下来的诗歌中,哪一首才属于他。曾缄的七言本,刘希武的五言本,于道泉的自由体,哪一本更接近于原文。《东山诗》中的“ma——skyes——a——ma”到底是未生娘、少女、佳人,还是在小资们反复念叨的“玛吉阿米”……在我后来的阅读中,仓央嘉措一步步成为那个出生宗教世家(说仓央嘉措家中世代信奉宁玛派即红教),受过严格宗教训练的宗教领袖。我并且依据自己的理解,逐渐明白所谓“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的佞言,不过是仓央嘉措不愿受比丘戒,并希望将以前受过的戒解除而已。他有过化解教派纷争的宗教理想,也有过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政治制度的政治理想,而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反映自己在缺乏人身自由,深受陷害的情况下,对第巴桑结嘉措的怀念和佛法修行的心得,他的诗歌从密宗的角度出发,全能地做出宗教上的诠释。
我因此想象,1706年(康熙四十六年)冬,被“诏送京师”的仓央嘉措路过青海湖畔时,刚察草原的寒冷像疯狂的铁骑肆虐,草原一片枯黄,彤云低垂,雪山黯淡,牛羊已经失去踪迹,百灵忘记呜叫,仙女湾湿地的水泽地已冻结成冰,黄鸭和赤麻鸭也早已逃遁,满目荒寒。哨儿风扑过来,带着雪粒和冰碴儿,打着尖利唿哨,它钻进每一个微小的缝隙,在那里成为小丑,逃窜。氆氇、毡房、皮帽,没什么可以御寒了,如同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了,圈套像雪花落下来,罩着来时的路,梵音和诗歌无法去温暖它们。那曾经的门隅,葱郁树木,雪线云影,还有开在四月桃枝上的鲜花,依旧比诵经声还安静。而那佛光闪烁的布达拉,人人都在武装。仓央嘉措看一眼远处的大天鹅,这些从遥远北方迁来的冬候鸟,洁白安详,如同这个世间的尊者,漫步湖岸或者翔于低空。它并不理会这世间的纠结,不理解灰飞烟灭,它也不知道纷争和密谋,权利和陷害,它看到的,永远是水泽之上随风舞动的雪花,是一低头时,那藏在草茎中冬眠的虫豸。佛法藏在天地间,自己却就此别过。仓央嘉措转过身,雪花再一次降落。
人们低下身子,伏在水泥大坝的铁栏杆上,观看,有些人举起相机来,对着哗哗流水,游人模样。他调的是微距吗?我从没有过给一条滑溜溜的鱼拍裸照的经验,也不曾抓拍它们活蹦乱跳的模样。人们唏嘘惊叹。我知道,此刻,那水面之下,正有无数条湟鱼小鲤鱼一般跃起来,朝着水流的上方,它们正在用渺小和微弱创造它们生命中辉煌的一瞬。我挤过去。我原本是要离开,但我还是又一次伏下身去。我的样子仿佛在给那些小小的鱼们鞠躬。
“半河清水半河鱼”,这条河流两岸原本长满了葳蕤沙柳,因此叫沙柳河,我不曾亲眼见到那些水边植物葱绿旺盛的过去。现在,这条河流两岸除了大大小小的碎石和丛丛野草,再没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植物将它们的阴影投下来。草原的阳光无遮拦地烤在石头和水面上,也烤在青白色的水泥大坝上。蹲踞的坝面上横砌着许多条水泥台阶,河水从大坝上摔下来,并没有溅起白色浪花。水势浩荡,但不激越。草原上的河,暗含劲道,表面却依然宁静地倒映着亮白天光和散淡白云。大坝之下回旋的清澈河水中,遍布密密麻麻的小湟鱼,它们摆动灰褐色或者黄褐色的小身体,仿佛摇曳着无数面窄小旗帜,呐喊。一寸,或者两寸,那么小,但是它们的目标那么专一。扭动,回身,再扭动,然后跃起。它们跃过水泥台阶的机率并不高。许多鱼依旧落下来,溅在水面上,甚至被水流冲到更下方。这并不是结束。扭身,游动,跃起,再跃起……我看着一条小湟鱼跳了三次才跃上一个台阶,而整个大坝,有30多条台阶。隐藏在小湟鱼柔弱身体里的坚韧和倔强,以及河流的坚韧和倔强,弱小与强大,它们对峙、坚持、冲击,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站在它们旁边,想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废话。
推开哗啦作响的铁皮大门,涌现在眼前的,是许多水泥砌就的小小鱼塘。靠近去,看见波动的水面之下,静伏无数湟鱼苗,也只有麦芒大小。小院静谧,铝合金窗框和用来封闭房屋的大块玻璃正折射出耀眼阳光,这使得小院如同葵花般灿烂。这是位于沙柳河镇上一户养育湟鱼苗的人家。健壮羞涩的女主人正在拌湟鱼饲料:磕开鸡蛋,剥离蛋白和蛋黄(最好不用蛋白作饲料),磨细黄豆,取出熬熟的猪油,加盐,搅拌。饲料撒下去,小鱼们纷纷争食。“饲料一次不能喂得太多,”女主人说,“一年湟鱼长一两,养一年才能放生。”扭过头,我看到女主人脸上的慈爱和悲悯,如同此刻阳光。“你错过了放生节。”女主人补充。我熟悉那个节日,虽然未曾亲历,将古老的宗教仪式和旅游混在一起,期待一种效益。效益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慢性病,它匍匐在水泥路上,扭动隐形的爪牙,一点一点侵吞土壤、根须和水分。而放生,跳坝,淡水河枯竭,偷食,禁捕,生长缓慢,人工受精,淡水养殖,湟鱼所经历的事情,如同我们。
这个傍晚,在县城一户屋顶盖着红色彩钢瓦的农家院,我遇到大盆种养的花,高原上遇到盆养的花,这让我心存温暖。夹竹桃、天竺葵、倒挂金钟、月季、四季海棠……花开得并不娇艳,偶尔探出一两朵,似乎跋涉许久,满经脉的倦意,那枝叶也蒙着层萎黄,仿佛正在枯去,白蝴蝶却多,无声息地翩跹。猫咪四仰八叉地睡在花盆下,太阳光转过去,也不知道挪一下窝,黑狗描着黄眼圈,了一眼,吠一声。院内大片空地,葳蕤野草贴着南墙角。想着春来撒几粒菜种,肯定葱绿。但是这家女孩告诉我,“我妈妈不会种菜。”女孩回答得理直气壮。这让我气馁。厨房里雾气腾腾,人们正在为客人准备全羊系列:开锅肉(水一开就捞出来的羊肋条),血肠(羊血加蒜苗、姜末、花椒末、盐和羊肠灌制而成,煮血肠时需要用一枚大针在鼓胀的血肠上戳个气孔,以免血肠爆裂),羊筏子(瘦肉剁成末,加入少许面粉,放入花椒老姜等粉末调料,用带皮羊油包卷,煮熟),肚腺皮(羊腹部的软肉),白条(高原上,哪个人点菜时不说来二斤白条呢),煮羊头(羊角已经截去,留下两个眼睛似的黑窟窿)。羊终究是这个世界上最温顺的动物,它生存的意义就是毫不吝啬,献出自己的每一寸肌肤。厨房一侧的红砖墙上,悬挂着白粗线串起的黄蘑菇。蘑菇已经风干,失去色泽,像一串古人遗失的项链。此前,在县城的小街上,我看见这些来自草原的黄蘑菇大堆大堆摊放在水泥地坪上,等待出售。一斤20元,靠摩托而站的长发男人,并没有将黄蘑菇迅速卖出的热情。
这是招待贵客的高原饭食,它体现的依旧是夯实拙朴的高原心情。奶茶,青稞酒,羊系列,中间加几盘檗:黄蘑菇炒肉,蒜泥拌黄瓜,香菜拌萝卜,酸辣土匣丝,虎皮辣子,酿皮子,鲜辣麻香。其间主人进来歉意,微笑,说没有湟鱼。尽管在湖畔吃湟鱼是想象中的最高待遇,但一年长一两肉的小小湟鱼,我们怎能下筷。
选自《青海湖》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