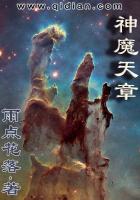在战国时代,士人精神堕落到了最低点,士人阶层也逐渐庞杂化、无序化,这一情况持续到了西汉初年,转变便已悄悄产生。从战国末年的士风沦丧、人心不古,到北宋时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经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就是士人精神逐渐积蓄力量,最终成功自赎的过程。
199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笔者在《读者》上偶尔读到这样的一段话: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日子,可是,三天之后就是复活节了!
读至此处,笔者豁然开朗。世事如此,人生如此,历史大势亦如此。
《周易》中的“复”卦,所代表的正是最艰难的情况之下的“一阳来复”,其中包含的哲理,正是一切事物降至其自身的最低点时,就会出现上升的转机与反弹的动力。
士人精神也是如此。在战国时代,士人精神堕落到了最低点,士人阶层也逐渐庞杂化、无序化,这一情况持续到了西汉初年,转变便已悄悄产生。
从战国末年的士风沦丧、人心不古,到北宋时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经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就是士人精神逐渐积蓄力量,最终成功自赎的过程。
对于人的一生而言,一千多年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对一种社会群体而言,一千多年是开枝散叶、迎风绽放的花期。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当时的士人们并不知道这一过程需要上千年,但是他们中的执着者依然无怨无悔,为着这一群体精神的浴火重生而奋斗。
深渊中的挣扎
士人精神之所以会堕落,一方面是因为士人阶层内部存在的“信仰危机”,即儒家和墨家在各自的思想与实践中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分裂局面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为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原则。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大秦帝国面前,他们突然发现,以往的方法行不通了。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不但在制度、法令、管理方面严格要求统一,而且在思想、文化、风俗方面也要实行一统的政策。秦帝国是这样,西汉王朝也是这样。在统一的时代,游走于各地的士逐渐失去了表现的机会,而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也是能够忠于职守、彰显气节的人。
群体精神已堕入深渊的士人阶层,终于开始反思他们应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奸士的转型
秦末汉初的奇人叔孙通的一生,正是士人阶层精神状态转变的浓缩表现。他从谄媚、阿谀转向营造礼乐制度、重建信仰,虽然还带有投机的色彩,但已经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叔孙通在秦朝时因为善于写文章、知识渊博被征召入宫。以他的才能本来可以被任命为博士,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过人的表现,任命就迟迟未下。秦始皇去世之后,陈胜、吴广掀起了反秦战争。
当使者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朝廷时,秦二世召来朝中的各位博士、儒生问道:“在楚地戍边的那些士卒攻下蕲县进入陈县,对这件事,各位是什么看法?”
在场的三十多个博士、儒生不清楚秦二世的脾气秉性,便按照自己所学的那些纲常伦理之道,直言不讳地说:“做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攻打他们。”
谁知秦二世是一个喜欢文过饰非的人,对他而言,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了起义,就说明他治理国家不当。所以,秦二世听到儒生们的这番言论就发了火,脸色顿时变了。
叔孙通因为迟迟没有被任命,一直想要找个机会表现自己。
他通过近日来对秦二世的了解,以及刚才儒生、博士们发言时对秦二世表情的观察,已经知道了秦二世的心理变化,便上前说:“各位儒生的话都不对。当今天下已经统一,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而且先帝在时就毁掉了以前为了割据而建起的城池,销毁了杀人的兵器,向天下人昭示不再用它。何况现在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都能遵法守职,四方八面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地方官们正在搜捕他们治罪论处,不值得忧患。”
秦二世听到叔孙通赞扬自己是贤明的君主,还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强盗的行为,自大感马上冲昏头脑,高兴地说:“说得好!”然后,又重新询问在场的每一位儒生,让他们重新回答对此事的认识。儒生们有的说这是造反,有的说这是盗贼。
在场者逐个发言之后,秦二世命令监察官审查每个儒生说的话,凡说是造反的,都要下狱治罪,因为秦二世认为他们不该说这样的话。那些说是盗贼的,都免掉职务,因为他们都没有率先表示对皇帝的支持。而第一个说陈胜起义军是盗贼的叔孙通,却获赐二十匹帛、一套服装,并获得了他期望已久的博士之职。
叔孙通离开了皇宫,回到自己的住所,就有一些刚才在场的儒生问道:“先生说了些什么讨好话?竟然得到皇帝这样重的赏赐!”
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啊,我如果不那样说,几乎逃不出虎口!现在我说了违心的话,别人一定会轻视我,可是谁知道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呢?再说,等到事态闹大了,秦二世也许会迁怒于我,把我杀掉,我不如及早逃走的好。”
叔孙通在宫中的表现,是出于自保的心理。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颠倒黑白,找准了秦二世的喜好,在这个残暴君王的面前逃过了一劫。此时的他,是随波逐流、无底线无原则的。他不顾是非只顾活命,虽然一时蒙骗了秦二世,却自己也没有把握将来不会因此而引来祸患,所以才要火速逃命。
叔孙通逃离了都城咸阳,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薛县,当时薛县已经投降了楚军。等项梁到了薛县,叔孙通便投靠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到了楚怀王(义帝)的身边。在攻灭秦朝之后,楚怀王被项羽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去了,叔孙通便留下来侍奉项羽。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带领五个诸侯王攻进彭城,叔孙通就投降了汉王。而后项羽夺回彭城,刘邦败北,这回叔孙通没有再做墙头草,而是跟着刘邦一起逃走。直到此时,叔孙通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
叔孙通总是穿着一身儒生的服装,刘邦见了非常反感;他就换了服装,穿上短袄,而且是按楚地习俗裁制的。刘邦是楚地人,看到叔孙通穿上了自己家乡的衣服,很是高兴。
应该说,刘邦讨厌儒生,只是一己的好恶,而且刘邦也不会因此而杀掉叔孙通,但叔孙通却投其所好,专门费心在细节上做文章去迎合刘邦的口味。确实,“细节决定成败”,刘邦也从此开始觉得叔孙通比以前顺眼多了,说的话也中听多了。
那么,叔孙通这样讨好刘邦,是为了向上爬,还是忍辱负重呢?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
当初,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追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可是叔孙通从来不说推荐他们的话,而专门推荐那些曾经聚众偷盗的勇士。他的那些弟子都很不高兴,在背地里抱怨他:“我们侍奉了先生几年,幸好能跟他投降汉王,如今他却总是不推荐我们做官,却专门推荐那些坑蒙拐骗的社会渣滓,这有什么道理?”
这话传到了叔孙通的耳朵里,叔孙通便郑重其事地召集大家,对他们说:“现在汉王正冒着生命危险去和西楚霸王争夺天下,现在需要的是战斗英雄、特种部队,而不是宣传队和文艺兵。我问问你们,难道你们觉得自己擅长阵前厮杀吗?所以,我先要推荐那些能上战场打仗、斩将夺旗的勇士。等到天下太平了,肯定会让你们大展拳脚,你们不要着急,得等机会,我肯定不会忘记你们。”刘邦听说了叔孙通这番话,觉得他又有远见又忠君,而且不把士人看得那么重要,心里大为高兴,就任命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
叔孙通对追随他的人讲话时,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所以他对刘邦浴血奋战的生涯表现出十分钦佩的样子,这样的奉承话正中了刘邦的下怀。作为一个在马上拼杀争夺天下的强权者,刘邦喜欢听到的就是对他战功的赞美,而叔孙通在非公开的场合也这么做——其实他是故意做给刘邦看的——就更能看出叔孙通的忠心了。可见,叔孙通对刘邦的心思揣摩得极为透彻,而且分寸拿捏得也很准,所以给自己带来了实利。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已经统一,诸侯们在定陶共同尊推汉王为皇帝,叔孙通负责拟定仪式礼节。为什么讨厌繁文缛节的刘邦会想要拟定仪式礼节呢?
因为他身边的功臣们基本都出身于基层,不懂得礼法,在朝廷饮酒作乐时争论功劳、狂呼乱叫的事时有发生;还有的人发酒疯,拔出佩剑用力地砍削庭中的立柱,刘邦总觉得这太像在村子里的小酒馆聚众酗酒了,一点都没有皇帝的派头,因此很是头疼。
叔孙通知道刘邦的心病,就劝说道:“那些儒生很难为您攻城拔寨,可是能够帮您巩固基业。我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上的礼仪。”
刘邦说:“只怕会像过去秦朝的那些礼节一样烦琐吧?那种礼仪我可受够了,而且我也记不住啊!”
叔孙通的回答是:“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所以从夏、商、周三代的礼节有基本的延续性,但也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进行改动。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白,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略用古代礼节与秦朝的礼仪进行糅合,制定一套适合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礼节。”
刘邦对此还是犹豫不决,他说:“先生你倒是可以试着办一下,但要让它通俗易懂,主要是得考虑我能不能够做到。”
现在叔孙通终于等到了机会,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那就是“制礼作乐”。他一味地向刘邦低头,其实等的就是这一天,现在,他要用自己的想法来规范这个帝国的秩序,让西汉王朝成为一个懂礼仪、有底蕴的礼法之邦。
为了顺利制定出礼仪,叔孙通奉命征召了鲁地的儒生三十多人。当时有两个儒生不愿去,还讽刺叔孙通说:“您侍奉过将近十位君主,而且都要靠阿谀奉承才能受到重用。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战死者还来不及埋葬,伤残者也没有痊愈,却要制定礼乐法规,这不可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有和平、稳定地发展百年以后,才能真正建立礼乐制度。我们绝不会违心替您办这种事。您办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去。您还是走吧,不要玷辱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势的变化。”
叔孙通就与征来的三十人一起向西来到都城,他们和皇帝身边有学问的侍从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郊外拉起绳子作为施礼的处所,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进行演练。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帝可以先来视察一下。”刘邦视察后,让他们向自己行礼,然后说:“我能做到这些。”于是命令群臣都来学习,这时正巧是十月,能进行岁首朝会的实际排练。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已经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大典的礼仪是:
在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导着诸侯,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摆设着各种兵器,树立着各式旗帜。谒者发令说“小步快走”,所有官员便得立即各就其位,大殿下面的官员则站在台阶两侧,有几百人之多。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
列队完毕后,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然后皇帝才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然后引导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肃然起敬的。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最后,监察官员对在场者的礼仪进行纠察,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对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
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话,行为上也没有失当的。大典之后,刘邦非常得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顺便进言说:“我的弟子们跟随我很久了,而且他们也参与了制定朝廷礼仪,希望陛下授给他们官职。”刘邦便慷慨地将他们都封为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黄金都分赠给参与制定礼仪的儒生,这些人都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大圣人,通晓当代的紧要事务。”
从制定礼仪这件事可以看出,叔孙通并不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之前的种种行为,虽然有向上爬的嫌疑,但是他这一次冒着很大的风险,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并不是要单纯地讨好刘邦,而是想要树立一种新秩序,并且建立起礼乐制度对政治行为进行引导的体系。
在礼仪制度建设完成后,他并没有贪财,也没有将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这恰恰说明他不是为了权力、金钱而做这件事,而是为了他的信仰、他的理想。
在汉朝建立前,叔孙通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对秦二世那样的昏君,他都会假意逢迎。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他卑微地活着,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终于挺身而出,做了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从“奸士”到名臣,其实正是他试图让士人阶层介入政治,在制度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自我转变过程。
殊途同归的坚持
士人坚持理想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无条件的坚持,即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都要固守自己的原则;另一种是有条件的坚持,可以不拘小节,可以进行变通,但最核心的原则却不容动摇。
这两种坚持,性质上不分高低,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西汉初年的政坛上,这两种坚持的形式同时出现过,那就是在吕后专权时,就吕氏外戚封王的问题进行的一次大争论。
汉高祖刘邦本来只是一个默默无名之人,后来在秦末的大变乱中加入到反秦军队,才慢慢崭露头角。他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一方面是靠一批勇猛善战的大将,另一方面是靠善于运筹帷幄的文臣谋士。所以,在他统一天下后,举行了一个仪式,与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们订立了一个关于富贵等级的政治契约。
契约中规定,功臣们可以在朝廷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且规定只有刘姓(也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同族亲戚)才能封王,只有拥有大功的人才能封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征讨。
这个政治契约,一方面保证了功臣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刘姓江山的安全。皇帝为功臣们提供特殊待遇,功臣们负责拥护刘姓人做皇帝不受侵犯。这个规则让汉高祖和他的功臣们相处得比较融洽,彼此间很少出现什么争斗。
但是,汉高祖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权,以皇太后的身份干涉朝政,名义上是辅助她的儿子惠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家族吕氏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