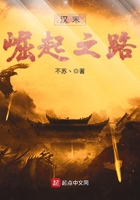花园里依然花草葳蕤。柳市是一个不分四季的地方。鞋跟在路面上叩击出单调的脆响。丛好闻到了馥郁的花香。这样的气味令她疑惑,居然会是这样,当年为什么她没有闻到花的芬芳?由此,她就看到了自己在十八岁时来到柳市时的状态——麻木,呆滞,没有希望,在少女时期却已经苍老。而那时,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啊,丛好悲伤的想,她并没有任何奢望,不过是想的得到一个女孩子应有的庇护。
丛好深深地吸气,让馥郁灌满肺腑。她怕一瞬间,自己就再次丧失掉感知这种气味的能力。
修理厂的门前蹲着一个人,结实,粗壮,两只耷垂在膝盖上的手让人感觉出即将要掘进土地里的动势。丛好远远就看到了这幅夜色中的黑黢黢的剪影,一下子想到了那个蹲在自己家楼下,最终将自己母亲带走的男人。这个人影看到丛好走过来,向她叫了一声:
“丛好!”
丛好心里颤一下,这种瘪瘪的兰城腔调既熟悉又陌生,令人不敢确认。
人影站起来,是一个牛高马大的男人样子。他向她跑过来,继续叫:
“丛好!”
柳市的街灯虽然明亮,但丛好还是无法把这个跑向她的男人看得分明。是她的心里倏忽黑暗了下去,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终于站在眼前了,伸手拉她的胳膊。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叫嚷,“防守反击你懂不懂?防守反击!”。丛好虚弱地说一声:
“张树,是张树吗?”
张树坐了十年的牢,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让他出来后就直接成为了一个毫无指望的男人。张树的父亲在一次工伤中丢掉了两只手——一只卷进机器里,另一只徒劳地去拽,结果两只一起卷进去。张树的母亲下岗了,只差一年就可以享受到“退休”的待遇,但还是被赶到了下岗者的队伍里,每个月一下子少收入好几百元钱。一家三口运气都差到极点,对于生活的态度就一个字:骂。
这个时候的兰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年那些说着南方话的人,已经成为了兰城真正的主人。兰城所有能说得出口的好东西,都被他们消费了。他们已经不屑于给兰城人配眼镜,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兰城人的眼睛已经学会了仰视他们。
出狱后的张树愤怒地发现,兰城几乎所有长相美丽的“花儿”,都被那些只有三寸高的南方人“摘”了,她们高出大半个头地依在那些男人肩上,骄傲地在兰城招摇过市。
愤怒归愤怒,但是张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出狱后,张树接连谈了几个女人,都是些饭店服务员之类的角色,没法让人用好的比喻来形容,但张树不嫌弃她们。他坐了十年的牢,把一个男人最好的时光葬送掉了,在里面只有靠“打飞机”来安慰自己,现在没了禁锢,只要是个女人就是好的。张树都三十多岁了,当然已经懂得怎么“摘” 了,而且真的是被憋坏了,所以根本就没了挑三拣四的念头。
结果张树不嫌弃她们,她们倒嫌弃张树了。在她们眼里,张树除了在床上差强人意,其他简直就是一无是处的,没工作,没钱,家庭条件差,而且脾气大,你不让他舒服他就揍你。于是最终都跟张树说了再见。
张树被很具体地拒绝在生活的外面,豁出去再坐一次牢的念头都有。他算看清楚了,自己根本没什么指望,再过上几年,连没了两只手的父亲都比不上。
有一天,遇到一个齿轮厂的熟人,老远就跟张树喊:
“张树,你媳妇回来了!”
张树以为对方是在说刚刚从他家搬走的那个女人,没好气地吼一声:“我捶死她!”
那人愣一下,说:“你以为我说谁呢?是丛好啊,老丛家的那个闺女!”
张树的心一下子蹦在嗓子眼。张树出狱后打听过丛好的消息,知道她和她父亲去了南方的柳市。
那人又说:“你媳妇看起来混得不错,穿着羊绒大衣呢,骑着辆破车子都像个款婆。”
对方一口一个的“媳妇”,叫得张树的心抖抖的,丛好的身份不由得就被他用“媳妇”固定住了。张树灰暗的生活,一下子就萌生出理直气壮的希望。他少有地敏感了一下,丛好“骑辆破车子”这个细节,被他看出了一种对于往事的缅怀和眷恋。他认为丛好一定还记得他。张树决定了:找丛好去!
张树勒令自己的父母给他拿出了一笔路费,他来到了柳市,找到了向宇汽车修理厂。当年,这个私人厂子的老板在兰城齿轮厂招聘技术人员,是一件被大家记住了的事情,所以,张树很容易就落实了他要寻找的方向。按图索骥,他找到了,却没见到丛好,只见到了她的父亲老丛。
刚刚过完春节,汽车修理厂开工的第一天,老丛就劈面见到了瘟神。见到张树的老丛像见到了鬼一样,哇地叫一声,往后蹦一步,脸变成猪肝那样的颜色,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张树不懂他干吗这副样子,问他丛好的下落。
老丛吼起来,说:“丛好死了,你见不到她!”
张树当然不信,但眼前的老丛不复当年,心宽体胖,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还是让张树有些胆怯,他说:
“你别骗我,叔你骗我有啥意思?”
老丛继续吼叫:“你离我们远点儿!我活了快有你三个这么大了,逼急了我跟你把命换了,我也不亏!”
张树一听这话就笑了,心里又有了底,说:“叔,这话我听过,这话你十几年前就跟我说过,叔你咋这么爱跟人换命呢?”
老丛跳着脚说:“你放屁!谁说我爱跟人换命?逼急了我才换!”
张树说:“好好好,换就换,叔你想换咱就换。不瞒你说,叔,就算我只活了不到你三分之一那么大,可是我也早就活够了,我早就活够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恐吓了。老丛心头一凛,呆呆地,开始在办公室里转圈子,转着转着,突然就软了下去,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摸出张银行卡给张树,说:
“叔求你了,别再害丛好了,拿上这些钱回去吧。”
说完老丛很诚恳地告诉了张树卡上的密码,怕他记不住,还说了三遍。
张树想一想,就拿着卡走了。他找了家便宜的招待所住下,然后就到银行把卡里的钱全部取了出来。匪夷所思,居然有整整十万。这是老丛暗地里存下的所有积蓄,连大脸盘刘姨都不知道。老丛也是穷怕过了的人,这些钱是他目前踏实过日子的精神保障,但是他宁肯全部给出去,只要张树这个鬼不再把他的女儿拐走。老丛心里隐隐地觉得,只要这个丧门神出现,丛好就一定会跟着他逃掉。
老丛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虽然他看不透自己的女儿,但丛好身上的那股子劲儿,却是老丛刻骨铭心的——跟她妈一样,骨头里就长着往外飞的翅膀!
老丛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出去,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适得其反,更加坚定了张树找到丛好的决心。张树觉得自己来柳市是来对了,还没见到丛好,好处就已经摆在眼前了。十万,妈的在兰城要挣几辈子!张树本来含混的目的一下子清晰了,认为自己来找丛好,就是来找希望的,这个希望会以各种姿态来满足他,钱,乃至爱情!
张树决定天天到向宇汽车修理厂的门前去等,做了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他相信总会等到丛好的。而且,这种等待目前还不是艰苦的,有种悠闲的味道,守株待兔似的。现在张树有钱,当即换了一家星级宾馆住,给自己添了身昂贵的行头,还去夜总会玩了几次,都找了小姐,很是尽兴。
惊恐的老丛天天看到张树那个死样子在厂门口晃来晃去,一筹莫展,心惊肉跳,终于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2003年,丛好和张树住进柳市一家星级宾馆时,又一场伊拉克战争即将打响。
那位阿拉伯领袖在电视里说,要把巴格达变成美国人的坟墓。他的这个态度又一次蛊惑和怂恿了丛好,使得她在时隔十二年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蒙昧少女的懵懂状态。
眼前的张树,被丛好再一次赋予了某种有意味的象征,是一个向着纯粹,向着简单的美好而去的可能。他就是那把能够打开丛好这只锁的钥匙。
在去往宾馆的路上,丛好是一种梦游般的感觉。多年前,那份疼痛被张树温柔驱散的眷恋感,像洪水一样包裹住她。丛好的头靠在张树的肩上,有种相依为命的滋味。直到被张树脱光了衣服搂在怀里,丛好才有一瞬间的清醒。她想到了潘向宇,却是这样的想法:潘向宇是不属于她的,自己最终也是要被驱赶开的,好像一笔无偿使用了很多年的债务,最终你还是要把它还回去。
张树对丛好的身体是尊重的,尊重到几近虔诚的程度。这个时候的丛好,在他眼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齿轮厂技校的傻女生了,她和她的生活,在张树眼里,都宛如天上人间。张树觉得眼前的丛好,像一个古代女子,这可能和她的装束有关:中式的对襟薄棉袄,结着中式的纽襻。但张树说不好,他觉得连丛好呼吸出的气流,都有股“古代”的味儿。连丛好的内衣都那么吓人,那种丝质的精良和蕾丝的繁复,是那些他所经历过的兰城女人们绝对没有的。这些都让张树有了望而却步的压力。所以张树是拘禁的,是如履薄冰的,像是在朝觐。
这种谨慎的态度却打开了丛好的身体。
她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方式。潘向宇是高姿态的,在床上下巴都是扬起来的,他只是索取,天经地义般的毫无顾忌,猛烈地来,猛烈地去,像一轮接着一轮的打击,打击过后,只留下满目的苍夷。
现在,丛好被温柔地对待。
张树是低姿态的,但绝对不是敷衍了事和消极怠工,反而是一种鞠躬尽瘁的全力以赴和舍生忘死。当张树的头埋在丛好的耻骨间时,丛好便彻底震惊了,她从来不知道还可以这样。丛好麻木以久的身体绽开,那种复苏的感觉,让丛好禁不住颤栗着叫出声,拼了命地要把张树整个人都拥进怀里。她的指尖掐入了张树的后背,继而翻身将张树压在了自己的身下,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猛烈来去的打击者,那种疯了一般的滋味,让她飞起来,滑翔着,随风而行,再也跌落不了了。
迷乱中,身旁的手机响起来,丛好看都没看就关掉了手机。
她感觉得到张树在身下的耸动,然后那种被滚烫的子弹点击了一般的滋味,在她身体的深处激荡开。但她依然不知餍足,腰臀拼命地起伏,仿佛在弹跳一般。直到张树忍受不了地发出了哼声,双手卡在她的肋下,硬硬地阻止住了她的亢奋。
张树使劲把她搂在怀里,任她在他的怀抱里持续地抽搐、痉挛,最终慢慢地平息下来。
丛好觉得自己一定是休克了,等到意识恢复,甚至猛然间想不起自己这是身在何处。张树俯在她的头顶,对着她再次发出了当年的叹息:
“我摘得花儿多了,就你最好哇。”
丛好凝视着张树。这个当年的少年,已经具备了鲨鱼一般的体态,脖子上堆积出一圈肉,胸前堆积出一圈肉,腰腹上堆积出一圈肉,剪得只有寸把长的头发,鬓角处居然已经花白。丛好伸手抚摸他的脸,顺着轮廓,一直抚摸下去,指尖划过他的脖颈,胸膛,腰际,最后轻轻地揽住他的后背,将他拉向自己,把自己的脸和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张树感到自己的肩膀上湿了。
张树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对待过?刹那间,这个粗鲁的人也有了一些伤感。但他适应不了这样的情绪,不禁晃了晃自己的脑袋,好像是要让自己清醒过来一样。
他们在宾馆的房间里不分昼夜地做爱,饿了就打电话叫人送东西上来吃,困了就睡一会儿,其余的时间都用在身体的剧烈运动上。每次结束,丛好都要求张树和她一起冲澡,对此张树不能理解,觉得如此频繁地洗来洗去毫无必要。丛好就不勉强他了,心想,慢慢来吧,给他些时间。——人是可以自己提高自己的。
偶有间歇,他们也交谈几句。
丛好问:“这些年你想我吗?”
张树说:“想,不想我就不会跑来找你。”
丛好说:“都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张树却总结不出来。他干脆说:“我打飞机的时候想的都是你!”
丛好在黑暗中轻轻地笑了。
张树问:“你想我不?”
丛好说:“也想。”
张树问:“那你是怎么想的?”
丛好也总结不出来,想了一阵,突然笑着喊道:“防守反击你懂不懂?防守反击!”
张树却已经听不懂她的意思了。
张树说:“那时候我没‘摘’成你。”
从好说:“现在还来得及。”
这样过了三天,直到精疲力竭,耗尽了所有体力。
丛好虚弱地做出了决定——和张树回去,回到兰城去。她忧伤地想,母亲当年离开兰城,最终不是还要回去吗?——在她身体变得臃肿,头发白多黑少的时候,除了兰城,哪里都不会是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