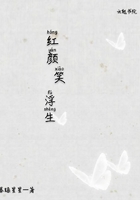我们三顶黑轿才离开根敦营地的范围,假装成奴仆的鸠就来到我轿边回我说,前头璇玑坐那顶轿子突然停了下来,我忙叫停自己的轿子,去到璇玑那顶大轿旁,只见伪装成轿奴的顿珠,架着只穿着里袍的璇玑,往路旁边的树林走去。
“你们要去哪里?”我快步追上他们问。璇玑转身没答我话,而是将一大团衣服扔到我怀里。
顿珠稍微扭头对我说:“年门主,你怀里那就是要找的地图,此地不宜久留,师弟让你们赶紧离开,我们两人一会自会离去。”
我刚一听还以为璇玑又给闹什么别扭,不过很快我听到阵压抑不住的呕吐声,刺鼻的酒臭,还有呕吐物发出的恶臭,熏得我顿时也恶心起来,不过这里离根敦的营地并不远,如果他们发现不对追过来,就凭顿珠一个人,拖着已经醉死的璇玑,怎么可能全身而退。
等我缓过几个气,璇玑怕也吐到吐不什么东西来,只剩下他浓重的喘气声,我把那衣裙一股脑穿到自己身上,又从怀里拿出张手绢,走到璇玑身边,弯身想帮他把嘴边沾着的秽物擦干净。璇玑一手按停我,舌头发重道:“你走,带皇帝走……”
我用手绢帮他擦嘴角说:“我们一起来的,当然一起走,就这样把你丢在野外,明日皇上问起,他也会责怪我的。”
“妇人之见,轻重不分……”看来璇玑吐完以后,人清醒了不少,已经有力气教训起我来。我推开他那渗满冷汗的手说:“现在你爱怎么说随你,反正这会你得听我的,我的影堂陈堂主。”
他听了我的话,并没反驳,而是用自己湿冷的手再次按定我,我没好气的就想问他要干嘛,他已经从我的手里抽走那手绢。还有力气抢我东西,那我也不必顾及他到底还能不能走动了。我伸手就撑起他一边手对顿珠说:“大师,此地的确不宜久留,我们还是赶紧上轿离开吧。”
顿珠和我,一左一右硬是把璇玑扶回了轿里,等他上了轿,我也不管其他了,立刻命令轿奴起轿,没回到我的净华园前,即使天王老子要停轿,也绝不许再停,璇玑要吐就让他吐轿子里好了。
另一顶轿里的禛,这会已经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如果人人的酒品都像皇帝老爷他这样好,那该得有多好。我们一路警戒的回到净华园,分别安置好禛和璇玑后,我才得以稍微坐下休息一阵子,这一坐下才顿觉腰酸背疼,劳累不堪。估计刚才禛和璇玑也是如我这样,开始灌下那么多酒,虽然已经酩酊大醉,不过因为心里记挂着正事,这醉醉不入心,直到拿到地图上轿,离开根敦营地的范围,他们才松下神经醉个不醒人事。
他们这一睡,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幸好之前早以做好安排,今日园子里有十三爷撑着。十三爷之前连月养病,今天第一日回园请安,皇帝特宣他独对,平日皇帝宠隆这位皇弟,无日不见向为人知,现在经月未见,皇帝拖着弟弟说上一天的话,哪里有朝臣敢非议半句,捏这样的龙须。
我们赶在晚膳前悄悄回到九州青晏殿。刚进殿门,已经在这唱了一天独角戏的怡王,只见他身上穿着明黄绣五爪金龙四团的亲王袍,脖子上带的是禛亲赐的蜜蜡朝珠,这是禛以前做皇子时自用的朝珠,朝冠顶镶红宝石,看见怡王迎过来,禛几步上前,双手张开一把抱住要跪下的怡王说:“十三弟,今天让你受累了,你的病好点没有。”
“回皇上的话,允祥害皇上操心了,允祥的病已经好多了。”怡王淡然微笑道。
禛听了怡王的话,仍旧不放心,自己伸手就去摸怡王的腿,摸过以后才放下心来说:“果然消肿了,的确是好了不好。”
我对他们这亲热劲已经习以为常,只转头对跟我们过来的璇玑小声解释说:“皇上和十三哥向来兄弟情深,你听了不要随便误会,回了家也不要为难十三哥。”
那璇玑倒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听了我的话只小声说了句:“谢年大人提点。”他脸上虽然没什么,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能感觉到他心中此时有股难名的妒忌,而且他不是妒忌皇帝如此亲近怡王,而是妒忌怡王能得到皇帝如此关爱。
他该不是得到怡王的宠爱后,现在又想来勾引皇帝吧!我一味乱想,身后站着的璇玑这时一脸红一脸白,我给他下的咒已经散去,他的眼睛再又看不见了,他用自己无光的眼珠子死死瞪着我,小声骂我说:“无耻!年七把你脑子里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统统给我抹掉!”
听到他骂我,我才想起,不但自己能感应到他想的事情,他也能窥见我的想法,而且很多时候他比我更会窥探对方内心。我想着便骂他说:“你才无耻,随便窥探别人的内心。”
“容儿你在说谁无耻?”禛可能听到我没压好的声音,立即便问我道。我转头看着已和怡王相携走到北墙正中,御座上坐下的禛,嘻皮笑脸道:“皇上奴才正和陈堂主说那根敦无耻,尽会使些美人计,陈堂主你说是吗?”
听我这样问,璇玑一本正经的答我说:“是的,无耻之人正如那狗改不了****一般。”
我听得脸都绿,他哪里是在骂根敦,分明是在骂我,被他这话刺到的还有禛,禛很不自在的挪了挪身子,我知道禛肯定是想起自己那失败的美男计,以为我是暗指那事,在生他的闷气。
坐在禛下首的怡王,此时圆场说:“臣弟今早收到年大人的捷报,尚未恭贺皇上取得地图,看来我大清平定西北指日可待。”怡王说着从凳上站起来,跪到地行礼,我忙随怡王跪下,身后那璇玑礼行得比我更好,不知道的人怕会误以为他是世族子弟。
“这趟能取回地图,全赖陈福巧施良计,陈福你快过来,祥弟,净容这会可给我们寻得个好帮手了。”禛一脸喜色的对怡王说。
怡王转头避开禛的眼光,阴沉不定的看着我和璇玑,我看他脸色就知道,他八成是不同意璇玑来帮我的,不过璇玑做事从来只问自己不管别人,怕是他反对也没起作用。
璇玑很见机的跨前半步给怡王打千道:“奴才陈福叩请王爷金安。”
怡王敛下脸色,舒了口气才道:“起来吧。”
“陈福谁教你这些的,看你行礼的动作倒比朕好些臣子懂规矩。”禛看似不经意的随便一句,直接刺中的璇玑的要害。看来禛已经在怀疑璇玑的身份,这也对,一个刚入官场的人,怎么会那么熟悉宫廷礼节,不过我是知道他这些礼节,怕是平日里跟怡王学的,又或者他根本就是个贵族子弟,如今只是顶了个璇玑的名字在生活。
昨夜璇玑随我们去做了件,绝顶机密的事情,禛现在要深究璇玑的身份也不奇怪,要让禛知道璇玑以前是八爷的人,璇玑是我举荐的,他出事我必定跟着倒霉,我这时已经骑虎难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双膝朝地上跪下,不是跪禛而是跪怡王。
“容儿对不住十三爷,还望十三爷宽恕容儿。”我直挺挺跪下地说。
怡王听了我的话,一下拘束不安起来,他怕是已经想到我接下去要说什么,张嘴就要辩白,不过我那容他开口接着自顾自的就说下去:“容儿不应该把十三爷的禁脔,诓来做自己的影堂堂主,容儿知道错了,还望十三爷看在容儿也是一心为国的份上,饶过容儿这一会。”
刚喝下口茶的禛,噗的一声将嘴里的茶水喷到了怡王身上,怡王青白着脸死死的看着我,我胆怯的瞄瞄怡王,又瞄瞄禛。这一殿四人里这时最自然的莫过于身为禁脔的璇玑,他坦然得就像刚才我说那人根本不是他,甚至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怡王顾不得擦衣袍上的茶水,忙转身去给被茶水呛到禛的顺背,我也担心的问禛:“皇上您没事吧?”
禛先是摇头,再又点头,边咳嗽边指着璇玑,抬头两眼汪汪满带疑问的望着自己弟弟,虽然禛咳得说不出句话来,不过我们也知道,他是想问自己的宝贝弟弟,这璇玑真的是他的禁脔吗?怡王憋得满脸酱红,张了张嘴竟挤不出句话,果然平日里能妙口生花的怡王,只有在被问到,他是不是金屋了璇玑时才会吃憋。
他说不出无所谓,我代他说:“皇上,净容的陈堂主便是近来京中疯传那西山戏子,就是外传给十三爷养在西山别墅的那位。”
怡王在西山圈养着个戏子的流言,大早几个月前就在京中传开,要不是惧于怡王的权势,京中那些好吃懒做的八旗子弟早就想去看看,传言中把怡王迷得夜不归宿的戏子,是怎生的一个模样。再加上这次怡王连养病都挪到西山去养,就让那流言更喧嚣尘上了。
只是估计连禛都没想到,传言中那戏子居然是璇玑这样的人,他用种既有点难以置信,又好象有点明白个中奥妙的目光,来回的看着自己弟弟和璇玑。怡王似乎想许多,最后咬了咬腮帮子,满脸悲壮的朝禛点头承认道:“皇上,他……陈福他的确如年大人所言,他是臣弟的……”
禛又怎么舍得让自己这宝贝弟弟为难,立马挡下怡王接下去的话,转头对璇玑说:“原来都是一家人,这样敢情更好,这样朕就能完全放心,让你去给朕办事。十三弟你能找到你这样位……这样位的贤助,这也是你们两人的福气啊。”
言下之意,璇玑这位‘弟媳’,皇帝他是认下了,我都不知道是要夸禛开明,还是说禛宠弟弟,已经宠得没有个边际了。璇玑脸上带了人皮面具,所以看不出表情,不过我察觉到他内心,那阵暗带隐伤的讽刺情绪,不过他表面上倒是给装出了个样子,双膝跪到地上谢主隆恩,怡王无可奈何只有跟着跪地谢恩。
我果然没想错,璇玑那身世要说穿了,我们一准倒霉,不过只要把事情推到怡王身上,他这皇帝四哥便不会深究,只当那些规矩是自己弟弟给/调/教/出来的,即使日后禛发现,陈福就是当年那璇玑,禛也会看在自己弟弟的份上既往不咎。
禛把心中的疑虑解开后,亲自拿出锁在东暖阁中暗柜的地图,也就是之前我们从陇山上带回那几份地图,和我们这次取回的地图合在一起,终于合成幅完整的地图。
这天下午,禛依璇玑所奏,秘密把白晋、雷孝思、费隐三个神甫宣进园子,他们曾参加过《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如今我们要让他们,把刺绣在衣物上的地图,按统一的尺度和规划绘制成将士们都能看懂的地图。
跪安以后,我一身轻松的跨出九州青晏的殿门,眼睛看不见,听我步声前进的璇玑,跟在我后面,用鄙夷的语气道:“怎么,就开始松獬了。年七你是真没见识,还是在装?你以为拿到那东西,便大局已定?真正的较量,这才刚开始,接下去要为出兵廷议,要选拔合适的将才,这一连串的大动作,你以为会没有任何阻力?朝廷里那批老骨头,可人人都想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不会有几个人支持皇帝出兵的。”
我大为惊讶的转头望着璇玑,他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真正的较量这才开始?我本还想向他问个仔细,不过走在我们前头的怡王这时,倒回头来将璇玑拉走,留我句话说:“容儿,你要为皇上分这份忧,最直接的办法是回头去问皇上,需要你办些什么。本王的禁脔,本王就先带回去了。”
他最后一句,大有抱怨的意味在里面,不过怡王也说得很对,想帮禛,我应该转身回东暖阁,问禛需要我怎么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