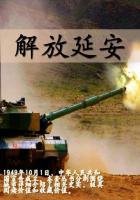静谧微凉的夜,热泪一颗颗滑落,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兴师问罪么,为什么又忍不住眼泪?
衬衣很快就**大片,欧黎没追问,将她背回房放在沙发里,片刻后端来一盆稍烫的水替她清洗又脏又凉的双脚。脚洗好之后他又重新换了盆水和毛巾替她擦脸,并细心在泪流不止的眼睛处停留好一阵子,让她明天眼睛不至于过于浮肿。默默看他做着这些,宋词的心脏一阵阵绞痛,剧烈程度令她忍不住颤抖。
将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做完一切的他才挨着坐下,宠溺摸摸她的头:
“傻小孩,还在哭呢,到底怎么回事?接到电话我吓了一跳,来,说说。”
“欧黎…”泪雾朦胧里的男子依然有着和当年分毫不改的容颜,温言温语亦是熟悉的语气语调,可是宋词不敢确定他真的就是自己十四岁开始认识的少年,那张光盘足以颠覆一切认知与信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也找不到愤怒或者勇气逼问事实。
伸手替她擦掉蜿蜒泪水,欧黎微蹙眉头,琉璃般的瞳仁洋溢着浓浓柔情:“你只要说出发生什么事,我才能想办法解决或者想办法让你高兴,傻小孩,平时你也不是这么爱哭的人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啦好啦,别哭,有我在,什么事都会好起来,不想说可以不说,行不行?”
他越说,宋词的泪水越汹涌。
温暖的怀抱,节奏如常的心跳,靠在他怀里,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过。
可是,自欺欺人是她最不擅长的事,一闭上眼睛,那些画面就像魔鬼似的狞笑着跳进脑海。
怎么劝都劝不好,欧黎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遂拉起怀抱里的人,小心翼翼捧住她的脸:“傻小孩,我还记得你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最必须的就是信任和坦诚,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我爱你,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懂吗?”
一句我爱你,思绪混乱的宋词忽然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反常的只流泪不说话是害怕失去——
或许,从相遇伊始,所有一切都变得不重要,除开他。
而自己,也不是那个可以当做什么都不在乎的倔强小女孩。
她在乎并浓烈爱着他,所以不能失去,即便所谓的失去只是想象。
“我也爱你。”
言罢,挣脱束缚站起的她莫名一笑,迅速而用力的解开上衣扣子。线衣,衬衣,长裤,底裤,当所有衣物纷纷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落地,欧黎对着光洁如玉的胴/体目瞪口呆。他是个正常的年轻男人,眼前一/丝/不/挂泛出美好光泽的娇躯是他心爱的之人,说没反应是假的,可是,喉头滑动的他很快联想到什么,惊愕面容逐渐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
“你…你干什么?”字字重如千斤,他问得艰难,只是此时的艰难与本能反应并无关系。
“不是说爱我,那么,证明它。”
“别胡闹,会着凉的。”
弯腰欲捡衣物,手指却如石头般僵硬,勾了好几次都勾不起一件,他索性回房取来一床毛巾毯。
明显感觉到他的手在抖,雕塑般站立的宋词淡淡重复自己上一句话。
“就算爱需要证明,也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欧黎轻轻开口,睫毛覆盖住布满忧伤与担忧的眼。
“两个毫无感情的人尚且能做,为什么两个口口声声说相爱的人不能?或者说,所谓的毫无感情,根本就是可笑且可耻的谎话。”凉意丝丝缕缕攀爬上未着一物的躯体,她的嗓音也是轻渺的,但不知不觉间有股由内而发的寒意浸在里面。清楚看见近在咫尺的男人往后趔趄一小步,她笑了,凄凉如凋落的残花。
“你…”
尚未斟酌出合适的话语,宋词已抱上来,冰凉咸湿的唇贴上他的。
错愕张嘴的瞬间,她的小舌滑进去,疯狂吻着。
他们之间自然有过拥抱接吻之类的亲密举动,只是没一次像这回,浓郁血腥味充斥其间,热烈,绝望。当两人唇齿间全都溢满温腥味道时,欧黎决然推开她,缓缓倒退至米色墙壁旁,秀颀身体无力滑落,斜刘海遮住填充太多复杂的眼睛:“是不是徐远婷找过你?宋词,对不起。”
极尽狂热因为道歉骤然冷寂,宋词扯了扯嘴角想笑,殊不知,笑比哭还难看——
只有老天清楚,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对不起。
一句道歉,便足以证明事情不仅是真的,而且在发生的当时,他是清醒的。
想到潜意识里不断说服自己他有可能被迫或被下药,泠然立在原地的她觉得很可笑。欧黎是谁,他是从小就跟父亲混黑道在父亲死后摆平所有争端纠纷的角色,区区一个徐远婷,怎么可能给他下药或用强?原来,并非只有不爱的时候才借口多多,爱到深处,人会为了心里的人心甘情愿接受借口。
“为什么?”苍白无力的问题其实没什么意义,只是,除开这三个字,她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欠她的,而且…”
“欠她的?”宋词记起自己央求徐远山时的迫切与尴尬,冷冷讥诮:
“所以,人情债肉偿,是吗?”
尖锐刺骨的反问像一把利刃直插心房,顷刻鲜血汨汨,满面颓丧的男子努力撑着墙面缓缓站起,有气无力走向门口:“很多事情我无法跟你解释,也不想让你知道太多。知道得越多,过得越不安生,我爱你,不希望你卷入是非。很晚了,你留在这休息,我出去。”
“一个随时可以跟别的女人上床的男人,有什么资格言爱?你跟徐远婷,让我觉得恶心!”
用最快的速度将衣物套上,宋词狠狠推开欧黎,飞一般的逃出去。
黏黑如墨的夜,如同一头巨大的兽吞并天地万物。
什么东西扎入脚板,剧烈疼痛阵阵袭来,却不及心痛的万分之一。
无处可去的她借着路灯走到距离帝景几百米处的江畔,整整坐了一宿,落脚的地方,一片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