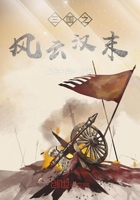好在这面汤已经不是太热,所以没有烫着女儿。但是看到精心准备的晚餐,一下子全没有了,她坐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安慰女儿说:“倒就倒了,别生气了。我本来打算带你去吃肯德基的,这不是正好吗?走吧,我们去吃肯德基。”
肯德基这种洋快餐,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随着这几年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城市人已经不再热衷于这种垃圾食品了。但是对农村的女儿来说,她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吃过,无异于一个传说。记得我与前妻离婚之前,有一次准备外出打工,因为舍不得女儿,我问女儿想吃什么?女儿说,想吃肯德基。于是我带着她满县城地找肯德基,后来才知道这个县城,根本还没有一家肯德基店。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女儿说:“会不会和动物园一样,应该关门了吧?”我说:“这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万一关门了,我们再翻进去。”女儿并没有怀疑我,在爸爸的面前她相信一切,相信什么事情都不会难住爸爸的。她忘记了刚才的不快,欢快得像一只小麻雀,坐在自行车后边,开始满大街地找肯德基。
虽然已经半夜了,肯德基店里还是有许多顾客。有人专门在这里蹭免费网络,有人是在这里谈恋爱,有人在这里吃夜宵。反正到了半夜,这家二十四小时的快餐店,就成了不想进酒吧的时尚青年最清静的场所。
说实话,我是第二次吃肯德基。第一次已经是好多年前,一位女老板请我吃的。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果然如孩子所料,很香,很好吃,比老家过年时炸的果子,还要香一百倍。当时别人埋单,并没有考虑到底要花多少钱。现在是自己出钱,我就有点拿不准了,不知道哪些东西便宜,特别是有一些名字,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比如蛋挞。
我与女儿站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才发现只有汉堡才是最好的,与老家的馒头最相似。而且从画面上看,那么大,每人一个汉堡,就足够了。于是,我与女儿每人点了一只汉堡。我想冰激凌就算了,太冷了,应该给女儿再点一杯饮料。女儿过去口渴了,基本喝的是白开水,对于饮料她是陌生的,特别是对于可乐,与肯德基一样,还没有喝过。等我问及可乐的时候,服务员说,特大杯八块,大杯七块,中杯六块。
女儿在旁边抢先说:“要小杯的。”我就说:“要小杯的吧,小杯的多少钱?”服务员说,没有小杯的,只有中杯,大杯,特大杯。我忽然想起以前听过老罗的演讲,明白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小杯这个词。
女儿说:“没有小杯就不要了。”
我摸了摸身上,明白自己囊中羞涩,所以顺从了女儿。我对女儿说,这些饮料里边,有咖啡因,人喝了会上瘾的,就像抽大烟。这虽然是借口,却是事实。不过,对于有些人而言,当钱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那么毒品还是问题吗?对于有些人,当钱已经是最大问题的时候,上瘾应该也不是问题了吧?
当我们端着两个汉堡,坐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这汉堡,与招牌上的样子,却小了不少,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女儿看了看画面,又看了看面前的实物,然后怀疑地说:“爸爸,是不是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劲,于是端着托盘,又回到前台。我指着画面说:“那上边那么大,为什么这个却这么小?”
服务员说:“一样啊?我们觉得一样大呀。”
我说:“怎么会一样呢?明显小很多的吧?”
服务员说:“我们觉得是一样的。你如果嫌小,可以多点几个呀?”
我说:“你们这是虚假宣传知道吗?”
服务员说:“你看看那下边的小字吧。”
我抬头再看了看,那个巨大的画面下边,写了一行小字“以实际大小为准”。我简直被气疯了。真想掏出那张单位自制的采访证,再吓吓他们。当我打电话给专门负责消费维权的同事,同事说,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报社六年前就报道过了。旁边的人也说:“一直都这样的,你不知道吗?”
其他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反而很奇怪地看着我,还有人甚至露出了嘲笑的神情。我心想,是自己吃得少,孤陋寡闻罢了,时代早就适应了这种幻象。所以我赶紧端着托盘离开了。回到桌子上,我递一个给了女儿。
女儿问:“筷子呢?”
我说:“吃这个不用筷子。”女儿四周看了一圈,发现大家都直接用手,也就明白了。在农村用手抓饭吃,会被家里人骂的,认为是脏孩子。但是在文明的城市,大家都学洋人,用手抓着吃,把肮脏当成了一种时尚。
女儿用手抓着咬了起来。其实女儿与城市人的动作,还是有差别的,女儿是满手抓着,而城市人仅仅用三根指头捏着,其余的指头像唱戏时的兰花指一般翘着,好像在体现自己很文明很干净的样子。
女儿吃完了,突然抬起头,发出一声感慨:“没有想到,这白菜,生着吃,也挺香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兔子爱吃菜叶子。”在老家,孩子们饿了时,偷吃过地里的生萝卜、西红柿,却从来没有偷吃过生白菜。我一直没有动手,只是看着女儿吃。她吃得那么香,一边吃一边回味,一边吃一边停下来,打量一眼这个汉堡。我拿起自己的那一块,又递给了女儿。
女儿说:“这是你的,你吃吧。”
我说:“都是给你买的。”
女儿摇摇头:“爸爸吃,你应该也饿了。”
我说:“爸爸不饿。其实爸爸在单位吃过了。”
我撒了一个谎。其实中午采访结束,只是匆匆地啃了两个馒头而已。看着面前的汉堡,老实说,我口水都出来了,但还是强咽了下去。在我一再强求下,女儿看了看汉堡,又看了看我,然后抓起汉堡,吃了起来。这一次,她吃得顺畅多了,里边的白菜没有一丁点掉出来。吃到最后一小块的时候,她还递到我嘴边,让我尝那么一口。
我没有拒绝。我知道,这一口,不能解决温饱,而是父女之间的情义,是一种温暖。等吃完了,女儿才问我:“爸爸,这东西,为什么叫汉堡呢?”我还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汉堡,只知道它与我们的馒头一样,都是食品的名字而已。我们吃了一辈子的馒头,只知道咽下肚子,肚子就不咕咕叫了,谁又追究过为什么它叫馒头呢?馒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坐在我们对面桌子上的好像是一对母女。她们点了一堆的东西,有汉堡,有薯条,有鸡腿,有鸡翅。之所以知道这些名字,是我一边看着她们吃的东西,一边与墙上挂着的画面进行了对照。据我估计,她们两个人,总共加起来,应该有两百多块吧?但是,她们还没有吃几口,竟然就离开了。特别是有一瓶可乐,只喝了不到半瓶子。
“真是太可惜了。”我看着她们一离开,直到看不见的时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来到对面那一桌,提起那半瓶她们喝剩的可乐,蹲在女儿的面前。然后找来一个杯子,给女儿满满地倒了一杯。
我得意地说:“喝吧。”
女儿摇摇头:“不敢,喝了会上瘾的,上瘾了天天要喝怎么办?”
我开玩笑说:“上瘾了,就把你卖给这里。”
女儿说:“这是人家喝剩的。”
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端起来,一仰头,一口气喝光了,打了一个嗝,做了表率。然后又倒满一杯,蹲在女儿面前说:“到你了。”
女儿磨蹭了半天,才把杯子端起来,先轻轻地抿一口,咂了咂嘴巴,舔了舔嘴唇,然后告诉我说,与白开水就是不一样,里边有一群小鱼儿,喝下去的时候小鱼儿会不停地咬着你的喉咙,咬得你心里痒痒。
这时发现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对面那桌子刚刚离开的女人,她竟然返回来了。她瞪着眼睛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们这喝的是谁的可乐啊?我跟女儿刚刚上个厕所,你们就这样了?喝别人喝剩的东西,你们难道是乞丐吗?你们想喝难道不会自己买去?”
原来人家不是走了,是带着小孩上厕所了。四周的人都朝这边看着,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一把刀子。对待乞丐的刀子中还留有一些同情,但是现在这把刀子像是对待一个小偷那样毫不留情。他们觉得这个小偷,偷了别人钱包算是干净的,如今却偷了别人喝剩的半瓶子可乐,可能还有别人的唾沫星子。
我一时尴尬极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暗暗地想,这件事情要是大人干的,那就太离奇了;要是孩子干的,应该还是能说通的。最后我指着女儿,假装严厉地说:“这孩子,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呢?”说完,又转身对这个女人连赔不是:“对不起,孩子不懂事,要不我赔你一瓶吧?”
那个女人不再吱声,提起剩下的半瓶子可乐,稀里哗啦地倒进垃圾桶,然后气呼呼地离开了。女儿站起来,一句话没有说,也朝门外走。我推着自行车,跟着女儿,走一步就说一个“对不起”,一直走了大半条街。女儿每听到一个“对不起”,脸上就放松了一些,到后来就在前边偷偷地笑。
我看到一家好德超市,连忙跑过去,花了三块五毛钱,买了一小瓶子可乐,然后递给女儿说:“爸爸给你道歉,你尝尝这个可乐,里边的小鱼儿更多,它们会吐出一串串气泡。”
女儿撅着嘴,并不接,但是坐到一个草坪上,不走了。我坐到女儿的身边,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在爸爸上中学的时候,一天两顿稀溜溜的糊汤,都吃不饱,那个饿啊,恨不得咬自己的胳膊一口。有个同学家里很有钱,顿顿吃半碗倒半碗。有一次我要吃他的剩饭,他就朝碗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对我说,可以给你吃,只要你喊一声‘爸爸’就行。我真的喊了,因为我太饿了。”
我以为女儿怪我拿她做挡箭牌,伤了她的自尊。但是事后她才告诉我,她宁愿咬自己一口,也不愿意喝别人剩下的东西,觉得恶心。听完故事,女儿一下子贴到我怀里,不等我把新买的可乐递过去,女儿已经拿过那瓶可乐拧开了盖子,放到我嘴边说:“爸爸,你喝吧。”
我喝了一口,又递到女儿的嘴边说:“到你了。”就这样,我们一人一口,推来推去,喝到了什么时候,已经不知道了。等我们站起身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喝了那么久,一瓶五百毫升的可乐,却仍然还剩有半瓶子。
我对女儿说:“这些是留给你明天喝的。”
女儿说:“我要和爸爸一起喝。”
大街上的人稀少了,小汽车也零零落落,一些路灯熄灭了,高楼大厦的窗户变得一片漆黑,像一只只盲人的大眼睛。草坪上开始起了露水,把衣服都打湿了。偶尔有路过的人,自言自语:“还有人在喝酒。”在他们看来,在深更半夜,一人一口换着喝的,除了醉人的酒,还能有什么呢?
5、毛毛熊与二十一楼
第二天早上,就是正月初八,除了给女儿买了两个包子与一杯豆浆之外,我还给她准备了一点蔬菜,包括两个土豆,两个西红柿,与两个鸡蛋。我一再叮嘱她,什么时候饿了,就什么时候做饭吃,千万不要再等爸爸了。我还拍了拍电视,说是如果无聊,就看看电视吧,如果看不清,就使劲地拍。但是女儿说,什么都不需要,她要在家里做寒假作业了。
临到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回过头告诉女儿,今天的报纸上有爸爸的名字,是爸爸昨天忙了大半天采访的,是一起车祸,一下子冲到了桥下,死了三个人。晚上我会带一张报纸,给她看看。女儿听着,很自豪地问:“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爸爸的名字?”
我说:“不是所有人,但有很多人,订了我们报纸的人。你说爸爸是不是很厉害?”
女儿说:“好厉害。我们同学都说,说县长见到爸爸,都要握手的,是不是?”在老家那里,是没有记者的,有些报纸会设个记者站,基本是在宣传部兼职的宣传员。这几天经历了这么多,女儿还是表示了以我为荣,不知道是记者的光环,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光环,还是“父亲”头上的光环。
当我赶到办公室,打开当天的报纸,从第一版一直翻到最后一版,都没有发现自己昨天采访的内容。我有些奇怪,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又翻了好几遍。领导明白我在找自己的稿件,于是告诉我说:“收到宣传部的通知了,不准报道,因为死的三个人,都是日本人。”
我说:“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就不发生车祸了?”
领导说:“目前不是中日关系紧张吗?怕一报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日本方面要拿车祸说事。”
按照报纸的考核规定,由于上边的原因不能见报的稿件,打分只算一半。现在对我来说,算工分虽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早上跟女儿夸下了海口。本来想带一份报纸回家,让女儿看看“本报记者陈元”,证实这个城市很多人在这一天,都能看到爸爸的名字与爸爸采写的文章。
白天又发生一个车祸,虽然这次死的是咱中国人,领导就没有好意思再派我去采访。于是这一天,我一直无所事事,打了几个电话,到处找找线索,看看有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但是这一天,可能因为还在春节当中,坏人还没有上班,人性恶被节日的气氛冲淡了,所以整个城市安静得连一起像样的偷盗都没有,只有几个小小的因燃放鞭炮引起的小火灾。
天还没有黑透,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我还没有掏出钥匙,一把孤独的钥匙也不会发出叮当的声响,但是女儿已经替我把门打开了。当我再问她,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她告诉我,她在窗口看到的,看到我从一只蚂蚁一样的小黑点,越走越近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人。我明白,从我出门时起,女儿就趴在窗台上,朝着窗外的世界看着,她不仅在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也在等待着唯一一个亲人的归来。
女儿问:“你带的报纸呢?”
我装作吃惊的样子说:“哎呀,忘记了。”
女儿说,她回家后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当记者的爸爸”。我不知道,在女儿的笔下,这个“当记者的爸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对警察的央求,与动物园检票员的冲撞,以及在肯德基店里的尴尬,女儿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晚上临睡之前,看到女儿抱出一个布娃娃,湿漉漉的,不停地滴着水滴,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别人玩过的旧东西。她告诉我:“还没有晒干,如果晒干了就好了,就可以抱着它睡觉了。”
我问:“哪来的?”
女儿说:“捡的。”
我问:“从哪里捡的?”
女儿说:“从楼下。不过,我给它洗过澡了。”
我说:“扔掉它!”我看了看,上边黄蜡蜡的,明白那肯定是哪个小孩子,把屎尿沾上去了,不然人家不会扔掉吧。女儿紧紧地抱着,好像要被谁抢走似的。而且还拍着它,像是一位母亲在哄自己的孩子睡觉。
我说:“扔掉它,太脏了。”说实话,在我童年的时候,基本是没有一件玩具的,唯一一个就是弹弓,还是自己制作的。更别说布娃娃什么的了。到了女儿这一代,城市里的孩子,电动小汽车已经玩腻了,如今在玩变形金刚与遥控飞机了。每个孩子家里的玩具,都是成堆成堆的,说是玩具不准确,应该是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开发智力的工具。但是对于老家的孩子有什么呢?为了他们能够走出大山,父母不允许他们花费精力去自制玩具,希望他们把力气用在学习上,用在放牛、挖药与种地上,只有这些恐怕对他们才有意义吧?
女儿双手一松,这个肮脏的布娃娃就落到了窗外。窗外正好是一条马路,被她扔下去的布娃娃,被过往的车辆压来压去。女儿趴在窗台上看着,好像不是压在布娃娃的身上,而是压在了她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在楼下碰到打扫卫生的阿姨,才从阿姨那里了解到,为了捡这个布娃娃,还发生了一些故事。那是在我出门以后,女儿趴在窗口目送着我远去,发现有人把一只布娃娃扔进了垃圾桶。女儿看了半天,确定是别人扔掉不要的,于是赶紧跑到楼下,从垃圾桶里拾起了它。